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中“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认定
——从“毒豆芽”事件谈起
康达刑辩看法
根据《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或者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从罪状看,“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犯罪构成中的核心构成要件要素。虽然司法解释中列出了“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认定标准,但司法实践中就这一构成要件要素的认定仍然容易出现偏差,这一问题在“毒豆芽”事件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01
“毒豆芽”事件始末
(1)“毒豆芽”的由来
所谓“毒豆芽”,通常是指在发制过程中掺入了6-苄基腺嘌呤和4-氯苯氧乙酸钠的豆芽。因具有提高种子发芽率、改善豆芽品质等作用,上世纪80年代以来,6-苄基腺嘌呤和4-氯苯氧乙酸钠就被用于豆芽的发制,还曾以食品添加剂的身份被列入关于食品添加剂使用的国家标准。不过,原卫生部在2011年发布的《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2760-2011)中却将6-苄基腺嘌呤和4-氯苯氧乙酸钠调整出了食品添加剂的行列。相应地,《卫生部办公厅关于<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2760-2011)有关问题的复函》(卫办监督函〔2011〕919号)和《关于食品添加剂对羟基苯甲酸丙酯等33种产品监管工作的公告》(质检办食监函〔2011〕765号)两份文件也明确不再允许将6-苄基腺嘌呤和4-氯苯氧乙酸钠作为食品添加剂使用,理由是缺乏工艺必要性,并未提及对人体健康有危害。
(2)“毒豆芽”入刑
2011年4月17日,辽宁省沈阳市公安局打掉了多个在豆芽发制过程中使用6-苄基腺嘌呤、4-氯苯氧乙酸钠等物质的作坊,涉案人员随后因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被判刑。这起案件拉开了全国范围内“毒豆芽”入刑的序幕,被称为“毒豆芽”第一案。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3〕12号)(以下简称《旧解释》),其第二十条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罪中“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认定标准。部分刑事司法机关便以此为依据,将6-苄基腺嘌呤和4-氯苯氧乙酸认定为“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大量“毒豆芽”的生产、销售人员因此被判处“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据媒体“澎湃新闻”报道,2013年1月1日到2014年8月22日间,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的相关案例有709起,918人因“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获刑。
(3)“毒豆芽”事件的反转
2015年4月13日,原国家食药监总局和农业部、卫计委三部门联合发布公告(2015年第11号),明确了豆芽生产过程中使用4-氯苯氧乙酸钠、6-苄基腺嘌呤等物质的安全性尚无结论,但不得将其用于豆芽的生产,违者由相关行政机关处理。随着行政主管机关监管口径的软化,刑事司法机关对“毒豆芽”的态度也迅速发生反转。2015年6月16日,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人民法院以没有证据证明4-氯苯氧乙酸钠、6-苄基腺嘌呤对人体造成何种危害为由,将一审被判处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芽农郭某、鲁某重审改判无罪,形成了同类案件中首例无罪判例。这起无罪判例造成了强烈的示范效应,从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的裁判文书看,2015年之后,“毒豆芽”刑事裁判的数量急剧下降。不过,直到2024年仍然有零星的“毒豆芽”刑事裁判出现。
(4)“毒豆芽”事件的启示
“毒豆芽”事件的出现,表明部分刑事司法机关对于4-氯苯氧乙酸钠、6-苄基腺嘌呤是否属于“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认定出现了偏差。中国法学会食品安全法治研究中心对2014年1月1日至2015年1月31日间的203份“毒豆芽”刑事判决梳理后发现,《旧解释》第二十条“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认定标准的四个项目均有判决书引用。而事实上,4-氯苯氧乙酸钠、6-苄基腺嘌呤不符合这四个项目中任何一项的要求:其一,禁止在食品中使用4-氯苯氧乙酸钠、6-苄基腺嘌呤的文件并不是法律、法规;其二,4-氯苯氧乙酸钠、6-苄基腺嘌呤不在《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单》或《保健食品中可能非法添加的物质名单》之上;其三,4-氯苯氧乙酸钠、6-苄基腺嘌呤并不属于国务院有关部门公告禁止使用的农药、兽药;其四,4-氯苯氧乙酸钠、6-苄基腺嘌呤对人体健康是否有危害尚无定论。
食品安全关系到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对食品安全领域犯罪严惩重处既是刑事司法机关的法定职责,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然而,刑罚作为最为严厉的法律制裁手段,刑事诉讼作为大量消耗司法资源的诉讼活动,应当适用于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将刑事手段适用于应当通过行政手段解决的食品安全问题,不仅不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而且浪费了大量原本应当用于惩处严重危害食品安全行为的宝贵司法资源。“毒豆芽”事件中的豆芽生产不合规问题本可通过行政手段调整,却引发了一批法律适用混乱且前后矛盾的刑事案件,严重损害了刑事司法的权威性。为了防范“毒豆芽”事件再次出现,有必要对当前刑事司法机关的“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认定现状进行审视并有针对性地对认定规则加以完善。
02
“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认定现状
1.“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认定依据
目前,“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认定依据主要包括《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1〕24号)(以下简称《新解释》)第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第15批指导性案例中第70号案例。
《新解释》第九条是“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现行认定标准,该条款关于“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表述共有三项:一是因危害人体健康,被法律、法规禁止在食品生产经营活动中添加、使用的物质;二是因危害人体健康,被国务院有关部门列入《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单》《保健食品中可能非法添加的物质名单》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公告的禁用农药、《食品动物中禁止使用的药品及其他化合物清单》等名单上的物质;三是其他有毒、有害的物质。由于使用第一项进行认定时需要援引法律或法规,而《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或法规以原则性条款为主,第三项又属于兜底条款,故依据这两项开展认定在司法实践中不具有操作性。第二项则列出了四个包含具体物质名称的名单,便于刑事司法机关“对号入座”。因此,司法实践中主要以这四个名单作为“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实际认定标准。
不过,《新解释》第九条无法完全解决“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认定问题。一方面,这四个名单并非都定期更新。如《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单》在2011年之后就再未更新。另一方面,虽然《新解释》第九条第二项表述时在四个名单之后缀上了“等名单”的表述,但此处的“等”字究竟是作等内解释还是等外解释尚不明确。如果作等内解释,将导致部分“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无法得到认定。如果作等外解释,“等名单”所代表的未列明的名单该如何理解亦不清楚。司法实践中,目前只是将市场监管总局陆续下发的多个附有“有毒有害专家认定意见”的特定规范性文件中所列名单上的物质作为“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予以认定。例如《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打击食品中非法添加非布司他及其系列衍生物违法行为的通知》中所列的非布司他及其系列衍生物可以被认定为“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即便如此,这些名单的数量仍然是有限的。因此,仅仅使用《新解释》第九条,无法解决四个名单和市场监管总局特定规范性文件所列名单之外的物质的认定。
其实,这一问题早在《旧解释》第二十条首次确立“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认定标准时就已经存在。该条款第二项中列出了《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单》或《保健食品中可能非法添加的物质名单》两个名单,但也无法有效解决这两个名单之外物质的认定。为此,最高人民法院通过指导性案例的方式确立了“同等属性和同等危害”裁判规则。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第15批指导性案例,其中第70号案例为北京阳光一佰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习文有等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该案根据当时有效的《旧解释》作出判决。判决认为,被告人在食品生产经营中添加的盐酸丁二胍虽然不是国务院有关部门公布的《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单》和《保健食品中可能非法添加的物质名单》中的物质,但根据扬州大学医学院葛晓群教授出具的专家意见和南京医科大学司法鉴定所的鉴定意见证明,其与《保健食品中可能非法添加的物质名单》中的其他降糖类西药(盐酸二甲双胍、盐酸苯乙双胍)具有同等属性和同等危害。据此,该指导性案例将盐酸丁二胍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的“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虽然“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认定标准随着司法解释的废立而改变,但这一指导性案例所确立的裁判规则目前仍然有效。根据该裁判规则,如果能证明食品中添加的某物质与《新解释》第九条第二项所列四个名单及市场监管总局特定规范性文件所列名单(以下简称“五个名单”)中的特定物质具有“同等属性和同等危害”,就可以将该物质认定为“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
2.“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认定中的问题
不过,将《新解释》第九条及“同等属性和同等危害”裁判规则用于“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认定时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在这些问题未得到妥善解决的情况下,“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认定容易出现偏差。
第70号案例并未明确“同等属性和同等危害”的具体内涵,出于操作便捷性等原因的考虑,目前实践中主要将“同等属性和同等危害”理解为具有相同的核心药效团。这种理解的科学依据为药理学上的构效关系理论,即化学结构相似的药物可通过同一机制发挥作用,引起相似的生理效应。根据这一理论,当某物质与五个名单中的特定物质具有同一核心药效团时,不仅前者可以被认定为是后者的衍生物,而且前者与后者还对人体健康具有相似的危害。此时,该物质就可以被认定为与五个名单中的特定物质具有“同等属性和同等危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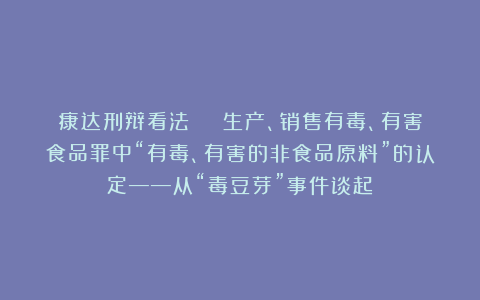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多个特定规范性文件中附的“有毒有害专家认定意见”普遍采用这一理解。如2023年的《关于打击食品中非法添加那非拉非类物质及其系列衍生物违法行为的意见》中所附的“苯丙代卡巴地那非,那非、拉非类物质及其系列衍生物有毒有害专家认定意见”中就指出,苯丙代卡巴地那非属于新型那非类药物衍生物,与“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西地那非、他达拉非等核心药效团一致,具有同等属性和同等危害。司法实践中也采用这一理解实现了五个名单外“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认定。如2023年江苏省张家港市公安局在办理一起食品非法添加案件过程中,发现添加物双辛酚丁并不在五个名单上,但专家意见认为其与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特定规范性文件中所列的有毒有害物质双醋酚丁具有同一核心药效团,从而认定两者具有同等属性和同等危害。
然而,这五个名单中所列物质的核心药效团种类有限,且其中部分物质如革皮水解物并非单一化合物,当名单之外的物质不具备相应的核心药效团,但实质上对人体健康有危害时,就无法根据“同等属性和同等危害”裁判规则将这些物质认定为“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
如果把“同等属性和同等危害”的内涵理解为对人体健康危害的相当性,同一核心药效团只是对人体健康危害相当性在化学结构上的一种表现方式,便可以突破同一核心药效团的限制。然而,采用这一理解在实际运用过程中也会出现一些问题。一方面,在进行人体健康危害相当性认定时存在寻找对标物的困难。对五个名单梳理后可以发现,名单中所列物质的毒性差异极大。既有毒性较大的农药如敌敌畏,也有毒性较低的药品如万古霉素。在将五个名单外的物质对名单中物质进行人体健康危害比较时,应当选择哪个毒性等级的名单中物质作为对标物,现有认定标准无法解决。另一方面,会得出在食品中合法掺入的物质也可以被认定为“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悖论。以人体健康危害相当性为认定规则时,既然万古霉素被列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名单,那么与万古霉素对人体健康危害具有相当性的抗生素也可以被认定为“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但事实上五个名单中的抗生素数量相当有限,反而不少抗生素都作为合法兽药应用于食用动物生产。对于这一悖论,现有认定标准也无法给出合理解释。
另外,司法实践中对于人体健康危害的相当性的判断也存在科学依据不足的问题。对于与五个名单中物质不具有同一核心药效团的物质而言,其对人体健康危害的相当性无法通过构效关系理论得出,需要从毒理学数据、暴露水平评估等维度将其与五个名单中物质比对后才能作出判断。然而,对威科先行数据库上近3年的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刑事裁判书梳理后发现:在那些与五个名单中物质不具有同一核心药效团的物质被认定为“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案件中,“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认定依据仅仅只是专家或行政机关基于固有知识和经验出具的推断性意见。这些意见中只是陈述了该物质对人体健康具有何种危害性,便以此为依据将其认定“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并没有指出该物质与名单中何种物质相比对人体健康危害具有相当性,也未附上相应的毒理学数据、暴露水平评估等科学证据。这种认定意见虽然有专家和行政机关的专业性和权威性作背书,但在缺乏科学证据作为根据的情况下,容易过多地受案件内外各种主观因素影响而失去可靠性。近年来判决的“毒豆芽”有罪裁判,针对不在五个名单中的4-氯苯氧乙酸钠、6-苄基腺嘌呤,司法机关只是依据行政机关提交的4-氯苯氧乙酸钠、6-苄基腺嘌呤属于“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简要认定意见。认定意见中,并没有就其与五个名单中的何种物质对人体健康危害具有相当性进行分析,更没有提供毒理学数据等科学证据予以支撑。对于与五个名单中物质不具有同一核心药效团的物质的“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认定规则不尽完善,是导致“毒豆芽”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如果这一问题未得到解决,类似于“毒豆芽”事件还可能会出现。
03
“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认定规则的完善
综上,“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认定中存在的问题,核心在于与五个名单中物质不具有同一核心药效团的物质,依据现有认定标准无法实现合理认定。因此,有必要在现有认定标准基础上,针对这类物质制定合理的认定规则。
(1)法益分析
合理的认定规则需要满足两方面的要求。一是合理的认定规则应当有助于保护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对应的法益。依据合理规则得出的“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认定结论应当有助于实现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立法目的,而《刑法》中特定罪名法条的立法目的正是该罪名所保护的法益。二是合理的认定规则需要体现法益的保护倾向。法秩序的稳定性对于法律发挥秩序维护功能至关重要。将现有认定标准反映出的司法机关对该罪名相关法益的保护倾向在新制定的认定规则中得到体现有助于维护法秩序的稳定性。基于此,在规则制定前需要先分别根据刑法条文和认定标准对这一罪名所保护的法益进行分析。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所保护的首要法益是食品生产、销售管理秩序。该罪名位于《刑法》第三章第一节。《刑法》第三章的类罪名为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第三章第一节的类罪名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因此,从体系解释的角度看,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产生源于所生产、销售的食品质量存在缺陷,违反了国家的经济管理法律法规,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而食品生产、销售管理秩序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食品生产、销售管理秩序是一个难以被准确界定的概念。刑事诉讼中要准确把握这一概念,可以通过分析现有认定标准反映出的司法机关对食品生产、销售管理秩序法益的保护倾向。
现有认定标准中的“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可以分为两类:一类物质对人体健康产生损害的风险较大,不得以任何形式入口,如敌敌畏、吊白块等,禁止食品中掺入这类物质的食品生产、销售管理秩序的确立基于这类物质对人体健康产生损害的风险。另一类物质对人体健康产生损害的风险较小,能药品等形式入口,如西地那非、盐酸克仑特罗等,禁止食品中掺入这类物质的的食品生产、销售管理秩序的确立不仅基于这类物质对人体健康产生损害的风险,还基于其它的行政管理目的。这正是五个名单中物质毒性相差较大的原因。以《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单》中的万古霉素为例,其作为一种经过安全性评价的药品,对人体健康产生损害的风险很低,禁止将其掺入食品或食用动物饲料的食品生产、销售管理秩序的确立不仅基于基对人体健康产生损害的风险,还基于防止耐药菌泛滥的行政管理目的。万古霉素被认为是治疗多重耐药革兰氏阳性菌严重感染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掺入到食品或食用动物的饲料中,虽然不一定会给人体健康造成现实危害,但必然会加速万古霉素耐药菌泛滥,导致人们在被万古霉素耐药菌感染时面临无药可用的境地。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所保护的次要法益是人体健康。从文义解释的角度看,立法者在罪名中将食品限定为“有毒、有害”,并在罪状中要求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都强调了食品或其原料应当具备“有毒、有害”属性,即具有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的可能性。从体系解释的角度看,虽然法条对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基本犯的表述中并没有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的表述,但其结果加重犯却直接将“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作为加重情节,这也就意味着基本犯包含了对人体健康造成一定危害,但尚未达到严重危害的情形。此外,现有认定标准也反映出司法机关对人体健康法益的保护倾向。具体表现为:《新解释》第九条“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认定标准关于三类物质的表述中均强调了有毒、有害或危害人体健康,而五个名单中的物质也均具有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的可能性。
(2)规则构建
通过上述法益分析可以看出,与五个名单中物质不具有同一核心药效团的物质要被认定为“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需要同时侵害到食品生产、销售管理秩序和人体健康两项法益。不过,两项法益受到侵害所需具备的条件并不相同。在食品中添加特定物质时,只要该物质具有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的可能性,就足以侵害人体健康法益。而只有在该物质对人体健康产生的危害达到一定程度,或在食品中添加特定物质会影响到特定行政管理目的时,才足以侵害到食品生产、销售管理秩序法益。在认定特定物质是否为“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时,需要先审查其是否具有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的可能性。
结合上文所述司法实践中“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认定中存在的问题,刑事诉讼中就特定物质具有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可能性的判断,不能仅凭专家或行政机关所做的推断性意见就直接认定,还应当根据逻辑和常识,对其认定依据的充分性开展审查,特别是作为重要依据的毒理学数据、暴露水平评估等科学证据。
在确认该特定物质具有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可能性的基础上,还需要进一步核实其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的程度。需要根据其毒理学特性,通过实验收集急性毒性、慢性毒性、遗传毒性、致癌性、致畸性、生殖毒性等毒理学数据,将相应毒理学数据与名单中有相似毒理学特性的物质进行比对,判断其是否存在危害相当性。如果在某个毒理学指标上达到了相当性,该特定物质就可以被认定为“有害、有害的非食品原料”。如犯罪嫌疑人使用氰化钠毒杀土狗后将狗肉售卖用于食用,狗肉中所含有氰化钠的半数致死量为6.4 mg/kg(大鼠经口),远远小于名单中敌敌畏的半数致死量50至110mg/kg(大鼠经口)。因此,既不在名单上,与五个名单中物质也不具有同一核心药效团的物质氰化钠可以被认定为“有害、有害的非食品原料”。
如果某些物质虽然具有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可能性,但危害性程度与名单中物质不具有相当性时,需要进一步核实添加该物质是否会影响特定行政目的实现。例如,将某种人用抗生素用于食用动物生产时,虽然其对人体健康危害性程度可能不如万古霉素,但同样可以影响防止耐药菌泛滥这一行政目的实现。因此,在确认该抗生素具有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可能的基础上,结合特定行政目的,也可以认定其危害了食品生产、销售管理秩序法益,从而将其认定为“有害、有害的非食品原料”。不过,是否影响特定行政目的实现是一个具有较强专门性的问题,基层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在个案中很难做出准确的判断。如果允许个案中对此进行判断,判断标准的不统一可能引发法秩序的混乱。为此,这类物质要被认定为“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应当由国家行政主管机关市场监管总局统一规定,包括对四个名单进行增补或发布附有“有毒有害专家认定意见”的特定规范性文件,例如上文提及的《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打击食品中非法添加非布司他及其系列衍生物违法行为的通知》。
如果采用上述认定规则,“毒豆芽”案中添加的4-氯苯氧乙酸钠、6-苄基腺嘌呤将无法被认定为“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4-氯苯氧乙酸钠、6-苄基腺嘌呤并不是“五个名单”上的物质,且与名单中物质也不具有同一核心药效团。因此,认定其是否为“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需要对其毒理学特性进行判断,认定其对人体健康具有危害可能性的基础上,或是确定其特定毒理学特性与名单中的物质具有相当性,或是确实其基于特定行政管理目的需要已被市场监管总局列入增补名单。然而,4-氯苯氧乙酸钠、6-苄基腺嘌呤对人体健康的危害性并不明确,也不在市场监管总局的增补名单上。因此,按照上述认定规则,“毒豆芽”案中添加的4-氯苯氧乙酸钠、6-苄基腺嘌呤无法被认定为“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
作者简介
翟李鹏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 实习律师
中国人民大学证据法学博士,具有12年直辖市公安机关工作经验,专注于刑事辩护、刑事控告等业务领域。
#artContent img{max-width:656px;} #artContent h1{font-size:16px;font-weight: 400;}#artContent p img{float:none !important;}#artContent table{width:100% !import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