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8-30 11:43
#头号创作者激励计划#
雪地里立着块木碑,字是刻上去的——“红卫兵小将晓黎之墓”。路过的人多半不知道,这墓里埋的是开国将军的女儿,走的时候才22岁,距她到北大荒插队,也就一年半的光景。
晓黎她爸是解放军的将军,1955年授的衔,打硬仗的时候腿上中过枪,后来走路都有点不利索。可到了60年代初,因为些特殊情况,将军自己拔枪没了。好在晓黎的妈是西北某省市空军疗养院的大校政委,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也没耽误晓黎在师大女子附中上学——那可是北京最有名的女中,能进去的都是拔尖的孩子。
1966年夏天,全国开始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这才真把晓黎的人生给拧了个弯。那时候她才19岁,一个小姑娘家,哪扛得住那么大的压力?今天有人贴她家门上的大字报,明天同学见了她就躲,慢慢地,她精神就快崩了,有时候说话都颠三倒四,有点不正常。她妈在西北听说了,赶紧坐飞机回北京,把她接走了,天天守着照顾,好半天才把她的状态拉回来点。
过了不到两年,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晓黎也响应了。打包行李的时候,她妈帮她叠了两件新棉衣,反复叮嘱“到了那儿别逞强”,可晓黎没听进去——她想着,到北大荒好好干活,说不定能证明自己不是“问题家庭的孩子”。
刚到北大荒的时候,晓黎确实挺拼的。黑土地上的活儿重,割大豆、翻地,她跟男知青一样干,没多久就当上了农工班的班长。营里组织女篮,她个子不算最高,可跑起来特冲,打球作风泼辣,成了队里的主力。她待人也实在,谁要是干活累得动不了,她就主动帮着扛;谁想家哭了,她就陪着坐一会儿,连里的知青都喜欢跟她来往。
1968年初冬,北大荒下了第一场大雪。雪下得大,把草甸、耕地、房子全盖白了,知青们都跑到外面看雪,有的还打雪仗,可晓黎却觉得浑身不得劲——身上没力气,关节还疼,连饭都吃不下。团医院的大夫给她量了体温,听了心肺,也没查出啥毛病,最后特批她回北京看病。
晓黎当时高兴坏了,她刚离开北京不到半年,做梦都想回去。走之前,她挨个问连里十几个北京知青:“家里有没有要帮忙办的事?带东西还是捎口信?”没人跟她客气,有的让她给家里带点肥皂,有的让她帮着看看老人。晓黎把这些事都记在小本子上,揣在贴身的口袋里。
回北京后,她先去医院做检查,剩下的时间就跑知青家。城东的胡同里钻过,城西的大院里去过,城南的平房也跑过,十几家跑下来,她自己的病都没顾上好好治。后来她没了的消息传到北京,那些知青家长都直跺脚,有的老太太还抹眼泪:“可惜了这孩子,心善,办事还牢靠。”
可北最后给的诊断结果,把晓黎和她妈都打懵了——红斑性狼疮。我后来专门问过医生朋友,他说这是种自体免疫病,年轻女性得的多,分两种:一种主要伤皮肤,常见在脸上;另一种不光伤皮肤,还能连累心、肾这些内脏,平时会发烧、没力气、关节疼,还老反复。晓黎得的就是后一种。
大夫还说,晓黎这病不是突然得的,病根早在运动那阵就埋下了。那时候她天天担惊受怕,晚上睡不着,饭也吃不下,神经系统(中医说的“肾”)和消化系统(“脾”)都乱了,时间长了,身体的免疫功能就出了问题,这病就找上门了。
晓黎在北京治了半年,病情稍微稳定了点。可这时候,家里外头的说法就来了:“这病又不是绝症,总在家养着不干活,不就成了’落后分子’?”“别人都在北大荒锻炼,就她躲在北京,像话吗?”连里的知青也老写信来,说谁当了畜牧排副排长,谁当了基建排副排长,谁被选成了团支部委员,还有人去修战备公路了——字里行间都是“大家都在进步,就你落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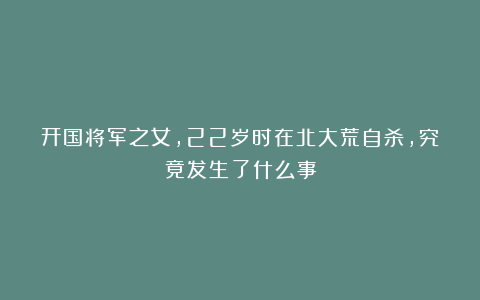
晓黎好强,哪能受得了这个?她拿着那些信,跟她妈说“我要回北大荒”。她妈舍不得,可那时候的大环境就是这样,连她妈单位的同事都劝“让孩子回基层锻炼,对治病也有好处”。最后没办法,她妈只能帮她收拾行李,还偷偷往她包里塞了点中药。
1969年9月下旬,晓黎跟战友契兰一起坐火车回北大荒。火车哐啷哐啷响了几千里,晓黎一路上没怎么说话,就盯着车窗外看。窗外的天是灰的,地是白的,一眼望不到头,她越看心里越沉,觉得那片黑土地上,好像没什么等着她的希望。
路过团部医院的时候,晓黎突然跟契兰说“我想再看看病”。她找到医院一个年轻的男大夫,跟人家说“我能不能留在医院治病?我可以帮着干活”,话说到最后,她甚至红着脸提了“想处对象”——她知道北大荒的连队条件差,没发好好治病,想通过这种方式改善下环境。可那男大夫听完,脸色立马变了,特鄙夷地说“你这是耍流氓”,还把这事告诉了契兰。
契兰本来就因为晓黎“求爱”的事有点烦她,回到连队后,没几天,晓黎的“丑事”就在女知青里传开了。有人添油加醋,说她“在团部医院纠缠大夫”,还有人说她“在团部的时候,躺在大卡车轱辘底下耍无赖”。晓黎听到这些话,躲在被子里哭了一夜,第二天眼睛肿得像桃子,谁跟她说话她都不搭理。
那时候晓黎还得靠安眠药才能睡着,之前在火车上,契兰怕她出事,一直帮她拿着药。可回到连队的当天,契兰忙着收拾行李,忘了把药从晓黎手里要回来。
第二天上午,同屋的鲁莉(跟晓黎是师大女附中同年级的,当时当司务长)从食堂回来取账本,一进门就看见晓黎躺在床上,盖着被子,看着像睡着了。鲁莉喊了她两声,没反应,走近了才发现,晓黎的脸色是青灰色的,一点血色都没有。她心里一慌,掀开被子,看见枕边滚着个空安眠药瓶——那是晓黎从北京带来的,瓶身上还贴着医院的标签。
鲁莉吓得尖叫起来,赶紧往营部医务所打电话。营部离连队有12里地,医务所的王大夫左腿有点瘸,接到电话后,骑着自行车拼命往这赶,路上摔了两回,膝盖都擦破了。到了宿舍,他一进门就喊“快开窗户!全都打开!”,然后从药箱里拿出强心针,给晓黎扎进去,可没用了——晓黎的心脏早就停止跳动了,身子都硬了。
这事惊动了营部,毕竟是全营第一个知青出这种事。教导员张孝先挺负责,亲自接待了赶过来的晓黎妈和妹妹晓辉。晓辉跟晓黎长得特像,看见木碑上的字,当场就哭晕了,还是晓黎妈扶着她才站稳。
安葬晓黎那天,张教导员穿得整整齐齐的——正规军的棉衣棉裤,腰上扎着宽宽的武装带,站在雪地里致悼词。他的声音有点哑,念得很庄重:“晓黎是毛主席的好孩子,她听从毛主席的教导,上山下乡,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她是为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献身的……”
晓黎妈当时没哭,就站在那儿听着,直到悼词念完,她才伸手摸了摸木碑,说了句“孩子,委屈你了”。后来晓辉说,那天她妈回到招待所,整整哭了一夜,眼睛都哭肿了。
现在离晓黎走的那年,已经过去五十六年了。小东山的雪还年年下,木碑早就换成了石碑,可知道晓黎故事的人越来越少。有时候我会想,她在地下安息了吗?她是在回北大荒的火车上就下决心走的,还是在连队被人说闲话的时候?她走之前,有没有想过北京的家,想过她妈和妹妹?
这些问题没人能回答。要是晓黎还活着,凭着她的聪明和踏实,说不定早就有了疼她的爱人,可爱的孩子,干着自己喜欢的事。可她啥都没捞着,22岁的年纪,就把生命永远留在了北大荒,一辈子全是遗憾。
咱们活着的人,总说“往前看”,可这些遗憾不该被忘了。记住晓黎的故事,不是为了沉浸在过去的痛苦里,而是想告诉自己:别让那些无意义的压力,逼得人没了退路;别让那些冷漠的眼光,寒了心善的人的情。毕竟,每个人的生命都该被好好对待,不管在哪个年代。
#artContent h1{font-size:16px;font-weight: 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