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驾环游中国之福建省福州市
有些地方你去了,是风景;有些地方,你去了,是一场意难平。福州马江海战纪念馆,大概就是后者。就算你不太懂历史,一推开那扇门,心里也会“咯噔”一下:这里安放着一段国人的难堪、一锅没熬好的血汗,以及若干年挥不散的阴影。说是近代海军纪念专祠,倒像是一面不忍细看的镜子。
很多人提到晚清,总是“唉”上一口气:穷、乱、腐、散,满清后期就像一锅被踢翻的杂碎汤,里面什么都有,什么都不新鲜。街头巷尾的百姓,日子勉强能熬,朝堂上的大人们,却一个比一个能“演”,赔了钱又丧了地,满世界都觉得清国好欺负。你随便翻翻书,有几仗能看?但提到马江海战,老一辈都会摇头,说这仗,打得实在丢人,都不用等甲午海战收场,窝囊事早就摆在台面上了。
那年头的福州,造船厂气派得很——据说在东亚能排头,但命运就是这么捉弄人。马江海战说白了,像是清廷下决心让对方砸个稀巴烂。谁也没料到,开战不到半小时,福建水师就全军覆没,11艘兵舰能浮的都沉了,700多名将士喋血江中。这种败,没什么“过程”,更像突然拉闸断电,把20年心血一夜烧成灰。
你说法国人打这仗,他们也不明白怎么就赢了。原本还准备来一场磨人的硬仗,结果棋还没摆好,仇就报完了,连喊口号都来不及。有人说,这叫“赢得稀里糊涂”,大致说的就是这事。
时间轴定在1884年8月23日上午十点。法国人送来战书,摆明说——我下午两点准时开打,谁也别多说。换个普普通通的国家,估计早就磨刀霍霍准备干架了,但清廷一如既往,能避的就避,能拖的再拖点,最好对方自己打累了就收兵。当天下午,闽浙总督何璟收到法军战书,立马让船政大臣何如璋知会一声。怪就怪在,何如璋这会儿还在想着:是不是能再熬一夜?会不会赶明儿还能和稀泥?他干脆啥都不说,压着不通告张佩纶,所有福建水师将士都一头雾水。
天总归要塌,谁也拦不住。法军不同意拖延,何如璋这才急急转身补了通知。张佩纶拿到消息的时候,兵舰早干不了啥准备。平时号称纪律严明,令下得紧——“敌不火,我不火,谁敢乱动,一刀斩了。”这话有点像打气,但到了真刀真枪,全变成了枷锁:人家打你才还手,这不是稳稳地让敌人占“起手式”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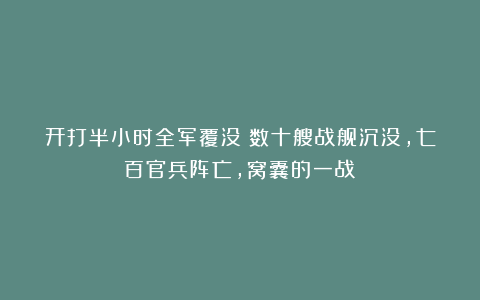
开战时间一点四十五刚到,对面驶来一艘船,法军误以为福建水师要进攻,司令孤拔心里一紧,命令开火。炮声一响,马江海战就此爆发。谁都没想过,忙乱当中半小时而已,什么荣耀、坚持都被炮火搅碎。福建水师是清政府二十年辛苦攒下的“海军种子”,损失在一场来不及谋划的灾难里,人的拼劲再大也逆不了这条江流。700多人,都是带着命上阵,哪怕刀枪拼得满身伤也没法逆天改命。
法军这头倒好,几乎没什么损失——战死人数连个位数都没摸到,有人甚至传说连一具尸体都没留下。这段时间,福州的天都是阴的。哨兵、舰长、工匠,哪怕有不怕死的人,发现局势塌下来,全成了留不住的泡影。
想起张佩纶和何如璋,这俩是典型的“有头没胆”。一开炮就跑,风长雨急,张佩纶甚至冒着暴雨逃了二十里地,身后是战友的鲜血,是岁月的灰烬。曾经是清廷重臣,如今落魄如丧家之犬。不是谁天生胆小,是那时那个朝堂,人人都怕担责任,出了事能躲多远就躲多远。谁都知道,朝廷是能拿你问罪的,但江山的塌陷,又有谁管得了?
一场仗败光了所有海军的底子,还顺手毁掉了福州引以为傲的造船厂。那条江边,后来的回忆都只剩下残兵折将和老百姓唏嘘的碎语。关于马江海战的流言,至今还在福州的大街小巷里有回响。有人说,这场战事从头到尾都透着荒诞,像是庙会搭台,只是最后连戏子都跑了。
纪念馆这地方,讲真——不单单是看展板。山下有昭忠祠,公墓安静藏着阵亡将士的名字,空气里透着点铁锈味,仿佛还没散干净的烟火。旁边的石阶,攀上去能看到梅园、炮台和那栋英国副领事署。每一棵老榕树,都像看尽了几个朝代的风风雨雨,枝桠纠结,一边摇着黄叶,一边替死去的人守着老城的秘密。
教堂立在江边,阳光洒下来像是摸索着往过去里走。你走在那儿,经常会问自己:要是那一仗没那么急,后来的中国海军是不是能多熬几年?那些年头的阵亡官兵,他们到底怎么想的?谁是英雄,谁是逃兵,谁又真正背负了历史的重量?其实谁都没答案,历史的沉重,不归谁一人。
说到底,马江海战不是一个符号,也不是一块碑。它是每一次国人心里的刺,是老福州人茶余饭后的老调重弹,是脚下踩着陷坑还不敢喊疼的隐痛。我们去纪念馆,是在替自己找答案,也是替那些无名的善后者问一句:下次再来,会不会有不一样的结局?
每个人心里都揣着一场未完的马江。这伤,还是要记住,但你要是愿意,就坐在榕树下静一会儿,看看风,想想人,或许能理解什么叫真正的“无力回天”,什么是坚持到最后也毫无结果的人生。历史翻篇了,可遗憾还没走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