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
角 落
唐发忠
(下)
两情相悦
三姑家的鸡汤在砂锅里咕嘟,油花凝成一串串小珍珠浮在水面打转转。
“你表妹考上县中学,配你这军官正好。” 三姑的筷子敲着碗沿说,生怕如意不上心。
他盯着表妹发红的耳根,想起阵地上带刺的野花——青涩,却耐看。
“三姑,我脚伤好点就得归队,前方离不了我……”话没说完,表妹端着碗就跑了,辫梢的红头绳扫过门框,像道被风吹动的火线。
海子叔领来春燕和秋菊那天,太阳毒得能烙化鞋底。春燕初见面直往墙角缩,像躲炮弹的新兵,其实她之前已经见过如意,是在接风宴上。
“姐你咋能这么说!” 秋菊闯进来声音像块石头砸进院子,麻花辫甩得像鞭子,“如意哥的黑是晒的,脚跛是为国家受的伤,这是光荣!” 她仰着脸,下巴抬得老高,像株顶着烈日的向日葵。
如意看清了她眼里的那一抹光——跟他第一次摸到金灿灿的二等功奖章时一样,心里的火苗炽热而向往。
春燕跑后,秋菊从兜里掏出双鞋垫,针脚歪歪扭扭,却绣着山丹丹:“我绣的,别嫌弃。”
红布上的红线有点松,像她发颤的尾音。
如意接时指尖碰着她的手,两人像被烙铁烫了似的缩回去,秋菊的脸红得像山丹丹,转身往柴房躲,辫梢的红布条在门框上晃,留了串细碎的影子。
夜里躺在土炕,娘纳鞋底的“沙沙”声混着山风。“秋菊这姑娘,心正。” 娘的针在头发里抿了抿又说,“前队长媳妇骂咱时,就她敢回嘴。”
如意摸着鞋垫上的花瓣,想起秋菊白天护着自己时,辫子甩动的弧度——多像他接线路时,电缆在空中划过的弧线。
他摸出爹给的那枚钱,“康熙通宝”磨得发亮,边缘用刺刀刻个歪歪扭扭的“信”字。“明天我去找黑驴子。” 土炕“吱呀”响了声。“去干啥?” 娘的线掉在地上。
“告诉他,我孙如意的媳妇,得是秋菊这样的——心亮,骨头硬。”如意知道黑驴子因贪污撤了职已经不是队长了,心里愤愤不已,公开不敢报复,就怕暗里使坏。
第二天,如意在河边堵住洗衣的秋菊。河水哗哗淌着,她抡棒槌的样子像在打信号。
他把铜钱往石头上一放:“我爹给的,戴着能平安。”
秋菊的棒槌顿在半空,水珠顺着布衫往下滴,在石头上洇出小水圈。随即她从怀里摸出个布包,里面是晒干的山丹丹,花瓣脆得像纸片:“我娘说,这花插瓶里能开半年,花瓣儿干了也会香很久。你带着,就当我替你爹娘看着你吧!”
如意把干花塞进军装袋内,贴着心口。秋菊攥着铜钱,指节捏得发白,突然笑了,眼里的光比日头还亮:“我等你回来。教我接电缆线,我也想学咋把两根线接得牢牢的。”
月光漫进窗,照在鞋垫的山丹丹上,红得像阵地上的血。如意摸了摸左脚的绷带,笑了:该归队了,这趟探亲,值!
血染线缆
老山的雨比秦岭的急,砸在钢盔上“噼里啪啦”响,像要把石头敲碎。
孙如意带着通信排守4号阵地,线路在雨林里像蛛网,每寸绝缘皮都浸着雨水和血。
越南鬼子的“飞雷”藏在树杈上,铁皮罐头塞着炸药,细线拴着,风一吹就晃,像山里的蛇,随时吐出最毒的信子。
“排长,3号阵地失联,东边发现断口,像是被剪的!” 小张在电台里发颤,混着电流的滋滋声。
如意抓起工具包冲出去,雨幕把世界揉成模糊的绿。远远望着撑持界墙的水泥柱立在雾里像沉默的哨兵。
如意带着排障小组冲入雨中。
找到了故障区,断口的铜线泡在泥水里,闪着冷光。
他让战士们退后,自己踩着没膝的泥泞挪行,左脚旧伤在湿坡上拧了下,疼得他龇牙——像秋菊洗衣时,棒槌砸在石头上的那一下,震得心口发慌。
“小心树上!” 喊声未落,他看见榕树枝上的铁皮罐头,正冒着青烟。
他推开新兵小张,自己往旁边一扑,可爆炸比动作快。“轰隆”一声,热浪掀得他飞出去老远,耳朵里只剩下嗡鸣,像无数只蝉在叫。
醒来时躺在临时担架上,血顺着裤腿滴,染红了绑担架的青竹竿。右手攥得死紧,摊开一看,是那枚铜钱,红布浸成黑紫色,粘着老山的泥土。
“别睡!” 耳边有人喊,是小赵?不对,小赵昨天已经在排查线路时被流弹击中,牺牲了……他想睁眼,眼皮重得像压了块石头。
“如意哥!” 这声音脆生生的,像秋菊在河边捶衣裳,恍惚向他奔过来,“如意哥……”再后来,他睡着了……
三天后,在战地医院的手术台上,他最后一次醒来,扯了扯嘴角想说“铜钱还在,山丹丹花瓣儿也还在内袋里,可他咋也发不出一个字的内容,喉咙里却只“嗬嗬”的响……
野战医院的白床单覆盖着如意的脸,血花从绷带里渗出来,慢慢洇开,像极了秋菊绣的山丹丹,在老山阵地上开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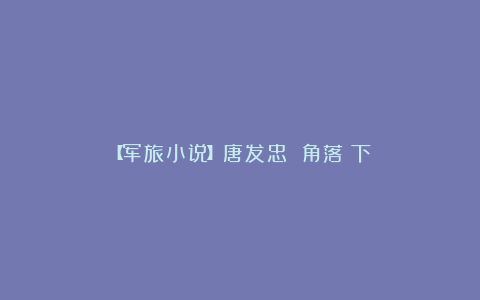
接枪妹妹
秋菊赶到老山前沿阵地时,如意的坟刚用碎石垒好,碑上的名字刻了一半,“孙”字的最后一笔还留着新鲜的凿痕,刻字的凿子插在旁边土里,沾着石末,像他没说完的话。
通信班长王强递来个布包:染血的铜钱裹在红布里,旁边是半截鞋垫——鞋垫上绣着两只鸽子,一只翅膀已绣好,另一只刚起针未完成。
“排长牺牲前把断线接上了。”王强抹着泪说,“线路通了,我们的炮群要反击了!”
远处传来雷鸣般的轰鸣,我方加农炮群开始怒吼。火光在雨雾里炸开,像无数朵山丹丹在黑夜绽放。
秋菊攥着胸前的铜钱(她用红绳串了,贴身戴着),指节按着自己的心跳——原来炮声的节奏,和如意接电缆时的呼吸声一个频率。
她没哭,她眼泪早变成了炮弹出膛的火。
作为“接枪妹”,她已通过正规程序通过了入伍手续,成了战地医院的一名护士,白大褂上的血渍总洗得最干净,她总说“如意哥的电缆要接得干净,咱的伤口也要处理得干干净净”,像要把这种殷红酿成反击的力量。
有次炮弹在附近炸响,她抱着药箱往防空洞冲,裤脚被弹片划破,露出里面的红布条——从如意军裤上拆的,缝在自己裤腰里。
“你不怕吗?” 护士长问。“不怕!”秋菊边摇头边给伤员换药,镊子捏着棉球,动作稳得像绣花:“俺是替如意哥来的,通信兵的线不断,俺的脚步就不能停。”
深夜值岗,她总坐在电台旁,听“滋滋”的电流声里传递着各种指令:“左翼炮群转移至3号地区”。那声音像秦岭的风,像如意走时的脚步声,像那只没绣完的鸽子,在心里扑棱着翅膀。
那天清晨,阳光穿透雨雾,通信排的兵欢呼:“反击成功!拿下高地了!” 秋菊站在山坡上,看信号弹在蓝天下炸开,红的,绿的,像她给如意扎的麻花辫梢。
她摸了摸胸前的铜钱,突然笑了。两个角落的距离,从来不是山路和炮火,是有人用命连着,用念想牵着。这铜钱,一面粘着秦岭的土,一面沾着老山的血,却把两个名字,磨成了同一个印记。
转业那年,秋菊把铜钱串得更结实了。护士长劝她去军区医院,她摇头:“我想去地方医院,离群众近,离家近。” 是啊,最要紧的阵地,不在高台上,而是在不起眼的角落。
坚守角落
秋菊走出市医院大门时,风裹着尘土往脸上扑。人事科那句“只会往伤口上撒消炎粉”的鄙夷的话还在耳边打转。
她摸了摸胸前的三等功奖章,金属的凉意顺着指尖往心里钻——忽然就想起如意临走前说的,“咱从秦岭的山角落出来,到云南老山守猫耳洞,哪儿的角落不是守?”
其实能在显眼的位置都是一种炫耀,社会的基石乃至人生的支撑点都在千千万万个不被人们重视的角落。
社区门诊的门是两扇掉漆的木门,推开时“吱呀”一声响。
老李正坐在门槛上擦听诊器,右腿伸直了搭在砖头上似有不适的僵硬感。“我当年在广西谅山前线当卫生员,突击队冲山头时,弹片炸进我腿里,也是在临时掩体里用消炎粉止的血。”
老李没抬头,却像猜透了她的心思,“老山的猫耳洞、谅山的掩体,再到咱这社区门诊,角落不分大小,能照见人就行。”
秋菊放下帆布包,突然看见墙上贴着张旧报纸,上面印着老山阵地的照片——猫耳洞前的电缆线拉得笔直,像道发光的线。
她忽然想起如意探亲时给她讲自己在读军校时,常常一个人很晚独坐在校园的白杨树下想起“家”的那个角落,说真想回去看一眼就走。可肩上的使命让他必须先去守护好国门的那个大“角落”。
他还说:“等边境安静了,我回来和你一起再守好咱家这个小’角落’”。可他没等到那一天,只留下那一枚刻着“信”字的铜钱和一句朴实无华的金子般的承诺。而这句承诺让她坚守这一生。
街坊们起初对她有点生分。王大妈是社区里的老住户,儿子在工厂当干部,第一次来门诊拿降压药时瞅着秋菊的军装皱了皱眉:“听说你从大医院下来的?咋不去外科做手术,来咱这给人量血压?”秋菊没辩解,只帮她把药盒上的服用说明用大字抄了张纸条,又提醒“最近降温,出门记得戴帽子”。
张大爷起初总绕路去市医院拿药,后来一次雨天发烧,秋菊冒雨上门送药,他才改来社区门诊。后来王大妈的老伴半夜突发心梗,秋菊背着老人往市医院跑,老李骑着破自行车跟在后面,腿一瘸一拐的,却把急救包护得紧紧的——打那以后,王大妈总往门诊送自己腌的咸菜,说“秋菊这姑娘,比亲闺女还贴心”。
“你说咱这门诊,像不像老山的通信站?”有天值夜班的老李忽然开口,手里擦着那把用了十年的止血钳,“如意在老山守着电话线,咱在这儿守着街坊的健康,都是把’线’往稳里接。”
秋菊望着窗外的路灯,光透过树影洒进来,在地上拼出细碎的亮——她又想起村口的老槐树,树影落在地上时,像如意当年画的线路图,歪歪扭扭却连得紧实。
她忽然懂了,如意从秦岭山角落到云南前线猫耳洞,从军校白杨树下到老山界碑,从没逛过都市的霓虹,却把每个角落都照得发光;如今她守着这城市的角落,有暖炕,有热水,有街坊的热乎话,够幸福了。
转年春天,市医院来人考察,看见秋菊给老人量血压时先焐热听诊器,老李帮独居的张大爷修水管,临走时叹道:“这俩老兵,把角落守成了群众的暖窝窝。”
秋菊送他们出门时,看见门诊门口的花坛上,不知谁摆了盆山丹丹,红得像团火——跟如意墓前的花,一模一样。
尾声
中秋节的月亮格外圆,把山路铺得像落了一层银霜。
秋菊和老李拎着网兜往山坳走,里面的月饼香混着苹果的甜,飘在风里。
路过村口的老银杏树时,秋菊忽然停下脚步,想起如意归队和她告别时就是在这树下,背着迷彩图案的战地作业帆布包,用手掠过她的头发,说“我去守祖国的那个大角落,你们守家里的小角落”。
“爹,妈,我们来啦。”推开柴门,如意爹正坐在门槛上编竹筐,竹条在手里转着圈,像如意当年绕电缆的样子。妈从灶房出来,手里端着碗热粥,说:“知道你们要来,特意熬了小米粥,跟你们社区门诊街边的粥一个味儿。”
吃饭时,妈摸着秋菊的手说:“当年如意在老山猫耳洞里连口热粥都喝不上,现在你们在城里,能守着暖乎乎的门诊,真好。”
老李放下筷子,从兜里掏出个小本子,里面夹着张老照片——是他在广西谅山前线时拍的,背景里能看见临时救护所的帐篷,还有面飘着的红十字旗。“我跟如意虽不在一个战场,却都懂’守角落’的滋味,现在咱把社区的’线’接牢了,他也能放心了。”
.夜深了,秋菊帮妈收拾碗筷,看见柜顶上摆着个铁皮盒,里面放着如意的二等功喜报,旁边压着她和老李的三等功奖章。月光从窗棂照进来,落在喜报上的“孙如意”三个字上,亮得像颗星。她忽然想起在社区门诊时,常跟街坊们说的:“咱这角落不大,却比啥都金贵——如意守过的老山角落,老李守过的谅山角落,咱得接着守,还得守得更暖。”
下山时,老李忽然说:“明年开春,把爹和妈接到城里吧,门诊旁边有空房,能种山丹丹,也能编竹筐。”
秋菊点点头,挽住他的胳膊,感觉他的手暖暖的——风从山坳里吹过来,带着桂花香,远处城市的灯火亮得像片星海,而他们守着的角落,就是这星海里最暖的那盏灯。
完稿于2025.2.郧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