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森氏·晓人”案件及原始资料之鉴定与处理
李 济
1929年秋殷墟第三次发掘,李济手持彩陶片
编者按
近期青海扎陵湖畔发现的“秦代石刻”,在学界引发广泛争议。信真和疑伪的双方学者,基于各自的学科背景各有举证,或补苴罅漏,或指瑕攻错,迄无定论。而不论具体结果如何,这种学理性的讨论本身就益人神智不浅。
事实上,此类带有传奇色彩材料的发现,在古今中外都发生过多次(如“坎曼尔诗签”、“耶稣之妻福音书”、“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光明之城》、“靖藏本《石头记》批语”等等)。尘埃落定之后,往往能在方法论和学术史层面催发精彩的讨论。
其中,李济《论“道森氏·晓人”案件及原始资料之鉴定与处理》一文值得一读。作者是中国现代考古学史上具有开辟意义的人物。文章依据西方学者的发现,对事件本身有清晰的梳理,同时结合中国学界情形,对于原始资料的等级与效力、研究者难以逃避的学术和时代风气影响、材料性质与意图解决的问题之关系等关键问题,均有透辟的反思。因转录如下,或许能为方兴未艾的学术讨论,提供一些“前车之鉴”。
文章原载台北《现代学术季刊》1957年2月第1卷第2期,粗体字为公众号编者所加。
英国是进化论学说的老家。也许就是这个缘故,一件有关进化论的人造化石轻轻地欺骗了英国最前线的人类学家、古生物学家、地质学家、考古学家以及他国在这几门科学的最高权威——欺骗了他们前后四十年。这一骗案出现在英国本土;人造的化石是百分之百的英国制造。案子正式开始在一九一三年,正式结束在一九五三年:前后恰为四十年。案情大致如下。
一九一三年出版的《伦敦地质学会季刊》,载了下译的一段科学新闻:
若干年前(一九〇八年),我在閟尔当附近的农场散步,看见补修路面的石子中,有甚为别致的棕色燧石,是在附近区域所不常见的。但探寻的结果,知道这些石子,就是从这一农场地面下的砾石层中掘出;这使我甚感惊异。不久我就追踪到出这种石子的地方访察了一次,正碰见两个工人在掘石子补路。发掘的地点,北出所知道的燧石矿层边界约四英里。此一发见鼓起了我很大的兴趣,因此就作了一番更切近的考察。我问作工的人们曾否看见过骨殖或化石一类的东西;他们似乎没注意到。我乃拜托他们;假如有这一类的发现,把它们妥为保存。以后常往访问,有一次一位工人就递给了我一小块很厚的、属于人的颅顶骨;随着我就在当地搜寻了一次,没有收获,工人们也没有看见另外的骨头。……以后又陆续访问了好些回,再也没听到新发现。此处的地层,似乎不出什么化石。好几年后,一九一一年的秋天,再游这一地方,我在那雨水冲刷过的、翻过的砾石堆里,却检出来了一块较大的、属于(与头一次得到的颅顶骨)同一头骨的前额骨:包括一部分左眼眶上的眶上脊……。
译自Quarterly Journal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 1913, Vol. 69, pp. 117-
又见Arthur Keith: Antiquity of Man, 1925, Vol II, p. 491转引。
上文的作者为:查尔斯·道森(Charles Dawson),他是一位业馀的古生物学家,他的本行是法律;他酷好古生物学,对于地质学、考古学更有兴趣。根据上述的及继续的发现,道森氏的老友、大不列颠博物馆的古生物学主任研究员,斯密士·伍德瓦德(Smith Woodward),把人骨的部分作了一次彻底的检察:全部资料包括九碎块头顶骨,一残块下颚骨。头顶骨最不寻常的部分是那特大的厚度——八至十二公厘。残阙的下颚骨仍带有第一、第二臼齿:它的形状、大小,肌肉生根处的纠结与沟脊,全形的曲度及结构——这些形态都个别地加了详细的研究。伍德瓦德的结论是:
头顶骨重要处皆是人形。下颚骨似属于一个猿的,所具有的一切形态,除了臼齿外,没有可以列入人形的。
J. S. Weiner: The Piltdown Forgery,p. 5
这一初步结论的含意最重要的而予人印象最深的是这一化石人所代表的品种:头顶已取得人形,但仍传有猿形的若干痕记;下颚虽保持完全的猿形,所装载的大牙却表现了人式的咀嚼磨搽面。这一介乎人猿之间的体形凑合,恰恰地暗符了主持进化论学者的一种长期的愿望。猿与人之间,似乎必须出现此一体形,方能充实生物进化论的理想论证。因此,当时英国自然科学界的重镇,除了大卫·瓦特斯顿(David Waterston)外,如伊里约·斯密士(Elliot Smith)、阿瑟·吉士(Arthur Keith)、杜克威士(W. L. H. Duckworth)、梭拉斯(W. J. Sollas)等,都很热烈地欢迎了这一新人形种属;伍德瓦德命名的“道森氏·晓人”遂正式排入人类宗祠里的祖宗灵位了。
“晓人”的下颚骨及臼齿
(Natural History Museum, London)
配合了并加强了这一初步结论其他的论证,为古生物的、地质的,以及考古的若干观察与发现;这些发现大半都由道森氏得来,它们奠定了晓人(俗名:閟尔当人)的年岁计算的基础。属于这两[三]门的主要证据为:
(一)地质方面的:出晓人的地层,在砾石层的最下面,砾石层是更新统冰川时代冲积成的。
(二)古生物的标本有河马、鹿、獭、马骨;又有更老的古象及犀牛的遗存。有些化石,道森认为与晓人同时,有些,也许比晓人更早。
(三)考古学的证据为若干早期的旧石器及更老的晓石器出现,并有一件古象的腿骨制成的骨器。
但是,自从道森于一九一六年去世后,别的科学家在这一地方的搜寻,都失败了;直到一九五〇年的时候,还有一次大规模的发掘在閟尔当附近一砾石台地进行,移动了成吨的土方,所有的土方均经铁筛滤过,却没有寻出任何人工遗存或化石。
自一九一三年后,四十年间,讲进化论的书籍论文中,道森氏·晓人所占的地位,比出土较早的爪哇猿人,引起了更大的注意;因为大多数的权威学者都承认晓人的时代在更新统的早期,而他的脑容量已发展到与现代人相等——一三五八立方公分(参阅E. A. Hooton: Up from the Ape, 1949, p. 309),认为同出土的石器与骨器,证明晓人已经有了文化。这几点,在这一个时期构成了人类学家一般的信仰了。虽说是与头骨相配的下颚骨不断地使专门研究人类进化的学者提出疑问,这些疑问对于晓人在进化论的地位并没发生摇动。例如,以研究北京人出名的魏敦瑞博士(Dr. Franz Weidenreich)在一九四五年对此表示过一次意见;他说:
自从閟尔当人发现以后,凡是所知道的与早期人类有关的事实,均证明“人”不可能有一个带着猿形下颚骨的老祖宗;……发现的事实却是相反的:人形的下颚骨与人形的牙齿配合在保持着猿形品质的头骨下,却是常有的。
Franz Weidenreich: Apes, Giants and Man, 1945, pp. 22–23
但在一九四六年改版的《由猿上陞》(Up from the Ape)一书中,哈佛大学的虎藤教授(E A. Hooton)仍坚信英国学者复原的晓人是没有重大错误的;该书第三一一页有一段此类的辩论,今节译如下:
……有些人以为閟尔当人的头骨与下颚骨原属于两种不同的动物:下颚是猩猩的或黑猩猩的,头盖骨是人的。这是根据着一种错误的人类进化观念得出的结论。进化并不是一个机体的各部分之平均发展:它是跳动的,不对称的演变。人的身体,有些部分,如上肢,仍保持着爬虫的形态;别的部分,如下肢,在演化中却很快地变了形:适应新的环境,发生新的功能。人的身体好像一座常加革新的古老房屋似的,有些因为事实上的需要全改革了,有的扩大了,有的装了电灯,加了抽水马桶,有的保持原样……
虎藤教授如此比喻人类的身体,大致是不错的;但是用在头盖骨与下颚骨的部分却不十分适当。不过这一说法足可代表英美的人类学家大多数的意见。除了少数的专家外,道森氏·晓人在一九四六年前后所享受的信托仍有点像华盛顿发行的美国钞票一样。
事情的转变开始于一九四八年。
一九四八年十月,古生物学家用以测量古生物化石年代的新方法——氟量测验(Fluorine Test)——第一次用到閟尔当发现的化石人骨上。以氟量测验法断定化石年代在法国开始较早;这一实验的根据为埋在地下的骨骼吸收地下氟质的情状:埋藏年岁愈久,骨殖内吸收的氟量愈多。法国的矿学家加诺氏(Carnot),就他研究所得,曾编成一表如下:
上表见:Ruth Moore: Man, Time and Fossils, 1954, p.306
继续的实验证明这一现象大有区域的差异:埋在地下的生物骨殖吸收氟质的多寡,要看所在地氟质的储量:储量多,吸收就多,储量少,吸收亦少。此外又要看各种骨殖在地下的结合状态,有的利于此项吸收,吸收率快;不利于此项吸收的,吸收率亦递减。因此单独靠化石中所吸氟量,并不能断定它的相对的年龄。但是,出于同一地点埋藏情形相似的化石,氟量与结合状态既无差异,若是有时代的不同,这一不同的程度即可由各标本所包含的氟量检定出来。与最后这一点有关实验的完成,大半是英国的地质人类学家峨克莱博士(Dr. K. P. Oakley)的工作。
峨克莱的实验成功后,大不列颠博物馆的负责人乃允许他检查道森氏·晓人各化石标本包含的氟量。由此一检查所得的发现,最重要者可以分两层说。
(一)晓人的头顶骨与晓人的下颚骨所吸收的氟量完全不等。不但如此,两部分的骨殖所含的其他化学成分如淡气(N)、炭素(C)、水分、硫酸盐等,互相比较,均相差甚大。这些成分在枯骨中的含量都具有时代的意义;根据这几方面检查的结果论断,认为是晓人下颚骨的时代与新近埋在地下的骨殖没有什么可以称述的分别;头顶骨的部分所含的各种化学成分,只能与新石器时代埋藏的生物骨骼相比。由此计算,四十年来在各种书刊中习常看见的现代人类的最早祖先、晓人的面貌,所根据的复原资料,至少有两种不同的来源;两种的时代都不能到达如道森氏及英国的几位大权威所标榜的岁数。
(二)再从别的方面检查晓人的头顶骨部分,更发现这一部分是陆陆续续地杂凑起来的一件赝品;道森的关于这些骨块的报道几乎无一可信。新的检查发现了:(甲)出晓人的顶盖骨之砾石层,经过几次重掘,没有独立地出现过任何化石;砾石层内的化学状况,并不宜保存骨殖。(乙)头顶骨的氟量虽比下颚骨的较高;但若照一般所估计的年岁,所在的砾石层可以供给的氟量应远比所包含者多多。(丙)头顶骨的颜色曾经人工加以铁质颜色的涂抹。(丁)道森氏自己的记录没有任何部分可以证明,他检取的这些骨块是由没有经过搅乱的地层掘得的。(戊)与晓人的头顶骨含有同量氟质的河马化石,亦经证明由他处搬来,表面加了有铁与克罗米成分的颜料涂抹;所以决不是閟尔当地方的原藏。
以上两段参阅J. S. Weiner: The Piltdown Forgery, pp.189–205
自从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克拉克、魏纳、峨克莱三氏的联合报告发表后,晓人的案件可以说告了一个结束;这一报告澄清了四十年来讨论人类进化问题一层最大的障碍。这一伪件——一具假古董之王,所遭塌[糟蹋]的全世界知识阶级的精力与时间是一种无法计算的损失。作者的业师、哈佛大学的教授虎藤先生,由于他早年所受的牛津大学的教育,向来是笃信晓人真实性的一位肫挚的科学家。晓人的伪装揭晓时,他尚健在。当时有一位报馆的记者去访问他的意见,只得了他一句话。他说:“这好像有人向他[我]报告,美国通行的华盛顿发行的钞票是假造的!”作者一九五四年访问剑桥时,他老先生已归道山,就没得机会与他谈此案件。那时有的同学告诉作者,虎藤先生的逝世,与这一案件有些关系;他为这一事精神上所受的打击极大,这是上了年岁的人难加支持的一件事。
Earnest A. Hooton (1887–1954)
这一件假古董之王的出现,照已经揭穿的事实看来,确实经过了一番最缜密的布置与计划,所以能把当代若干最有经验的科学头脑哄骗了四十年;这真是:“君子可欺以其方”了。不过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骗案;这一案的经过实在可以给予从事自然科学以及人文科学工作的人们几种严厉的教训。现在可以从三方面讨论此案的教训:(一)此案的造成以及取信一时的缘因;(二)所引起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原始资料之鉴定与处理的问题;(三)可以供史学家参考的地方。
(一)晓人案的造成以及取信一时的缘因
魏勒氏分析此案的经过,以为这一伪装的人类祖先所以得到初期成功最大的缘因,是那时的科学界对于人类早期的发展留存在地下的证据有一种期待。这一期待因爪哇猿人的发现而更加强。廿世纪的初期,英国的生物界都熟悉达尔文、赫胥黎诸先进对于早期人类的可能形态说的预言,一旦真有近似这形态的化石人出现,真要使研究人类原始的科学家喜欢得手舞足蹈了。于是迫不及待地,不管他的籍贯族望门阀世系,大家都争前与他握手认亲。
The London “Bone Trust,” England’s most eminent anthropologists plus Dawson (second from right in the rear), admiring a re-assembled Piltdown skull, painting by John Cooke, 1915 (Ge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 via Science magazine)
阿塞·吉士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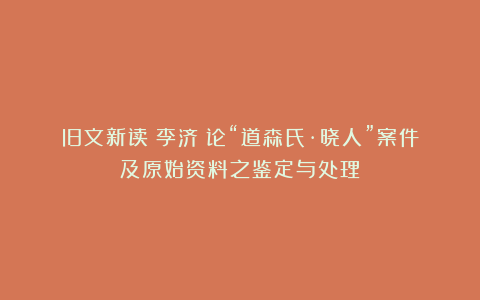
迟早我们总要发现像閟尔当人这一种人的!自从达尔文后,这是人类学家信仰中的一条信条。
(Arthur Keith: Antiquity of Man, 1925, p.667)
杜克威士说:
从解剖学上说,閟尔当人的头骨,把研究人类进化的学者们所期待的实现了。
(W. L. H. Duckworth: In Discussion to Dawson and Woodward, 1913, p.149)
梭拉斯说:
在道森氏·晓人的体质中,我们似乎实现了一种已经修到了人的智力,但尚没完全失去更早祖先所具的下颚骨及战斗犬齿的一位生灵。
(W. J. Sollas: Ancient Hunters, 1924, 3rd. ed.)
伊里约·斯密士说:
晓人的脑内模是所发现的人脑型最原始的最像猿形的。
在这四位权威学者领导之下,关于晓人的科学意见差不多近于统一了。与他们意见不同的,如大卫·瓦特斯顿的见解因此就没没无闻。这四位大权威固然脱不了疏忽、蔽于若干偏见的责任,但他们都是君子人,说的都是真话。同时主持这一喜剧的内幕人物——现在大家已共认是道森本人——他的手段确实高妙。譬如晓人复原所根据的原始资料,大半都由道森氏经手发现,但是他的记录既不完备,他很早就顾及到由他经手取得的此项资料的手续,可能引起外界的疑心。因此,他就把此组资料中几件极重要的项目,借重到场参观的另外一位科学家而问世。那时法国籍的德日进神甫——自民国十二年后,在中国工作了廿馀年,对于远东区域古生物研究有极大贡献的一位卓越的古生物学家——正在英国进修,碰上了“晓人”的诞生典礼。对于这一重要“发现”,一位青年的古生物学者如德日进神甫当然要发生绝大的兴趣。得了道森氏的允许以后,并经他的邀请,德日进神甫在晓人出现的地带“发见”了:古象齿一件、E字六零六号石器一件;并在一九一三年八月卅日发见了晓人的犬齿。最后的这一发现,是德日进神甫应道森氏的邀请而得到的;此一工作帮助他成了大名。但是最近重新检查的结果证明:古象齿是由非洲突利西亚(Tunisia)输入英国的标本;E字六零六号石器,曾经涂过含有克罗米成分的颜色,也不是閟尔当本地的产品。至于那更重要的、点睛的发现——一枚犬齿咧,据过去的记录,伍德瓦德在晓人的犬齿出土六个月以前曾替它作了一个预测的模型,而德日进神甫的发现差不多与模型完全一样。伪犬齿的原形是一颗年轻的尚未长成的标本,但是外表的用痕却显示了广大的且紧迫的磨擦;这是与自然情形最相乖违的部分。所以,假手德日进神甫问世的三件与晓人有关的证据,已经证明件件是假——假件造好了,埋藏在閟尔当附近的地方再由造假的人约请他去表演一番发现的工作。这一幕戏剧演得如此精采,当时的科学界也就很容易地被瞒过了!
德日进(Teilhard de Chardin,1881—1955)
来华期间和胡适有交往
晓人享受的信誉,不但有早期进化论学说的支持,很显然地还有若干感情的成分在内。分析本世纪初期世界学术的风气,英国没有疑问地是生物研究的中心。这一事实,英国科学家感觉得尤为敏锐。他们自己有此感觉,别国的科学家也尊重他们的这一感觉。晓人的出现,可以证明最大头脑的人类,最早生在英国;换过来说,最早的英国人也是现代人类最早的祖先。这一有生物学根据的事件所给予英国人的下意识的满足,可以与“大英帝国国旗飘扬处太阳永不没落”所给予的是一样的。由此,大英帝国人之领导人群的地位可以说是由于生理的禀赋了。英国科学家接受晓人证据的轻易态度与过分的热烈大半可以由潜伏在他们的下意识内的这一情绪解释。
(二)本案引起的原始资料之鉴定问题
“原姓[始]资料”可以说是作现代学术工作的人们所追求的第一对象;不少的成名的学者,成名的凭藉就靠着一批别人没有的资料。不过原始资料的价值,显然也是有等级的;等级类别的标准固然没有定说,它们的存在却可以由资料本身出现的情形与取得的手续看出。若将北京人与閟尔当人(即晓人)两件举世皆知的发现作一比较,专就出现的情形说,两组资料已有很大的分别。构成閟尔当人的形态及年岁的原始资料经过了最近的一次检查发表后,都知道是一件假古董,但在五年以前大家尚不信此说;因此这一名贵标本伪装的暴露,科学家都要归功于研究方法的进步——如氟量的检定、氮量的检定、X光线更精密的检查方法:这些当然都是事实。不过,要是回顾閟尔当人取得的手续,照考古学建立的标准说,这类资料的品质,尚够不上第三等的资格,因为它们没有:(一)准确的出土的记录;(二)没有正面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些实物与土层的直接关系;(三)第三者在该处发掘,不能证明所说的出土地层有出此类化石的可能。北京人的原始资料,从最早的一批起,即保有准确的田野记录;所出的大量化石,莫不有本有原,各有其原在地点及同层出品。故两组资料有关本身之报道,详略程度相差之距离甚远,其品质之高下亦可由此衡量。魏敦瑞所写关于北京人研究之报告,出版已逾十年,其资料之真实性与可靠性,无人提出疑问。
閟尔当人所以能成为一大骗案,若略加分析,作伪者之存心玩弄科学界尚是次义,只负一小部分责任;大半的责任实应由当时的几位权威学者担负,因为他们忽视了那时古生物学家及考古家已经建立的科学水准,忘记了閟尔当人这批资料甚低的品质及可靠性,他们所作的解释及推论都超过了逻辑的范围。照田野工作的习惯,像閟尔当人的复原所依据的几块碎骨用着拼凑工作,像斗七巧图似的,自无不可;但是用这些基础不稳定的复原标本,进一步地讨论人类进化的大问题,实在有欠斟酌。这类大问题的基础,只有第一等的原始资料方能负荷那建筑的重任。
所谓第一等资料者,若专就考古这门学问说,至少应该具有北京人那批资料的品质:为一有计划的发掘,有详细的地下情形之记录的资料。但是这一类资料虽是人人可以寻找的,并不是人人能有机会得到的,而田野工作很显然也只是少数人的专门职业。故考古家,同别种科学家一样,在进行他的研究工作中,不断地要采用品质庞杂的资料,其中大半是第二手或第三手货。这些二转三转的材料,却往往具有极高的品质,能否尽量发挥它们的内涵,就要看用的人眼力了。此处可以举中国药材店的龙骨为例说明此一意义。
中国药材里有龙骨一味,照中医的想法,可以治若干疑难病症,古生物学家对它们都[却]另有一种意见。他们从药材店里储藏的龙骨中可以寻出非常重要的及非常有趣的古生物的原始资料,并可以找出古代人类的化石。北京人的发现,最早的朕兆就是从中药店所采的龙骨中露出来的。最近十馀年香港的中国药材店又出现了同等宝贵的类似资料。对于它们的鉴定工作可以从两方面考虑:一为实物本身,一为鉴定人的心理背景。实物本身(假定它确是真实可靠的),固具有不同等的科学价值,反映出来的意见所具的学术意义,也可能有很多不同的等级。同是龙骨,中医对于它的意见与古生物学家对于它的意见相比,完全是两个境界。古生物学家在龙骨中所能发现的学术资料又要看有关它们来源的纪录而分等级;如下列各例:
(一)来源不分明的:例,香港药材店里巨人臼齿。
(二)采集范围可以说明,地点不能确定:例,河套人的门牙。
(三)有采集地点但地下情形不能说明:例,爪哇猿人。
(四)科学方法发掘出来的:例,周口店的发掘品。
(五)上项采集品中的新发见:例,北京人的头骨。
上列五例完全由它们的原在情形见于纪录的而分等级,由此归纳出来的一个原则是:关于它们的身份可靠的纪录愈多,所具的科学价值也愈高。故香港药材店的巨人白齿,只能供形态的比较研究,河套人的门牙已有地域上的联系,可以用着作进一步的推论了。若爪哇猿人,因为与若干其他的古生物有了亲切的关联,更具有一种对于猿人的生存时代讨论的根据。周口店的发掘纪录,连北京人的文化阶段,都能加以确切的判断。
由此一比较可以看出原始资料的学术价值并不完全附丽于资料的本身,也不全靠工作人的搜寻能力;这里有些机遇的成分,可以触成若干资料在科学研究中的特别用处。但是,因为工作人的低能,头等的资料降为三等以至于完全无用的例却是太多了,太普遍了。一般地说来,所有古董商经手的古物都属于这一类的例。但古董商同药材商人一样,本是与学术无关的企业,是不能以学术标准苛责的。最可惋惜的还是以学术相标榜的一部分职业收藏家的若干习惯。譬如广泛地搜索有文字的器物(墓志铭)而毁坏无文字的器物(全部墓葬的内容),如高昌墓砖作者的行为,结果只是把大量宝贵的原始资料化成毫无价值的废物。
构成原始资料的重要因素,至少有一部分应该在研究人的思想程序中寻找。蒐集资料的人有一个问题在心中盘旋,碰见了一批东西,使他感觉到这批东西可以帮助他解决这一问题;于是这批东西对于他就发生价值了。要是这批东西未经人用过,它的价值将更加提高。由于知识阶级接受了进化论,古生物留在地下的骨骸都成为研究进化学说的资料;这些资料也就取得了学术的价值。对于进化论不感觉兴趣的人当然也就看不出它们的学术价值,只把它们当着龙骨看待。不过这究竟只是这一问题的片面;资料的本身仍是构成资料价值的核心,也是科学研究的出发点。这一点颇有可以与实验室所得的资料相比处。以实验室的资料论,固然皆开始于实验者怀抱的问题、构思的计划,但其所追求的现象,要无客观性的存在,设计无论如何巧妙,实验是得不出结果的。实验室取得的资料,是人人在同一情形下,可以覆按的:若其是真,反对者不能使之永久湮没;若是不真,迷信者不能使之永不暴露;就是实验者自己的催眠,也不能长期欺骗自己。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领域内,资料的客观价值虽同样地存在,本身的性质与实验所得的却完全两样,而一经毁灭即永久毁灭。閟尔当人的资料,若同北京人的一样,在战时失踪,他的真相就不会暴露了;他的真伪或将成一永久问题。不过这儿仍有一个限度。怀疑晓人的真实性,很早就存在若干科学家的心中;早期因为这一态度有违时代的风气,就没得发挥适当的作用。近三十馀年,北京人、爪哇猿人以及南方人猿的新发现证明初期人类进化所循的路线是一种与晓人所代表的完全相反的方向。这些新资料研究的结果使晓人这副嘴脸在理论上已渐渐地没有存在的可能。所以,就是与晓人有关的原始资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完全毁灭了,他的真面目不能用科学方法揭穿,他的地位与重量也要与时俱灭以至于无的。
(三)可以供史学家参考的地方
将近三十年前,傅斯年先生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时,发了一个宏愿,他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见《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第十页。民国十七年十月刊印)。他在战前的努力都循着这一方向;不幸八年的抗战把他壮年的精力,大半浪费在消极的方面,但他所建筑的这一基础直到现在仍为史学家所重视。经过了这一长期的考验,现在可以检讨一次他所许的这一宏愿,理论上的根据是否稳定了?
1936年5月殷墟第三次发掘,傅斯年、伯希和与梁思永
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具有可以讨论的两层意义:第一层:是问题应如何开始,第二层:是资料如何蒐求;两层的关联虽是密切,仍可分开讨论。生物学与地质学的一般背景及所包括的范围都没有区域的限制,若要把历史学以及语言学建设得和它们一样,意思是否要把传统的夷夏的界线与中西的界线完全取消咧?取消了这些疆界,代替的应该是什么?对于最后这一问的答案,可以说是全部人类文化史的背景。以全部人类文化史为背景建设中国的历史学,不但是一个新的观点,更是一个蒐求历史资料的新路线。由这一看法到达的第一个境界就是地质学家丁文江先生告诉他的朋友的话,他说:“中国境内作现代学术工作,真是遍地是黄金,只要有人拣。”这话并不是单就地质学的立场为地质学说话;他的话也是为从事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语言学的工作大众说的。若把中国历史当着尧舜以后人类堕落的故事说,或当着周而复始的循环故事说,一部廿五史已说得淋漓尽致了!现代史学家可作的工作范围是很窄狭的;可用的资料也就大有限度。若把中国历史当着全人类历史的一部分处理,就是垃圾堆里也可以找出宝贵的资料出来——由一堆枯骨、一片破陶、一块木炭到最完整的钟鼎彝器,由最落后的区域的陋俗到最崇高社会的礼节,由穷乡僻壤乡人的土语到最时髦社会的演说词——这些都成了史学家的原始资料。
大部分的史学家现在已接受这一观点了,从这一方面蒐求材料的结果已有若干成绩可以列举出来。譬如:民国十二年的时候,胡适之尚向顾颉刚说:“发现渑池石器时代文化的安特森,近疑商代犹是石器时代的晚期(新石器时代),我想他的假定颇近是。”(见《古史辩[辨]》第一册二〇〇页)现在没有人再说商朝是石器时代;因为从垃圾堆内寻找史料的工作人们已经寻出不少的确实可靠的商代青铜器。
废墟中蕴藏的固有黄金,但也不尽是黄金;这拣取的工作是十分艰难的。所需要的工作条件应该以自己动手动脚为第一义。有了这类工作经验的人们都知道:同是资料,而以亲眼看见的为更可信赖;同是看见的,又以自己找出来的更可鼓舞研究的兴趣。所以新史学的第二境界可以说是“百闻不如一见,靠别人不如靠自己”。
资料与人接触之间,永远是一件事情的两面:一面在人,一面在物。资料能否取得人的信赖,是物的品质问题,人肯不肯信托自己所见及所得的资料,是人的见解问题。两面接触的结果,经常有下列的四类可能:
(甲)资料是真的,人亦信是真的:如法国南部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洞穴壁画;居延出土的汉简。
(乙)资料是真的,而人不信是真的:如章太炎之对甲骨文字。
(丙)资料是假的,而人信是真的:如一九五三年以前,人类学家之对晓人;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以前,中国读书人之对古文《尚书》。
(丁)资料是假的,人亦知道是假的:一九五三年以后的晓人,《尚书古文疏证》以后的古文《尚书》。
(甲)(丁)两项可暂不论;(乙)(丙)两项,不但引起纠纷,并且妨碍学术的进步。问题又回归到这类情形发生的最初阶段;这仍应该从资料的原始情形与取得手续说起。假定一批资料是真的,它能否取得人的信赖又要倚靠另外的两个成分:(一)最真部分若是发表出来了,是否符合当时的风尚以及研究人的思想习惯?(二)取得手续的巧拙及其安排。第二成分比较容易说明,今以甲骨文出土以后的历史为例:甲骨文为什么不能取信于章太炎,而能取信于现代的文字学家?因为章太炎所见的甲骨文是古董性质的:古董这类资料向来是有真有假。近代学人往往讥笑章氏的顽固;但就他不轻信罗振玉传拓的甲骨文说,却甚近于科学家的态度。至于现代的文字学家相信甲骨文字的理由,也是容易说明的:发掘出来的甲骨文字的资料,在地面下的情形、出土的情形以及出土以后的情形,都有很清楚的交代,每一步的历程所保存的纪录都是多方面的可以互相校勘的。最要紧的证据自然是:殷商时代确有用龟甲兽骨贞卜并刻文字的这件事,而骨卜的起源远在商朝以前已有不少的实物可以证明。在这一情形下,真实资料之能取信于人似乎是必然的;至少就甲骨文出土的历史看,可以作此一判断。
学术的风气与研究人的思想习惯影响学术资料的命运也是很显然的一件事。假古董之行世并不完全起源于“存心欺骗”。作假是由仿效演变出来的;仿效实为艺术发展之初步现象;古董之成一种商品也就等于仿制品取得了经济的报酬;这一发展,没有任何学术的意味。摹仿的作品有时要超过原件,若专就艺术而论艺术,真假之间并无辨别的需要。若是当作历史资料用,辨伪的工作却是必要。辨伪完全是一件斗智的工作。为假古董所矇混的,与其责骗人者之不道德,不如说受骗者之不细心。伪古文《尚书》之所以行世千馀年,因为千馀年的中国读书人不细心;晓人之受崇拜四十年,也是因为这一时代将[的]大部分的生物学家,以及有关部门的科学家之不细心。
假古董的骗人虽为害甚烈,遇了细心的人把它揭穿,随时就可剔除。史学家最大的难题却在如何处理真材料。这一难题牵涉的方面很多,中心的事实是如此的:真的史料与哲学家追求的真理有类似的地方:它们都是无情的、不变的。它们的出现可以为时代风尚加注解,可以把个人的思想习惯纳入正轨;也可以讽刺当代的迷信,不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细心人处理这些材料,若要把它们各作适当的安排,更需要一种职业上必具的胆量。故新史学家的第三个境界应该是:“宁犯天下之大不韪而不为吾心之所不安”,原始资料遇了这种有勇气的人,庶几乎可以相得相辅了。
现代史学界最前线的工作者所喜欢的一句口号为:“有多少证据说多少话”。这句口号喊久了,似乎尚需要重新界说一番。证据是否指所有的原始资料?要证的是什么?这真是史学界的大题目了。原始资料既可分成若干等级,可以作证据的程度显然是不同的。但是要证的是什么,却是最可以使好问的工作人“辗转反侧”的了。要证过去有个黄金时代?要证将来有个大同世界?要证文化只有一个来源?要证民族只有一种优秀?要证天命有常?要证人类进步?这些,好多史学家都尝试过了,但都在材料本身中发现了矛盾。用作证据的资料,唯一可以避免矛盾的方面,为证明资料本身存在之真实性。史学家所有的工作企图若能达到这一目标,其他待证的问题,也许就随着解决了。这是史学家可以追求的第四个境界,姑称之为“无用之用是为大用”的境界。
在这一境界中作历史学语言学的工作,可以说和生物学家地质学家的工作情形是同样的。
[附注] 本文前段所用资料,凡未个别注明出处者,皆根据魏勒氏:《閟尔当伪件》(J. S. Weiner: The Piltdown Forgery, 195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一书,特此申明。
一九五七,二,八,台北。
李济与父亲及儿子李光谟,1937年摄于昆明北郊
值班编辑:继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