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究竟是一座怎样的城市?有人念叨着它偏远、闭塞,说这里和繁华两个字隔着大山大水。可也有人不止一次憧憬那里,一年四季都像极了长假,每一阵风,都是温柔。这样的地方,究竟是退守一隅的旧城,还是站在时代转角处的机灵鬼?八十年前,一位异乡来的摄影师,用手里的黑白胶片,留住了当年昆明的片段。那时的一切,就像传家老照片里的人——你看得清五官,却猜不透心思。
说起来,昆明“偏远”的名声,其实有点冤。大清末年,别处正琢磨着怎么把大件行李绑在骡马背上往前驮,这里早早就学会了与外面联系——不愧是“滇池之城”。别小瞧云南这根“边角料”,一百多年前的云南,不仅跟中原山水相连,往东南亚一带还颇有些生意经。每条大路尽头,是一群背着土货的小贩和几声老火车的汽笛。昆明的日子,早就和外面搅在了一起。
时间来到1940年代,世界仿佛摔了个跤——中国打着大仗,从北往南,只剩下几段安稳的土地。昆明,这个被群山半遮的城市,被命运选中做了一道后方防线。你敢信吗?那时候,逃着空袭来的学子、教授,把北大、清华、南开这么几所响当当的大学,掺和成了“西南联大”,扎根昆明。半张破桌子,一根削短的铅笔,他们在小屋里讲世界,讲希望,还讲理想——外头枪炮声不时轧过,但书生气却没断。
同样也是那几年,一个美国小伙子扛着照相机,跟随“飞虎队”混到了昆明。他算是见识新鲜的人——一边是远道而来的格皮靴西装兵,一边是云南的土路、老房和热热闹闹的集市。他最初以为自己会记录战争,没想到,镜头里打捞起来的,是一个城的浮生百态。
你别说,1942年的昆明街头,真没那么“破”。大马路上跑着老爷车、铁皮卡车,隔三差五撞进一辆吱嘎作响的马车。电线杆子也不少,上头缠着乱糟糟的线,就像头顶掉了毛的老母鸡——不过电的确送得进来,邻里几户晚上点着昏黄灯泡,远比很多同龄城市要新鲜。
但是随手拍下来的房子,却脱不开“旧社会”的影子。大多低矮,墙全靠石头垒,屋顶不是瓦,是一把一把的稻草草草遮雨。城里有片地方烧过一场大火,房子没了,只剩墙头上神仙泥像一排,神色虔诚地被风吹日晒。照片中看不出来,是不是被炸的——也可能不过是岁月太久,无人打理。生活偶尔就有这样的莫名劫数,谁也说不清。
说到出行,那会儿昆明的桥可没几个结实的。照片里,最醒目的还是浮桥——一列列木船当桥墩,夯实了木板搭在上面,不怕沉,但大雨一来,全城都得为它悬着颗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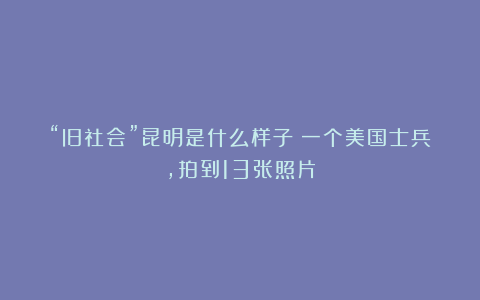
巷口有个小孩,也许是名美军摄影师喊了一声“小布点头”,这孩子回头就摆了个pose,可惜相机快门一声响,他一惊,眼睛正好闭上了。这不是摄影师设想的“英姿飒爽”,可那份憨气,却让人记好些年。
昆明的郊外,风吹过田地和兵营。新房子像是还没盖好,士兵们凑在屋檐下,有说有笑,也有些发呆——也许昨天刚写完家信。谁知道他们是不是临时住在这里,一会也许名单就会被调去前线。路边拉货的母亲,衣服洗到发白,裤脚带着补丁,小娃娃跟在身旁。有一张照片,母子二人背影被太阳拉长,马车悠悠驶过尘土飞扬的街道。有旁观者提一句:那女人看起来不过二十几岁,偏偏眉头早就刻了风霜。
过去那时的孩子,根本不知“童年”怎么写。照片里有几个孩子,小小年纪已经学着把东西挑上肩,有的挑煤块,有的挑着什么,看不清。走累了,两个人在路边扒拉石头,猜拳输赢。再大的理想,也让他们先填饱肚子再说。
寺庙、道观里的香火,总是络绎不绝。昆明人家多数不识字,想不明白前途在哪,便把希望全押在三炷香、两声叩首上。哪家庙门前香灰最厚,娘们们说那里的神最灵——反正日子都难,信什么也无妨。
有意思的是,山路上竟然开着汽车。别以为山高路窄,老爷车在那条迂回的小径上熄了又点、点了又熄。也不是有钱人的排场——也是抗战物资,救命粮食,全靠这些家当托起来。
老昆明和现在比,摸得着的“落后”,瞧得见的“拮据”。可就是这个地方,在最难的时候,挤进了一切希望与绝望。书桌旁的孩子,哼着自创的儿歌,土路上走过歪歪扭扭的马车,连每一缕炊烟里,都是求个平安、盼个明天。
八十多年过去,那些穿破衣的母亲、蹦蹦跳跳的小孩、盯着镜头的士兵,早就跟过去的日头一样渐渐淡远。但总有人会回头问一句:今天的昆明,若和当年的人们擦肩,这座城会不会自己都认不出他们?一方水土,撑过兵荒马乱,多少普通人咬牙扛过生活的辛苦。照片只留下短暂一瞬,却没人说得清,下一个春天,会不会像现在一样温暖长久。
想来,人这一生,遇见的地方,经历的命运,说得清算得明的太少。八十年前昆明的光景,就像一张泛黄的照片,有眼泪,有笑声,也有未曾说明白的故事,等着谁来细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