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塔可夫斯基(1932~1986),前苏联电影导演、编剧,毕业于莫斯科国立电影学院。主要作品有《伊万的童年》《安德烈·卢布廖夫》《索拉里斯》《镜子》《潜行者》《乡愁》和《牺牲》。
本书汇集了塔可夫斯基接受的二十二篇重要访谈,涉及艺术家“对电影与时间的独特解析;对美学的深入思考;对创作与信仰的执着;对流行艺术的不屑;对大众的复杂态度;关于政治、自由、名利、生死的犀利观点;关于女性议题的令人不安甚至不适的言论⋯⋯”这些访谈从侧面反映了塔可夫斯基对于电影艺术的观点,对此他是淡泊且傲慢的,对待不能理解的人则显示出了局促与苦涩。这样一种态度源于塔可夫斯基那种犀利的艺术观:“我认为艺术就是一件强大的武器。”
美国实验电影导演斯坦·布拉哈格认为塔可夫斯基是“当代最伟大的叙事电影导演”。布拉哈格强有力地详述了自己的观点:“20世纪的电影有三大任务:一是创作史诗,讲述世界各个群体的故事;二是聚焦个人,因为只有于个人生活的怪异之处,才能发现真理;三是拍摄梦境般的作品,照亮无意识的边界。我认为,安德烈·塔可夫斯基是唯一一位在每部电影中都能实现并平衡三者的导演。”
对于人们总是想要过分解读电影中的意象,塔可夫斯基一方面倾向于鼓励他们提出好的问题,他引用歌德的话说“要想得到聪明的答案,就要问出聪明的问题”;另一方面,他更喜欢劝说人们保留住那些意象背后的神秘性,“如果你去探究意义,反而会错过发生的一切⋯⋯分析一部作品必然会毁了它”。
精神性是这些访谈中凸显出来的塔可夫斯基的艺术准则。他认为艺术被赋予的一个艰巨任务就是复兴精神性,因为“人从本质上看是精神存在,人生的意义在于精神性的精进。如果人类做不到,就会世风日下”。“艺术应当提醒人类,他是一种精神存在,是广阔无际的精神体的一部分,而这个精神体也是其最终归宿。”或许这个角度是最切近地理解塔可夫斯基电影的法门,尽管不会是唯一的法门。
在《安德烈·卢布廖夫》中,塔可夫斯基感兴趣的是这位15世纪伟大的俄罗斯画家,其个性与其所处时代之间的关联,他与生俱来的敏锐度,他对时代的深刻领悟和完美复刻的能力。“他是一个以残酷敏锐性来观察世界的人,对于遇到的每样事物,对其他人习以为常、不以为意的事情,他都能保持极度敏感。⋯⋯艺术家始终是社会的良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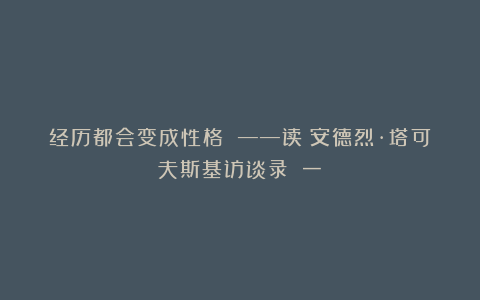
艺术家的个性与所处时代的关系被塔可夫斯基称为个性的辩证法。“人经历过的每个事件,都会变成其性格、观念乃至自身的一部分。因此,电影中的这些’事件’不应该仅是为了构成’主人公’所处的背景。以艺术家为题材的电影往往遵循这样的套路:主人公看到了一个事件,接着他开始在观众面前思考这个事件,然后在作品中表达自己的想法。在我们的电影中,从头到尾都不会有卢布廖夫创作圣像画的场景。他只是一个活着的人物,甚至不是每个片段中都有他的存在。”
因此我们不要指望看到一位画家的传记或者有关他的历史——事实上卢布廖夫的材料少的可怜,这在塔可夫斯基那里反而成了优势,让他得以“完全自由地建构他的个性,无须受到传记故事的束缚,也不用考虑人们根深蒂固的先入之见”——而是在导演的引导下,发现一个人的经历如何成为他的性格和观念,探索人类心灵的发展历程,这种转变和历程是我们每个人都不可避免要经历的过程,无论你是一个正在接受贿赂的官员、和尚,还是一个刚刚走出监狱的无所依靠者,或者人生中首次离开父母、进入陌生世界的大学生。
所谓艺术不是娱乐,在塔可夫斯基那里,帮助我们恢复精神性、增进精神性、救赎精神性的才是艺术;《超人》和《E.T.外星人》则是娱乐,因为导演把电影当作赚钱的工具,并为此最大限度地取悦观众。塔可夫斯基认为自己是第一类导演,“把电影视为一种艺术形式,他们会问自己关于个人的问题,会把拍电影当成磨炼,当成恩赐和义务”。他们绝不会取悦观众,而是一方面把观众当作平等的人,一方面也当作想要获得理解、获得启发的对象。因此艺术的观众永远不会像《超人》的观众那样多,因为艺术和观众之间都要互相审视和考核,因为“如果每个人都能理解艺术,那么杰作就会像田地里的杂草一样随处可见。也就不存在能力上的差异,不会促使大家争先恐后地挖掘潜能”。
历史也不是艺术的主题,就像僵化的好古所引发的索隐也不应当成为历史的主题。先入之见的可怕性在于,如果认定了古人的都是好的,或者华盛顿、牛顿的祖先在中国,其中就不仅仅是滑天下之大稽的问题,而是不但显得好像在屎上雕花,更加暴露了想要舐痈吮痔的丑态,二者都潜藏着要么向当权者献媚、要么想要捞取好处的小心思。只不过,高级黑和低级红之间仿佛只有一堵摇摇欲坠的薄墙,屎上雕花弄不好就会让自己变成遗臊撒粪,舐痈吮痔也很可能非但不能让皇帝满意,更令自己中毒弥深。我们说清末文人开始好古,或者那个有关《红楼梦》独成一体的索隐派,他们都是塔可夫斯基的批判对象,他们就像有些电影对历史的刻板描绘一样,与艺术已经无关,观众唯一得到的体会就是导演一定是无法忍受当下,因此电影成了他“对当下的逃离”的通道,而观众成了无辜的受害者。(未完)
评价:4星
(本文内容为作者独立观点,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授权事宜、对本稿件的异议或投诉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微信号|琴弦在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