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左图右史,邺架巍巍,致知穷理,学古探微。”清华大学有着悠久的人文传统。新时期以来,学校尤其致力于人文学科的溯源与重建。王国维、李学勤二位先生,恰好是前后两个时期清华大学人文学科辉煌成就的代表人物。温故知新,我们特开辟“经典重读”栏目,着重刊发二位先生具有典范意义的出土文献类学术论著,以飨读者。王国维先生著作以《观堂集林(附别集)》为主,李学勤先生著作以《李学勤全集》为主,力图较为全面地回顾二先生治学的成就和特色。
此次刊载李学勤《对彭裕商教授意见的处理建议》,见《李学勤文集》第三卷,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23年,第418—421页。
对彭裕商教授意见的处理建议
彭裕商教授已对陈久金先生三月十九日所排金文历谱稿,从铭文等角度提出了宝贵意见。兹对这些意见,提出处理办法的个人建议,供研究参考。
(一)克钟、镈应改排到宣王世,彭教授意见是正确的。我个人在去年三月札记《吴虎鼎研究的扩充》中有同样看法。
(二)卫盉与五祀、九年两件卫鼎确系同时。鼎与盉都和有 “穆王”的长思墓器相似,而五祀卫鼎有“共王”名号。这些名号,是生称还是死谥,学术界有争论,但铭中行事应与名号王世一致,即长思器记穆王时事,卫器记恭王时事。因此,就历日而言,把卫盉及两鼎放在恭王是不错的。
(三)二十七年卫簋与卫鼎、盉同出,均系裘卫所作,但从历日看,很难将簋放在鼎、盉后面。排在后面另一王,又嫌距离太远。既然鼎、盉在共王,簋置于穆世还是合理的。至于从“又”的“裘”字,如说晚期,卫簋也难放在那么晚。
(四)师虎簋的字体是西周中期的,不是晚期的。其器形是小兽首环耳的全瓦纹簋,实与无㠱簋接近,但后者似更矮胖一些。和师虎簋更相似的,是豆闭簋和即簋,都属中期[1]。我曾推定即簋在孝王时[2]。
以上各器都是没有盖的,是否均系失盖,尚待研究。有盖的则可举出蓝田寺坡村出土的弭叔师察簋,其器的部分也与师虎簋一致,年代吴镇烽先生定为懿王[3]。类似的有盖簋,还有唐县南伏城的一件[4]。总之,小环耳的全瓦纹簋多属西周中期偏后,无箕簋可能是其在晚期的孑遗。
从铭文的系联看,师虎簋也不能太晚,详见下表(表中的王年,是陈久金先生历谱所定)。可以看出,师虎簋不是孤立的,它牵涉到一大批器物,有相当复杂的人物关系,而这些人物的年代,又是有若干可供推计的标准的。特别是卫盉、鼎的历日属共王,已决定了各器的位置。
(五)器是扶风庄白微氏青铜器的组成部分。微氏有人名的四世,析约当昭王时,丰约当穆王时,墙则在共王时,墙之子应该在懿王以下[5]。现在陈先生历谱懿、孝、夷三王在位都短,最早见于懿王十三年,即该王最末一年,他下及孝王,并与厉王早年的人物有系联,是可以理解的。有关情况,请见下表:
这里面唯一的问题,是师鼎的师俗,如与共王时师俗父即伯俗父为一人,未免距离过远。但师鼎的师俗是“司邑人”的小官,五祀卫鼎伯俗父已与井伯等并居大臣之列,他们恐怕不会是同一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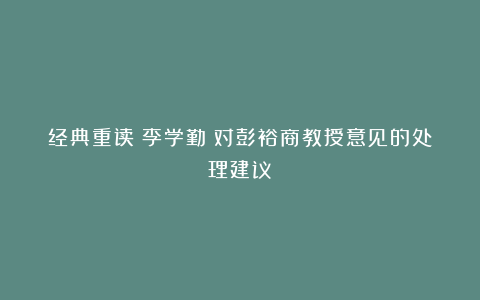
我认为,陈先生历谱中应予调整的,是牧簋。此器是腹部“倾垂”的双耳簋,下有方座,腹、座均饰波带纹,耳上有很大的兽首。和它非常接近的,有《殷周青铜器综览》簋330,惟无铭文;比较类似的,有《综览》簋340, 有盖,对铭象形“虎”字,显然较早。牧簋铭有内史吴,故前人均以之与师虎簋联系,定于共王以至孝王。现在排在厉王,是不够妥当的。建议移至懿王七年(前893),十三月戊申朔,甲寅系初七日,与铭云既生霸相吻合。
金文历谱,特别是西周中期一段,还需要不断修正。以上所论,谨请指教。
1999年5月7日晚
注释
[1] 林巳奈夫:《殷周青铜器综览》第1卷将此三器列于西周ⅡB,九a型,近似的还有吕姜簋、兑簋。
[2] 李学勤:《新出青铜器研究》,第87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
[3] 吴镇烽编:《陕西金文汇编》上,三九九、四〇〇,三秦出版社,1989年。
[4] 林巳奈夫:《殷周青铜器综览》第1卷,皆列于西周ⅡB,九a型。
[5] 李学勤:《新出青铜器研究》,第87-90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该文据孙诒让说,认为师酉簋有史墙,现在看来不确。
经典重读栏目往期文章可点击下方图片查看
排版丨林妖
审核丨张官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