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金雯老师的新著《西方文论》专节讨论了“文学与情感”,首先将“情感”界定为“身体与物质和社会环境的交接”,并将其分为观念性情感、无意识情感两种类型;然后探讨了文学情感研究的路径与方法,通过中西文论、作品案例的解析,展示了文学情感研究的复杂维度与多重可能性。金雯老师的文学情感研究最终指向主体性的构成与消解,在她看来,情感既是主体同一性观念的来源,也会呈现出不可知的特性,使人与自身产生疏离,乃至取消主体性。
本文摘录自金雯《西方文论》第三章第一节“文学与情感”,原题“何谓文学情感研究”。感谢金雯老师授权!
有时候,我们需要使用新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考察情感话语与其他话语的关系,也需要强劲的形式分析,阐释文学作品形式与意义的多维度展开。从文学的角度来说,最关键的可能不是确定最为复杂合理的情感分类系统,而是以情感问题为契机,考察主体构成、社会情境和话语系统之间的错综关联以及这种关联对观念构成的作用和影响。简而言之,就是考察处于社会情境和话语系统之中的身心互动机制。观念性情感在直观性和建构性之间滑动,始终不会僵化地停留在某处。因此,文学情感研究需要解决两个核心问题:
我们如何判断话语中的情感?情感范畴作为话语构建,与某些直观情感经验对应,因此大部分读者是可以从人物行为、表情和叙事者所用的情感范畴来辨别人物所承载的情感,并达成一致的。不过,这些情感范畴并不一定对应情感经验,也与早期现代的身心理论、道德哲学、美学、医学、性别话语、历史学和社会科学(政治哲学和社会理论)等话语对接,可以被分析、还原为建构情感经验的过程,展现情感的建构性。与此同时,有很多情感经验并不一定用情感范畴表达,我们在18世纪小说中发现许多主题和形式上的特征,都在暗示,而非表达情感。
与上述问题相关,我们需要考察文学语言如何构建身心关系,如何与同时代其他形塑身心关系的社会环境、话语系统发生互动。对文学形式十分敏感的新历史主义阐释框架总是尝试在文学形式和相关话语体系之间建立关联,说明文学形式和体裁的演变与话语体系及其所依托的政治经济关系之间的互文关系。文学情感研究也同样遵循这个原则,但回到前面的第一个问题,“情感”作为研究主题和对象并不稳定,有时是直接的心理刻画与情感表征(表情、声调等)书写,有时是暗示性的景物描写,有时是身体姿态描写。要把这些形式细节特征与探讨情感的跨学科话语系统并置在一起,考察它们之间互相渗透和影响的关系,这应该就是文学情感研究的主要内涵和意义,也是其独特的挑战。
首先,我们来探讨一下如何在文学文本中辨别情感经验。
我们在阅读文本的时候,一般要判断文本中呈现了什么样的“情”,但因为经验性情感并不完全与观念性情感对应,因此文学情感研究的第一步非常困难。我们往往无法解读情感,而是需要大量揣测,这个揣测的过程就是重新建构文本情感的过程。
文学作品的解读可以聚焦于显性主题,比如文学文本中描写的战争和政治经济格局,然而一旦我们开始解读文本对应的“主观世界”,就必须要面对不确定阐释的问题。文学情感研究将文学阐释的难度最大化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文学文本展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个体和时代精神?而文本的作者——当然这永远只能是我们建构起来的作者——对这种时代性情感又持有什么态度?这就是文学情感研究的本原性问题。
威廉·雷迪《感情研究指南:情感史的框架》,周娜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
在西方文学研究的脉络中,情感向来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雷迪在《感情研究指南:情感史的框架》一书中提出“衔情式话语”(emotives)这个概念,指“直接改变、构建、隐藏或强化情绪的工具”,但这个话语的边界很难划定。①文学文本中的所有语言都可能是衔情话语,我们可以分四个类别说明:
(1)情感范畴:如果文学作品中直接出现“悲伤”“惊讶”等字眼,那自然会给予读者较大的提示。但虚构人物的内心世界通常十分复杂,即便叙事者指出他们的情感状态,也仍然有很多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内心活动如同海面下的冰山。海明威提出了这个“冰山理论”,也在自己的作品中践行了这种创作原则。如果一个故事的叙事者不可靠,那读者就更不能把叙事中的情感范畴当真,康拉德、亨利·詹姆斯和麦尔维尔等作家都以使用不可靠叙事者著称。
(2)情感征兆:文学作品经常对人物的行为举止进行描绘,也会通过内心独白和心理转述等手段描绘内心活动,但不直接使用表示情感范畴的词汇来对人物的情感状态加以揭示。与此同时,有很多情感状态是复合而模糊的,可能是有意识情感和无意识情感叠加和交织而成的。这时候,读者只能以文本中包含的线索和征兆为依据推测人物的情感状态。契诃夫的短篇故事和剧作《海鸥》中都出现了突然拔枪自杀的人物,但并没有向我们揭示其心理动因,这时候读者就需要做出揣测。20世纪小说对人物内心的展示愈加隐晦,当代黑奴叙事、犹太人大屠杀小说和女性小说刻画了不少因为过往的创伤而承受忧郁、焦虑等情感状态的主人公。
(3)情感特质:文学中的情感不仅与虚构人物有关,也与作品整体的精神取向有关,在抒情诗中与言说者相连,在叙事作品中与叙事声音相连,有时候显现为“语调”,有时候显现为“美学特征”。倪迢雁曾分析“语调”(tone)这个叙事元素,认为在形式分析中“语调”经常被理解为“态度”或“立场”,但其实这两者都与情感相关。对文学作品“语调”的解读是对文本总体价值取向的解读。比如“偏执”(paranoid)这种情感基调被认为是后现代小说中常见的情感基调,托马斯·品钦的小说《拍卖第49批》(1966)是其中的代表。该小说主人公是一位居住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主妇,因为观察到城市中遍布的一些记号而开始怀疑是否存在一个秘密的收寄邮件的地下组织。这种对不可见和无法确定的系统性力量的阴谋论式揣测引发了不安,使人惶恐也使人自嘲。这种复杂的情感不仅属于女主人公,也可以被认为是小说叙事者的心理状态。情感特质同样蔓延在文学作品的审美取向中,我们经常使用“崇高”或“秀美”等审美范畴描绘文学作品,这实际上隐含着对作品总体情感倾向的判断。比如雪莱的《勃朗峰》就是“崇高”诗学的一个例证,它描写了阿尔卑斯山勃朗峰的险峻巍峨之相,思考强大的自然是否能与基督教信仰兼容的时代性问题,最终给出了一个较为肯定的回答,认为自然与精神相通,自然贯穿着神秘而宏大的精神力量。因此,“崇高”这个审美范畴与一种乐观的信念相连,表达对人与世界和谐关系的肯定,《勃朗峰》的“崇高”背后是拨云见日的欣慰感。正如文学作品的“语调”是一种具有政治内涵的文化态度,审美取向也是作品整体对生活世界的回应,具有干预观念和权力关系变化的政治功用。当代审美范畴紧密地与资本主义时期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分层相关。倪迢雁在自己的第二本著作《我们的审美范畴》中指出了三个最常见的审美范畴,其中最引人注意的可能是“萌”(cute)。当人们认为一个事物很“萌”的时候,是觉得“无助之物被同情和怜悯”,也是在表达一种对其占有的欲望。②情感与审美的连接也在与历史政治紧密地对话,“萌”物的流行印证和加剧了商品拜物的逻辑,让人们给无生命事物赋予机械性生命,但同时也让人们产生一种对其客观特质有所把握的幻觉。
Sianne Ngai, Our Aesthetic Categories: Zany, Cute, Interesting,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4)情感暗示:文学作品中看似与人物情感无关的细节和描写都可能是某种情感的暗示。《包法利夫人》是最为著名的文学案例,小说中包含大量对城市、小镇、农庄自然风光和家居物什的描写。这些描写不仅还原了历史背景,而且具有重要的情感功能:一方面以景写情,暗示人物情感;另一方面暗示叙事者看待景物的方式,隐含对包法利夫人追求感官和情感满足的方式的批判,提示她摆脱自身狭窄视野的可能。同理,我们在狄更斯、巴尔扎克、乔伊斯、沃尔夫、罗伯-格里耶等作家笔下都能看到大量对物品的描写,比如狄更斯《荒凉山庄》中的典当铺和《驴皮记》中的一众商品笼罩着“异化”的浓重阴影,凸显了人被物役使也因此沦为物的伤痛。
这告诉我们,文学作品中的所有元素都具有表情功能,都可以被认为是“衔情式话语”,对文学作品的“情感”做出阐释就是对整部小说展现的多重内心世界——包括人物和作者内心世界做出合理阐释,也是对这种内心世界的生成语境和政治批判意义做出解读。这也是文学情感研究的特殊难度。
从中文语境来说,“情”的用法一般是与语言联系在一起的。中国文学如何表情也是一个基础性问题,对情的呈现也以各种形式手段实现。除了使用情感范畴和情感征兆来写情,中国文学还大量使用物和景的描写。与此同时,对文学作品整体性的情感基调也有诸多解释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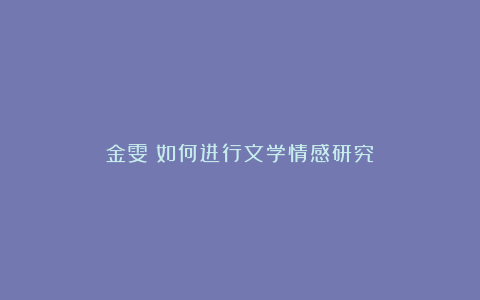
陈世骧《原兴:兼论中国文学特质》,收录于陈国球、王德威编《抒情之现代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
陈世骧先生于1969年撰写《原兴:兼论中国文学特质》一文,由此奠定了他后来于1971年提出的“抒情传统”的论调。他在文中指出,《诗经》中“兴”这种手法模拟“原始舞蹈时人们发出的激动的呼声”,达到“韵律与意念的交互感应”。③徐复观在《释诗的比兴——重新奠定中国诗的欣赏基础》中也将“兴”的手法与情相连:“兴的事物和诗的主题的关系……是由感情所直接搭挂上、沾染上,有如所谓’拈花惹草’一般;因而即以此来形成一首诗的气氛、情调、韵味、色泽的。”④“兴”并非无意义的语言重复,而是标志着情感被事物触发而外显的过程。李志春对这种说法做了补充,认为“兴”所寄寓的情感并非自然情感,而是“凝聚着生活世界的伦理价值”的道德情感,作为言此意彼的手法,“兴”不仅仅搭建了一条符号链,更是在其中注入了感物兴情这种物质性的流转变迁。⑤
中国诗词中的景物描写对情感呈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基于高友工先生有关律诗是中国抒情文学“美典”的断言,吕正惠对律诗中景物描写的情感功用做出分析。他指出,古风是“感情直接的表现”,而律诗却将情感熔铸在固定形式中,律诗的中间四句描摹意象,并构成两个对句,此处描写的自然意象因为对句的使用而得到固定和强调,经历了一个“本质化”过程,而一首律诗的最后两句也就因此可以顺利地将感官印象转变为对情感的呈现和感悟。我们可以在李商隐《锦瑟》的最后两句“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中清晰地体会到感官经验是生命最真实核心的情感。⑥
Zong-qi Cai, 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ry Creation, A Historical and Critical Introducti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23. 第8、9章讨论了“以情为中心的创作论”。
如在西方文学中一样,中国文学中的“衔情式话语”不仅与物和景的书写相关,也体现于中国诗歌贯穿的整体性情感基调。陈世骧在分析“兴”的文章中也对诗歌的情感基调加以解释:“诗所流露的精神或情绪的’感动’,此物不可割离,分布于全诗;所以我们称之为’气氛’,并以为我们已经体会到某种’诗情’。”⑦这也可以追溯至刘勰对情的看法,他在《情采》篇中提出“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在《物色》篇中提出“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⑧蔡宗齐在刘勰所论基础上总结出有关六朝“情文”的理论,认为创作意象的过程即“情、物、言这三者的互动”⑨。正如陆机《文赋》所言:“情曈昽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⑩同样的观点甚至可以延伸至小说。萧驰曾富有新意地指出,才子佳人小说的骈偶现象和小说中嵌入的诗歌有很多同构之处,体现了宇宙结构的规则性和对称性,流露出一种“感性的乐观主义与理性的乐观主义的统一”11。
可见,情的含蓄是一个跨文化现象,不能简单归于某一民族的表情方式。情感作为一种建构和实践,急切召唤着读者的阐发和解读。虽然我们在这一节中表示,考掘和说明作品呈现的情感是文学情感的基础,但这也构成一个完整的阐释循环,可以被认为是文学情感研究的终点所在。我们对文本情感的指认也是对其内涵的整体性阐释,需要调动文学研究的所有工具。
金雯:《西方文论》,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25年5月第1版。
注释:
① 威廉·雷迪:《感情研究指南:情感史的框架》,周娜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9页。
② Sianne Ngai, Our Aesthetic Categories: Zany, Cute, Interesting,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p.60.
③ 陈世骧:《原兴:兼论中国文学特质》,载陈国球、王德威编:《抒情之现代性:“抒情传统”论述与中国文学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77页。
④ 徐复观:《中国文学论集》,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93页。
⑤ 李志春:《从“即生言性”看自然情感与道德情感之关系:以〈性自命出〉为契机》,《国际比较文学(中英文)》2022年第1期,第123—140页。
⑥ 蔡英俊编:《中国文学的情感世界》,黄山书社2012年版,第26、29页。
⑦ 陈世骧:《原兴:兼论中国文学特质》,载陈国球、王德威编:《抒情之现代性:“抒情传统”论述与中国文学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77页。
⑧ 刘勰著,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157、1732页。
⑨ 蔡宗齐:《“情”的概念何以拓展——从先秦“情”“性”论辩到两汉六朝文论中的情文说》,《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2期,第47页。
⑩ 齐云主编:《古文观止》(增补本 上卷),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13页。
11 萧驰:《从“才子佳人”到〈石头记〉——文人小说与抒情传统的一段情结》,载陈国球、王德威编:《抒情之现代性:“抒情传统”论述与中国文学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5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