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十三,东昌府河面起雾。
渔网一兜,捞出半具泡发的尸首,颈上一刀,刀口翻白,像咧开的嘴。
巡按御史曾孝序蹲下身,用竹箸拨开头发,对身边书办道:“记下——右腕旧有刀疤,小指缺半截。”
他声音不高,却惊得芦苇荡里水鸟扑簌簌乱飞。
这是苗天秀,那位被家奴苗青伙同艄公砍了扔进河里的富绅。
尸首会说话,只是世人多半装聋。
这是《金瓶梅》第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这三回里,插入的一桩苗青弑主案。
故事说的是江南富绅苗天秀,表亲黄通判来信邀他同游东京。苗员外便带了家仆二人:一名安童,忠谨老实;一名苗青,伶俐却藏奸。
原来苗青早与苗员外新纳的小妾刁七儿在亭边暗里传情,被苗天秀撞破,痛打一顿,几乎逐出,赖众人求情才勉强留下,自此怀恨。
船过临清闸口,夜泊荒岸。
苗青窥得行囊沉重,暗起杀机,便勾结撑船的陈三、翁八:三更风起,灯影昏黄,三人持刀入舱。苗天秀梦中惊觉,只喊得一声“冤……”,刀已抹过咽喉,鲜血溅篷壁;安童被一脚踹落水中。
随即,三人搜出金银细软,将主仆尸体一并推入浊流,分赃而散。
两张卷宗,两种底色
谁知安童命不该绝,随波漂流十余里,幸得一老渔翁撒网救起。
少年死里逃生,连夜奔至东昌府提刑院擂鼓鸣冤。
当日正值夏提刑夏延龄坐堂,收下状子,即刻签票缉拿。
不出两日,捕快便将陈三、翁八锁到。堂上三推六问,二人熬刑不过,供出主谋苗青。
夏延龄发下火签,将陈、翁二人暂押死囚牢,一面行文各州县,画影图形追拿苗青。
风声传出,苗青已潜至清河。
他探得西门大官人门路通天,便托王六儿穿针引线。西门庆开口一千两,苗青咬牙如数奉上。
西门庆转手五百两送进提刑衙,夏延龄眉开眼笑,二人一拍即合。
次日升堂,把陈三、翁八重敲一遍,逼令翻供,硬坐“见财起意,谋财害命”之条,主犯苗青竟被轻轻抹去。
安童在堂下看得眦眦血涌,当场喊冤。夏延龄拂袖退堂,只丢一句“刁奴妄诉”。
安童走投无路,只得再投巡按御史衙门。
至此,巡按曾孝序——那位曾布之子、乙未科榜眼、朝野闻名的“四有清官”正式登上《金瓶梅》的舞台。
曾孝序者,都御史曾布之子,乙未榜眼,年未三十,朝野已称其“铁面冰心”。
安童当堂喊冤,血泪交迸,孝序静听片时,便记起两月前河滩那具无名男尸:颈上一刀,骨节寸断,当时无人认领,如今看来正是苗天秀。
曾孝序再看卷宗:
卷宗一:
“犯人陈三、翁八,见财起意,谋杀苗天秀,赃银三百两,各分不均,复推落水。”——供词上血红指印,是夏提刑与西门庆连夜“加急”画押的句号。
卷宗二:
“苗青主谋,买命一千两,内五百两送夏提刑,五百两送西门庆。”——安童跪在曾孝序案前,咬破指尖补写,墨迹未干,泪先湿纸。
他即刻带安童赴停尸棚,揭席认尸,丝毫不爽。
旋调卷宗,翻出旧日口供,墨痕犹湿,却漏洞百出。
孝序冷笑,命提陈三、翁八重鞫。
二犯见堂上青天,不敢再瞒,将苗青主谋、贿通官府之状,一五一十吐出。
孝序拍案震怒,朱笔如刀:一面飞签火票,画影图形缉拿苗青;一面草成弹章,直指夏延龄、西门庆同恶相济,受贿纵凶,坏法乱纪。墨香未干,雷霆已动。
“四有干部”曾孝序的结局
曾孝序不愧为“四有清官”——有文化,进士出身;有道德,“清廉正气”四字写在吏部考语最上头;有理想,想效包龙图再世;有信仰,信“杀人偿命”四字比佛经还响。
可惜,他只缺一样:无梦。
和 曾孝序不同,负责武松案的陈文昭则不然。
在武松案里,他把“死罪”改“流罪”,说“法外原情”。
那一句“人情两尽”像一把钝刀,割不断,却也不让血流尽。
陈文昭知道:梦不能当饭吃,但做梦的人,至少夜里还睡得着。
再说回曾孝序的弹劾,他递往京城的奏疏墨迹未干,翟谦的抄本已摆在蔡太师案头。
蔡太师朱笔只批四字:“该部知道”。像一记闷棍,打在鼓上,咚一声,余音全是嘲弄。
曾御史呈递参本之后,不见半点反响,便心知那二官已然暗中打点。
此时,恰逢蔡京陈奏七件事宜,皆是损下益上之举。
曾御史义愤填膺,难以按捺心中怒火,遂又呈上一道表章,言辞犀利地驳斥蔡京。
可叹的是,曾孝序是《金瓶梅》全书唯一一个清官,最终以家人入狱,自己被流放岭南结局的官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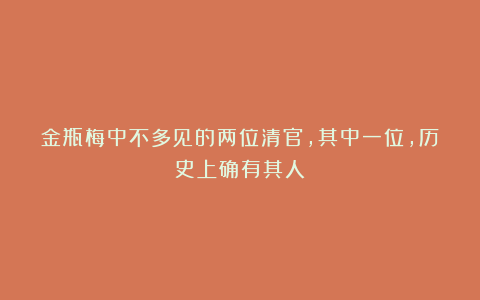
事成之后,夏提刑在西门府吃酒,酒过三巡,举杯笑道:“曾公雪冤,雪来雪去,雪不过银子一堆。
”西门庆嘿嘿连声,举杯回敬:“雪化得快,银锈得慢。”
陈文昭的“人情”账本
苗青本人倒逍遥。
案发第三日,他已剃了头发,换名“海清”,搭上南下的盐船。
船头浪高,他怀里揣着剩下的三百两——一千两买命,五百两买路,还剩三百两,足够他在扬州娶两房小妾。
水声里,他哼着小曲:
“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无尸骸。”
歌声被风撕碎,飘进曾孝序梦里。梦里他仍蹲在那具浮尸旁,用竹箸拨弄刀口,刀口忽然流血,流成一条河,把他自己淹没。
再翻翻武松旧案:西门庆使银子,陈文昭也收,却只在“活罪”上做文章。
武松脊杖四十,刺配两千里。苦是苦,命还在。
陈文昭在卷尾批一句:“留得青山,再图相见。”
十年后,武松血溅鸳鸯楼,青山果然还在。
若换成曾孝序,必是“立斩不待时”。斩得干净利落,却斩断了后来所有的可能。
却说曾孝序被贬岭南那天,灞桥风紧。
老仆挑着书箱,箱里只两卷《大明律》、一册《曾子家训》。
驿卒催行,他回望东京,忽吟一句:
“梦里输赢总未真。”
这是《金瓶梅》替他写的判词。
梦里,他赢了;醒来,枷锁加身。
苗青案终于尘埃落定。
王六儿得一百两、四套衣服,笑得见牙不见眼;
西门庆、夏提刑各得五百两,连夜把银子埋进后花园;
翟谦、蔡京的礼物堆成小山,连门槛都垫高三寸;
苗青改名换姓,在扬州开了“海清药铺”,专卖补肾丸。
唯一哭的是安童。
他在曾孝序被押出京那日,跪在道旁,额头磕出血。
血滴在尘土里,像一粒朱砂,很快就被马蹄踏碎。
曾孝序与陈文昭,本是一枚铜钱的两面:一面刻着“法”,一面刻着“情”。
铜钱抛向空中,落地时哪面朝上,全凭风向。
陈文昭懂得顺风,曾孝序偏要逆风。
逆风者,死得快;顺风者,活得长。
于是《金瓶梅》告诉我们:
正义不是迟到,而是压根儿没上船。船头上挂的旗,写着“皆大欢喜”。
尾声的尾声
很多年后,扬州瘦西湖畔,苗青在药铺柜台后打瞌睡。
梦里,他又看见那具浮尸漂来,刀口咧开,像笑。
他惊出一身冷汗,抬头,却见墙上新贴的官府告示:
“严禁私盐,违者重究。”
落款是“巡按御史曾孝序”。
苗青揉揉眼,再看,落款又变成了“陈文昭”。
他愣了半晌,忽地笑了:“原来都一样。”
风从湖面吹来,带着早桂的香。
香味里,浮尸的影子渐渐散去,只剩一湖碎银,晃得人睁不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