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庄水库建设记》连载:之一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间,天气已很冷了,我睡在窑棚中间的地铺上,被两边的人拥挤着,十分暖和。地上铺垫着新鲜的干稻草,虽然家里带来的旧棉絮不是很厚,但二、三十人拥挤在一个小窑棚里,密不透风,还是很暖和的。
“㘗”……,一声尖利的哨音把我从睡梦中惊醒,只听得:“起床啦,快六点钟哒,赶快起来,去迟哒食堂没得热水哒啊”,我听出这是连长卢治典的声音,有人厌恶地絮叨:“妈的驼子(卢是个罗锅背),汪他妈的个什么逼?老子一个好梦被他吵醒哒”,另一人接道:“你做的个甚嘛梦?是在吃妈妈儿吧?哈哈哈哈……”,男人们淫荡嘻笑着慢慢欠起身来。我一挺身坐起来,把仅穿一件单汗褂子的上身套进旧棉袄里,一咬牙钻出暖和的热被窝,穿上两膝和屁股都打着补钉的一条单裤,趿上我的破布鞋,跟着大人们钻出窑棚的草帘门。
乍一出来,被晨风一吹,浑身一个激零。四周黑黢麻拱的,天空的星星闪着清冷的寒光。满地白霜象下了一场小雪,踩上去发出轻微的嚓嚓声,凌冽的晨风一吹,脸象刀子割的一样疼。食堂里点着几盏煤油灯,灶台上巨大的甑子热气腾腾,炊事员佝身在甑子里一钵一钵地往外取饭。我们吃的是半斤一钵的大米饭,瓦钵盛装的、热腾腾的白米饭清香扑鼻,诱人食欲。下饭的菜是每人一勺水煮萝卜块,当下冬天的蔬菜本来就单调,除了萝卜就是白菜,但是人们的食欲却相当旺盛,不用什么爽口的菜肴,萝卜块煮熟了放点盐和辣椒面,一缽饭打一勺,大家或站或蹲着边吃边聊。事务长孙学伦对大家说:“您们各位老人家们听到啊,我咧食堂的筷子都尽您们拿光了啊,今儿中午您们各人自己带筷子,不带筷子莫说到时候您们就要撇棍棍吃饭的啊”。排长刘大平过来催促大家:“吃完了快些走啊,去晚哒抢不到好场子啊,我今儿在屋地跟你们把窑棚顶上的瓦捡一下,免得明儿一下雨你们屁儿都会闷到水里”。王家茂打趣地喊道:“是怕你们俩口子淋湿了得痨病吧”?说完挤眉弄眼的哂笑。我这时才十五岁,还是个不谙世事大男孩,对这些大人们说的“德行话”半懂不懂,也无心细究,三扒两下吃完一缽饭就赶紧回窑棚去换鞋。
我脚上趿的破布鞋是我的当家鞋,虽然前后都破了洞,可仍是我洗脚后上床时才能穿的鞋,出工只能穿草鞋。在家干活时一般都是赤脚,冬天里或上山割草、打板栗时不得已就弄双草鞋穿。买草鞋五分钱一双,看似便宜,其实不然,因为我一天才挣得一、二角钱。我们家弟兄五个,全靠母亲一双手做鞋穿,往往一年难于穿上一双新鞋,买草鞋穿就成为常态。那时有些老年人在家打草鞋卖,为了省钱,我也向他们学着自己打草鞋穿,还真打了些穿了,只是学艺不精,打的草鞋粗鄙不堪,勉强自己穿穿罢了。要讲穿得舒服,那就是布草鞋了,因为布不磨脚,还比草结实耐穿。但是破布非常难找,那时的农民们买不起布,旧衣服总是补了又补,最后还用来做鞋底,是绝不会丟弃的,所以想打一双布草鞋穿是非常难的。我这次出远门,母亲忍痛拿出家中所有积蓄给我买了一双二块七的解放鞋,还带了五双草鞋。我把解放鞋当宝貝一样爱惜,舍不得穿,塞在被子下面,每天没人时拿出来抚摸一下,嗅一嗅那淡淡的橡胶味,便得到一丝丝满足感。今天第一次上水库工地,我拿出一双新草鞋穿上,尽管我长期穿草鞋已经习惯了,但光脚穿新草鞋还是有点磨脚的,不过一咬牙忍一下,过一会也就好了。你别笑话,我为什么不穿双袜子?告诉你,自打十一岁到农村后就没穿过袜子了,可能小孩子抗冻些吧,下雪天我们还比赛谁能赤脚在冰雪地上跑呢。
我穿好草鞋,扛起工具,同住在各个屋场的民工们汇集在一起,向水库工地出发。看满天繁星在晨曦中闪着寒光,东方有了一抹淡淡的魚肚白。走在狭窄的田埂小路上,已冻得麻木的双脚都感觉不出新草鞋磨脚的微痛。来到新环境的兴奋和对将要到来的劳动强度的担忧佔椐了我整个身心。我当时也就十五岁多,虽然在家务农已有四年多了,但那都是在家庭和兄弟们的环顾下。再说生产队农活种类繁多,有重有轻,我们这些孩子们在农田里只是邯郸学步,没有定量和好赖,反正一天就混个三、两分(十分为一个标准工),到我满十五週岁来官庄之前,也才爬到了六、七分的水平。但这次的水库工地工种单一,就是挖土、运土,听说还是按挑土的担数记工分的,心中不禁惴惴不安,我这单薄的身体扛得住吗?
大约走了半个小时,晨曦中,庞大的水库工地展现眼前,一条狭窄的小溪流到这里被拦腰截断。河谷的左侧修了一条导流明渠,谷底大坝基础已具雏形,大约有四、五十米宽,二百多米长。两边陡峭的山坡上已开辟出了无数条倾斜的运土道路,全是由山顶山腰向谷底坝基汇聚。正值上工时分,山道上蚂蚁般的人流向各自的土场运动,高音喇叭里放着《公社是根长青藤》《社会主义好》等音乐,我还是第一次听高音喇叭唱歌,听得好振奋,仿佛浑身细胞都跳跃起来。不时地播音员又播放一段表扬稿:“XX公社XX大队昨天发扬苦干加巧干的精神,完成了多少土方量,大家要向他们学习”。我随大家来到左侧山上的沙河公社取土场,整个山头已被削平,各大队占据一个地盘在用多种方法取土。有用洋镐挖的、有用八磅锤钢钎崩的,还有的在挖炮眼,准备在上工前和收工后人少时放炮炸的。反正用一切手段和方法把荒山上坚实的黄土从混杂在一起的巨大石块中挖掘出来,再由民工们运到谷底坝基上去筑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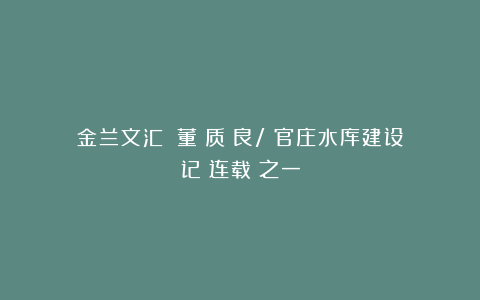
由于我人太小,又是新来乍到,自然就被分配去装土,就是用铁钯子把土装到畚筐和板车里去,这个活算轻活,是给妇女和老弱者干的。其实这装土也不轻松,大家为完成定额拼命爭抢,走到抛下空筐换一担满筐就走,不能有等待时间,否则就落别人后面了。遇有不能立即换筐,稍一迟延就嚷开了:“哪门在搞?没吃早饭啦”?这还是温和的,遇到性子火爆的:“你浑身没得四两力,哪象个种田的,早上没日喉啊”?这时,你不能回嘴,只能驼子不起腰,卯起搞。
我今早一上工就感觉到一种轰轰烈烈的大跃进气氛,工地上你追我赶,熙来攘往,一派紧张繁忙景像。你自己置身其中也成了组成这幅图像的一个元素,只能拚命去适应这种环境,没有退路。我是同一些妇女、老头们分在一起装筐的,这些女人除了一些十几岁的小女孩就是几个新媳妇。按照农民们的习惯,一般养了孩子的妇女是不会离开家的,但婚后尚未生育的新媳妇们除外。男人们对我们这些弱劳力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年逾七十的四类分子赵月卿是下饭菜,动辄喝斥教训;对我和几个尚未成年的小女孩则一本正经,老是催促快装快干;而对几个新婚尚未生育的俏媳妇,那就馋涎欲滴,丑态百出了。四队魏家富之妻尤运兰、五队刘大平之妻龚新梅,都是新婚不久的新媳妇,尚未生育,如花似玉的容貌和惹火的身段撩拨得一些男人馋涎欲滴,欲火难捺。几个胆大的故意走到她们身后磨矶,非但不嫌她们的土装慢了,还嘻皮笑脸的挑逗她们:“唉呀,你慢些蹶,莫把尿蹶出来哒。你那个狗日的大爷嘎(丈夫),真是他妈的畜牲,把我们的新姑娘夜的整哒白日的还要累,你莫跟他个王八蛋哒,跟兜我,我日的夜的把你供兜”。一边坏笑着还冷不防伸手去女人屁股上摸一把。女人扭身推一把坏种们,嗔骂着:“把你妈和你妹儿供兜去”!每当这时男人们都开心的哄堂大笑,毫不在意耽误了挑土。
后来,我知道了每天挑土的定额是四十担,人们为了少跑几趟,又能完成当天的任务,开始玩起滑头来,一次挑两担。领导们好象很傻,明知挑两担必然装的不满,非但不计较反而还表扬,这样一来,大家都学着去挑双担。其实,双担比单担多不了好多土,只是苦了我们装土的人,每筐不装满而要增加一倍的筐数,忙得我们连伸腰站一下的时间都没有,半天下来,我已经累得虚脱了。
中午,食堂送饭到工地来了,是炊事员用箩筐挑来的,两个男的挑饭,一个女的挑菜和开水。真是救星啦,早上吃的一缽饭早就化成汗水洒在土场上了,中饭一到,人们一涌而上的领来各自的一缽饭一勺萝卜,酣畅淋漓的吞下肚去。管你吃饱吃不饱,一人就一缽,中午炊事员挑不动,每人就一缽,不能多挑几缽来饭量大的分食,只能是绝对平均主义。我虽年龄小,饭量可不小,一缽饭也就吃个大半饱,不过单看这点我还是沾光的,七分的劳力却吃同大人们一般多的饭。
一天的劳作是有紧张和舒缓的,上午是一天的高潮,人们精神饱满,去来如梭,到中午吃过饭后,尚有半个小时空余,各人找个僻静处,棉衣一裹,躺地下迷糊一会。一点钟上工号吹起时,又呵欠连天的爬起来,懒洋洋地捡起钩子扁担去挑土。但只要一趟下来就恢复了常态,数着兜里的土牌子,看还差多少,然后争先恐后地赶起来。挑土的距离约有四、五百米,这是中等距离,根据地形,各土场的路程并不相等,最近的有三百米左右,最远的有一华里以上。离得越近,坡度越大,便无法用车子运土,离得越远,路越平缓,也就更多用板车和鸡公车(独轮车)运土了。我们沙河大队的土场是在中间地段,坡度较陡,约在二、三十度左右。运土下坡时一定要把车把杆抬高,让拖把在地上刮擦,产生摩擦力以减速。空车返回时两个人得使尽全力方能把空车拉上山来。 我也常被派去拉车,虽然回程时相当累,但运土下山时只叫我在后面跑,跟上不掉队,不叫别的运土车撞上就行。土运到河谷底部坝基上后,要以三十公分一层的厚度摊铺均匀,有一批人专门负责此道工序,名曰捡釆,铺好半幅后,就由两台苏联产的旧履带拖拉机碾压。
那时没有压路机,这两台拖拉机神气的不得了,昂着机头,喷着黑烟,从坝右边到左边咔、咔、咔分把钟就跑完了,然后再用倒档慢慢开回去。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实物的拖拉机(以前只在电影上见过),目不转睛地都看呆了,见它飞快的跑过后,后面一道笔直紧实的压痕让人叹为观止!看看旁边斜坡上八个男女民工笨拙地抓起一方石硪,好半天才拍出毛糙糙的一小片。两相比较,真是不可同日而语!无论在压实度还是速度效率上都让我感觉我们中国太原始落后了,唉,解放都十六年了,我们中国农民还在象看圣物一样的羡慕几台苏联旧拖拉机。听说这两台旧拖拉机还是省水利厅调来的,整个宜昌地区还没有这东西。
我就这样,一会儿装土,一会儿推车,逐渐也就习惯了。看河谷两岸,密密麻麻的挑土民工象蚂蚁般奔忙在几十条朝坝底汇聚的土路上,甲虫一样的各种板车,独轮车把一车车黄土输送到谷底的大坝上。从没见过大场面的我今儿是开了眼界,心中的隐忧在慢慢退去,没有什么了不起,别人奈得何的我也奈得何。正如俗话说的,和尚不是人做的?下午四点多钟,土牌子已够数的人们就慢慢开溜了,我们这些装土的人不能走,但挑土的人少了,我们也松活些了,一过五点,工地上便暗下来,我们也就正式收工了。
回到驻地刘家窑棚里,才感到一身的酸软疲惫,躺在铺上就不想动,邻铺王家茂见状对我说:“你快些去端饭啰,去晚哒食堂就要起锅烧洗脚水哒,缓会你就只有吃冷饭哒,总样?你明儿还奈不奈得何”?我强撑着说:“还好,就是小腿有点酸”。他说:“你今儿还是好的哟,搞的手上活,就只推了几趟车。我开始来的几天,一天的土挑下来,连肚巴子(小腿肌肉)酸疼打不过弯来,走路要扶到墙,解大溲都跩不下去,过几天你就晓得哒”。嘿,管他妈的,走哪算哪!我一骨碌爬起来去食堂吃饭了。在食堂,我一边吃着半冷不热的饭,一边听连长卢治典给大伙说:“我说你你你、(他说话有点结巴加弹舌)你们都听到啊,有些同志要赶快把支拨(购粮凭证)弄哈来啊,卯不弄哈来,寡是吃人家的总么行呢?一赶仗你就拉稀,哪个是你救急的茅室啊”?说到这句话时,他用歉疚的目光扫了一眼我们几个正在吃饭的人。“我的意思是说:人家也是淘达力把粮食挑到小溪塔粮管所换的支拨,你不能卯吃别人的,自已也要抓紧把支拨弄哈来,不然起,我就叫孙学伦不准借饭票哒!我也不晓得说打好多回,你默倒我是吃达嚼牙巴骨的饭,来跟你们日咕一遍又一遍”?听完我才明白是说有些人偷懒耍滑,不挑粮去小溪塔换支拨,老是在食堂借饭票吃,直接减少了食堂的粮食库存,事务长孙学伦不好得罪人,所以让连长来打招呼的。卢治典原是沙河大队长,很有些威望,一般人还是惧他的。
我昨天来工地的时候,是自己挑着行李和三十斤大米来的,不存在换支拨。虽然只挑了这点东西,但从沙河来官庄有三十多里路,且全是翻山越岭,走小路来的,人还是很累的。那时虽然有了小溪塔到官庄的碎石公路,但是没有汽车跑。椐说整个宜昌县只有三台汽车,其中还包括县委会的一台苏联嘎斯。一般人们出行全是步行,我挑着行李和粮食,走沙河三队翻百步梯,到梅子垭水库,再穿郭家冲到陈绱坪上公路,再经岩花直行十多里才到官庄。其实我们从小就在梅子垭、郭家冲一带挖麦冬、挖子弹壳、捡松蕈,最远曾到过陈埫坪。所以我虽是第—次到官庄,但我几乎就没问过路,一个人上午出发,下午三点钟的样子就寻到了沙河大队在官庄刘家窑的驻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