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1840名订阅者负责,期盼切近人生的好稿,期待作者关注,期待读者回应
纪实散文《东风渠轶事》连载之十一、十二
文/董质良
文/董质良
十一、又躲过一劫
二0二五年八月二日是东风渠普溪河渡槽垮塌四十五周年的祭日。作为当年参与修建此大桥和垮塌后又前去救援的人员,我亲历了那艰辛的抢建大会战和垮塌后悲惨的现场大救援。虽然时间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当时的场景与过程仍然印象深刻,历久弥新。现在将它呈现出来供年轻的一代了解身边和本地发生过的一些历史事件,或许并不精彩,但却真实,希望读后能让你有所感触。
一九七0年四月底,我们沙河营完成了红卫隧道的开掘工作,被指挥部调往普溪河协助抢建大渡槽的后期工程。普溪河渡槽是东风渠最大的水利及公路设施(当时定名东方红渡槽),此桥呈南北走向,横跨于四、五百米宽的普溪河上。设计为上、下两层,上层是东风渠引水渡槽,下层是宜保(康)公路桥。渡槽全长近千米,高五十七米,上下两层均为拱式结构。
一九七O年正值文革中期,极左气氛正浓,反对正常的科学观点,将按科学规律办事斥之为洋奴哲学、白专道路。东风渠普溪河渡槽,是整个工程最大的控制性建筑设施。如此巨大重要的工程设施项目,竟然是在打破迷信、依靠群众的思想指导下,由鄂西水利四团三连的一个小技术员简明新设计的。
又正值大抓三线建设,提出与帝、修、反抢时间,大干快上,只追求速度,不讲究质量。如此巨大的桥樑工程在当年缺少工程材料,没有施工机械的条件下,完全靠肩挑背扛,人力作业,仅用十四个月就完成了百分之八十左右的工作量。把我们沙河营调来就是要协助其他营在两个月以内的时间里,完成下余工程,一定要保证七月一号前完工并通水。
稍事安顿后,我们马上就投入了热火朝天的大会战。我们男民兵被分配拌混凝土,女民兵则从几十米深的桥下吊水上来搞砼体养护。可能因为我们是前来支援的客军,没有把最苦最累的挑伕工作分给我们,而是让我们做不磨肩膀的手头活拌料。可是这拌料也不是伢子玩的,人手一把魚儿锹(条状平锹),每人每天要完成三个立方米的工作量。河沙,卵石,水泥规定要拌和七遍(干三湿四),但事实上并无严格的施工监督,我们总是和个三,四遍就去逑,反正只求快,没拌均勻就被挑走了。尽管如此毛搞,在五,六月初夏炎热的天气里完成三个立方的工作量还是相当累的,一天挥汗如雨,两臂肿胀、酸疼。仗着人年轻和偷工取巧,我们每天下午四,五点钟就完成了定额,下班回驻地去。
整个大桥工地是三班作业,主要由鸦鹊岭团担纲。白天看长长的挑伕队伍象蚂蚁一样,每人一个坎肩,挑两个小萝筐,在数百米长的脚手架搭成的高架桥上川流不息,上下奔忙。夜晚整个工地一片灯的海洋,人声鼎沸,流光溢彩,刹是壮观。每天下班后,我们一伙年轻人说说笑笑,步行五里地回分乡土城岗驻地,吃过晩饭后,不知疲倦的我们又去分乡场逛街,或是下黄柏河洗澡。
从山沟里改换环境来到街镇上,人也显得十分亢奋,一天的劳累也就烟消云散了。分乡小镇古色古香,穿镇而过的小河上,一座由粗大的木樑和装饰着花格木雕的翘角房顶组合而成的桥樑,与当时浮燥的极左思潮下的社会风气和环境格格不入,反差极大。我每每看到此桥就有一种神定气闲,心旷神怡的感觉。可不知何年,此桥也变成了钢筋水泥的玩意,这也就是历史的进程吧。
经过一个多月的鏖战,浩大的普溪河渡槽工程终于完成了。我站在桥下,仰望美丽壮观,长虹般横跨南北的人工天桥,确曾生出过内心的赞叹和些许的自豪,心想古代悲壮的万里长城也不过如此吧,如今我们也用双肩和双手筑起了一座人间天桥!渡槽完工后约一个星期,七月一日,大桥指挥部在桥下河滩上召开了庆祝大会,庆祝大桥胜利完工,欢乐的民工们兴奋异常。晚上接着又放电影,演文艺节目,县供销社在会场供应副食饼子不收粮票,那气氛真象过节一样。我看完电影,怀揣两个饼子,同七队林秀武、许永福三人上桥去找地方睡觉。天太热,我们不想回土城岗去,再者,大桥完工后,徐发英营长高兴,对民兵们放任自流,未加管束了。谁知我们去晚了,桥面已睡满了乘凉的人们,没地方了,我们只得到桥下拱樑上去睡了一夜,丝丝凉风,惬意极了,睡得好巴适。
殊不知这一夜又是我们与死神擦肩而过的一夜,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大桥有质量隐患,而七月一号距大桥完工才短短几天,砼体结构养护期远未达到,是非常危险的。就在七一当天,指挥部已指令通水试验。当晚水头到达渡槽,只是在水流尚未达到设计流量前,上游堤坝出现了决口。水流一下减少,渡槽过水不多,重量不大,所以当晚未发生大垮塌,我们也就捡回了一命。
而一个月后的灾难发生时,我们沙河营早已调到黄艾公路建设工地去了。因而可说我和我的团队都是吉星高照的幸运儿,两个艰险的工地都毫发未损,感谢毛主席!七月三号,我们挑起铺盖卷,步行三十多里路来到黄艾公路付家冲驻地安营扎寨。这里的工程和生活之艰苦,简直无以复加,我在这里再次体验了许多稀奇古怪的荒唐事,咳,那都是后话,让我们还是继续普溪河话题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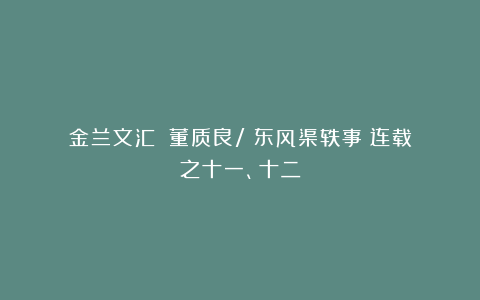
这里,我应该把当年的普溪河渡槽完工后的两次庆祝大会向大家介绍一下。就在六月下旬渡槽完工后的一星期,七月一日,大桥指挥部在桥下召开了庆祝普溪河东方红渡槽竣工大会。因为参加大桥建设的大量民工尚未撤离,加上本地看热闹的农民,所以庆祝大会的规模相当宏大,好几千人闹腾了一天。这天渡槽也象征性的通了一下水,但因故中止了,所以当天没有发生事故。
一个月后的八月一日,东风渠宜昌县指挥部仍在普溪河大桥下举办了东风渠宜昌县标段全部完工庆祝大会。火热的天气加上火热的氛围,无论是工程各级领导还是建没者们,都是真正的高兴和激动。普溪渡槽这个工程的控制性建筑没有拖工程的后腿,早在一个月以前就完成了。沸腾的会场,红旗的海洋,一阵阵歌声和口号声此起彼伏。晚上当然又是文艺演出,四里八乡的农民像赶庙会一样涌来普溪看热闹。因天气太过炎热,文艺晚会散场后附近的农民以及他们的亲友们,都涌到大桥上面乘凉睡觉,所以,到凌晨四点才发生的垮塌,仍然死亡了四、五十人。幸运的是,由于大桥完工已一个多月了,建桥的大量民工都已调往别处,当晚的垮塌中基本没有伤及他们,当然,也包括我们兄弟俩。
十二、大救援
话说我们沙河营到黄艾公路施工刚一个月,八月二号早晨六七点钟,我们吃过早饭正准备出工,突然,从我们刚修筑的毛坯公路上开过来四、五辆崭新的汽车。原来是宜昌钢铁厂(只存在几年就垮了)进口的日本八吨自卸大卡车,停在了我们驻地旁。车上下来一个干部模样的人,问道:“你们营长呢”?营长徐发英当即上前同他谈了一会话,转头对大伙喊道:“全营所有民兵马上上车,普溪河大桥垮了,赶快去抢救我们的阶级兄弟”。
闻听此言,大家都一愣,一时间竟反应不过来。天啦,我们亲手建起的雄伟大桥垮了?不可能啊!可事实上就是垮了(就同泰坦尼克号就是沉了一样)。赶快上车,我们迅即爬上车去,都没了平时那种乘汽车象开洋荤的感觉,胸间象阻了块石头一样。
汽车翻过分乡北边的山坡,一目所及,垮塌的大桥惨兮兮的景象一下跃入我们眼中:几根高矮不一,残存的桥礅刺向蓝天,上面扭曲变形的钢梁象死人伸向天空的手,往日长虹般美丽的人工天河已不见踪影。天啦!普溪河大桥,伟大而雄奇的建筑,完美与神圣的象征,倾刻间在我们的心中被强行颠覆了,在视觉和情感的双重冲击下,大家的双眼都蒙上了伤心的泪水。
汽车缓缓驶入普溪河河滩,一幅紧张忙乱的救援景象呈现眼前。宜昌各大厂矿调来的吊车停得到处都是。我还是第一次近距离的看见吊车,虽然都是些四吨解放吊(但那时汽车都稀罕,何况吊车)。面对重达数十吨如山一样的残体砼块,这几台小吊车显得如此渺小。今天凌晨大垮塌发生时,重达千吨的上层拱梁和渡槽砼体从五十多米的高空坠下,砸断了下层的公路桥拱,连同在公路桥面上熟睡的人们,一起陷入深深的河床之中。河滩的一片空地上,已摆放了一大片用白布包裹着的尸体。。由于天气太热,尽管才只有六七个小时,尸体已开始腐败,空气中有了丝丝难闻的臭味。
我们来到现场也不知干什么好,表面的搜救已差不多了,接下来是寻找被坠落的砼块掩埋的人们。无奈当时条件太差,尽管各大厂派来了他们可能是仅有的几台吊车,但是面对几十上百吨的巨大砼体残块,这几台四吨小吊车只能望洋兴叹。尽管如此,一些悲伤的失踪者家属,还是协同救援人员一起,不放弃任何一丝希望,在如山的水泥残块中坚持搜寻。吊车轰鸣着吊起一些较小的碎块,不时又有新的发现。每当这时,人们就蜂拥而上,刨出一具发黑的尸体,用担架抬往那片空地。我看见大多尸体都发黑萎缩,近乎赤裸,盛夏之时,本来穿的就少,救援时几拉几扯就没什么布片了。
我在河滩上到处转悠,不时望一眼那些高耸的残破桥礅,突然发现二号公路桥礅一二十米高的卷拱洞里有一根很粗的麻绳直垂地面。正不得其解时,旁边有知情者讲:上面捲拱洞里睡的两个人在天崩地裂的大垮塌过后才醒来。因为才凌晨四点多,四周还一片黑暗,巨大的轰鸣和气浪把两人吓呆了。两边的桥拱路面皆已砸断坠落,他俩站在了一根四面悬空,高达一二十米的孤墩之上。等到救援的人们赶来时才发现无法将二人救下.没有这么高的梯子,桥礅又四面悬空光溜溜的无法登攀,只好呼叫二人坚持住,等天亮后再想法救他们下来。这两个幸运儿最终是得救了,只是我们去的太晚没有看见。
我还听人讲有一女孩被垮下的残块压住下肢,她大声呼救,人们赶到后正用尽办法想把她救出来时,上方渡槽断裂后溢出的大水驟然而至,人们眼睁睁的看着她被无情大水吞没。
我们的大桥建设指挥部设在公路桥北侧的桥拱之下。当时被造反派夺权的宜昌县副县长谭某某(那年搞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时,曾任驻沙河公社工作组组长)被分配到水利工地来当指挥长,就在此办公、住宿。一九七O年八月一日,庆祝东风渠宜昌县段全部完工的庆祝大会的会址,仍选在普溪桥下的河滩上。作为总指挥长的他,今天是酸甜苦辣咸五味杂陈,从县长高位上下来,发配到这水利工地屈就一个临时的指挥长,心中的委屈和失落自不待言。而在这段施工期间,无数的困难和频繁的事故几乎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上面压任务,催工期,给他最大的支持就是毛泽东思想,政治挂帅。让他一个没有专业水利建筑知识的门外汉,来挑起这样大的一个水利工程的重担,可想而知他承受的压力该有多大。
好了,不管怎样,工程总算是完工了。今天,他一身的轻松,兴奋,召开盛大的庆祝大会,军民同乐都在情理之中。会场上红旗如林,歌声、口号声震天动地。欢腾了一天,晚上又是放电影,又是县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县剧团)表演文艺节目,热闹非凡。只闹到十一点多钟才散场,我们的谭指挥长在欣慰,疲惫的状态下回到桥下指挥部的寝室中沉沉睡去。突然,天崩地裂的一阵巨响把他从睡梦中惊醒,还没回过神来,就被腿部的一下重击击得失去了知觉。待到人们把他从废墟中救出时,他醒来的第一感觉不是肉体的疼痛,而是心灵的剧痛。转瞬间,他感觉自已坠入了十八层地狱,工程、身体都完蛋了。他知道自己万难逃脱大桥垮塌的责任。幸运的是他最终保住了性命,他睡觉的地方处于拱樑和桥墩根部的夾角之内,只压坏了腿部,侥幸的捡了一命。而另几名县里来的文化馆干部就没有这种幸运了。可怜几位有真才实学的年轻人,连同他们尚未完工的工农兵塑像,一起被埋在了废墟之下。我到公路桥南端入口侧畔去看了残存的工农兵塑像根部,当时就一感觉,再强大的政治信念,在大自然和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也显得仓白无力!有关谭指挥长以后的情况,由于我们继黄艾公路后又去了四O三厂初建工地,再没听到他的消息了,估计他又老又残,再难有鲤鱼翻身的机会了。
来接我们的就是这种日本八吨三菱自卸车,据说是发错港被中国海关截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