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朝二十年:盛极而衰的命运转轮
公元1115年这个冬天,完颜阿骨打还在琢磨,要不要一鼓作气跟辽人拼个你死我活。“这仗不好打啊。”有人在帐篷外小声嘀咕。可第二天凌晨,他还是把女真的各部头头都召过来了。有些人脚下还留着北方冻土的泥巴,有些人手里攥着刚切好的兽肉。谁都没想到,这帮北野里出来的汉子,竟然能一夜之间把辽朝扯下马,第二年就在哈尔滨那片地儿,插了“大金”的旗。
后来金人南下,1127年靖康耻,京城满城风雨。多少人家一夜间天翻地覆,有的被带往北方,有的就此消失。宋人的愤恨,江南的无助,都写在了史书角落。
这么看,金朝气势如虹。可你要再翻两页,却发现这段传奇转瞬即逝。二十年光阴,从高台的盛宴到土墙的落魄,金朝到底哪一步走错了?
头些年,金太宗还算是个有章法的主。他一手攥着刀,一手开始琢磨文礼——扩疆域的时候连饭都顾不上吃。最早那阵,他们骑马冻脸,打仗啃牛肉,南下之后一口气把中原北地都拽进了新国版图。你要问那时的金人怎么活?多半都硬气——不光能打,还能耐下心,慢慢学那些汉家的规矩。
不过风水轮流转,世道没几个人能把控。到了金世宗手里,朝堂变了模样。他挺信儒家的那一套,喜欢营造文气,整天有大臣在殿上讲学。说是“大定之治”,其实金朝上下都在“转型”——打仗的口号逐渐被诗书礼仪取代。世宗也不太管那些练兵的家伙,反而更爱在宫里琢磨怎么做个好皇帝。
有人说那是金人的黄金时代。可这黄金,看似光鲜,底子却混进了点沙子。
很多事一开始你看不出来。1189年,金章宗完颜璟走马上任,表面上朝堂还是很精气神。可有细心的人已经发现变化——过去宫里总有拢弓骑射的气息,现在满殿都是读书人的味道。章宗喜欢汉人生活,一心向往南方的繁华。他对女真的老路子,反而有点看不上,满国上下居然流行起了穿汉袍、写汉字的风潮。
这个“汉化”,倒也不是错事。谁不想活得讲究点?可问题是,金人本来靠马背立国,金章宗一心只爱书斋,连军队练兵都成了摆设。总觉得,朝堂变得越来越陌生,金人的根在悄悄搬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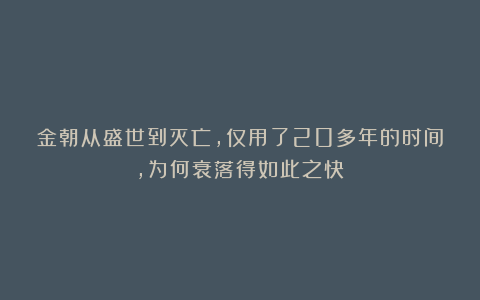
章宗身后那年,宫里连哭泣都带着疏离。金朝江河日下,军队里没人愿意带头出征,朝堂上大半都是亲戚外戚在窃窃私语。风声紧的时候,很多当官的只管保自己,遇到大事谁敢拍板?百姓心里也跟着漂——那些生在马背上的刚烈,早被京城的浮华酒气遮住了。
你说金朝是怎么从春风得意到一地鸡毛?有人在茶馆里敲着桌子,说“是把根丢了”。过去金人拼死南下,皇帝和草民一样心头有一股劲儿,可慢慢大家都被纸醉金迷的生活喂软了。原来骑射很重要,现在读书人比练兵的还多,人人都想做个富贵人。这种转变,让金朝像个脱了壳的蚌,外表还算光亮,里面却空了。
到了金章宗以后,“汉化”不光侵染了贵族,百姓也跟着入了迷。皇帝夜夜歌舞,把朝政丢给亲信,大臣整天想着门生故旧,没人惦记着北边的威胁。蒙古人就站在边上磨刀霍霍。南边还有宋朝虎视眈眈,复仇的火早就点起来了。
再说说那些糟心的决策。别看金朝头些年打得顺风顺水,他们对外的处事其实很糊涂。有个细节——当年辽国死活不让蒙古拿铁器,可金朝却开了这口子,贸易做得风生水起。结果蒙古人兵器一先进,金朝反而成了刀俎上的鱼。
有人问金朝后来的皇帝是怎么想的?其实很多时候他们根本没想清楚。边境屡屡告急,朝里还推来推去。蒙古铁骑一波波压下来,南宋也没闲着。金宣宗那会儿,有机会联合宋朝对抗蒙古,大家都在指望他能做点什么。结果他回头就去打南宋,北边丢了地盘,南边也没个朋友。说是补缺,实际上把自己困成了孤家寡人。
这时候谁还管民生?黄河决口,百姓流离失所。有人从京城赶出来,发现家乡变了模样。朝廷解决不了就开始滥发纸币,一夜间物价飞涨。你说百姓还怎么活?有的人揭竿而起,有的人逃到天涯地角。宫里倒是灯红酒绿,早没人关心菜价和池塘的水。
金朝灭亡也就成了必然的事。最后一任皇帝金哀宗,看着四面楚歌,朝堂上再没真心人才。兵士力不从心,众叛亲离,外面是蒙古的刀,里面是自家的恨。他把皇位交了出去,自己折了命。金人的故事,到这儿也就剩下史书上的叹息。
有时候回看那二十来年,你会觉得金朝的崩塌既快又让人难过。不是敌人太强,而是自己散了心气。金人本来是能拼能闯的,可惜做了大宅门的主人后,渐渐学会了温吞。连风都不再北方吹来,末路烛火,谁都盼着能有一次翻盘,可惜这盘棋,最后还是散了。
历史里总有那么一段故事,每一次盛极而衰,都像一场宴席刚燃起又被泼灭。大金,来得快,去得也快。我们常说,不怕千变万化,最怕本性改了又不自知。你说金朝能不能活得更久?这答案,还埋在那些北方早已风化的塔基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