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白求恩,咱们都知道他是高尚的国际主义战士,但他为啥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非要跑到战火纷飞的中国来,一门心思救咱们的战士?这背后的道道,比课本里写的要实在多了。
1938年他刚到晋察冀那会儿,看到的场景能把任何一个医生的心揪碎。前线下来的伤员,好多连块干净的布都没有,伤口烂得流脓,上面爬着蛆虫。护士手里就那么点碘酒,省着用跟宝贝似的,更多时候只能拿盐水糊弄。有个年轻战士腿被子弹打穿了,疼得直哆嗦,却连一片止痛药都没有,就咬着根木棍硬扛。白求恩后来在日记里写:“我在加拿大见过穷人没钱看病等死,但没见过把命不当命的地方——这里的战士不是死在敌人枪下,是死在没人管的伤口里。”
他不是第一次见这种仗。1936年西班牙内战,他带着医疗队去前线,首创了流动血库,硬生生把伤员存活率提了近四成。可中国的情况,比西班牙还糟十倍。缺药、缺器械、缺懂行的人,连个正经手术室都找不到,有时候就在破庙里搭块木板当手术台。但他没抱怨,来了就撸起袖子干,跟聂荣臻说:“你们缺啥我就补啥,战士们在前线拼命,我在后方多救一个,你们就多一分底气。”
这股子执拗,跟他心里的坎儿有关系。在加拿大的时候,他是有名的胸外科医生,按理说日子过得不差。可他见不得那些糟心事:有钱人家头疼脑热就住院,花一堆冤枉钱;穷人家真得了大病,医院门都不让进,就在街上活活熬死。有次他在医院门口看见个老太太,怀里抱着发高烧的孙子,跪在地上求医生,医生却推推搡搡让保安把人赶走。那天他没上班,把老太太和孩子领回家,自己掏钱买药打针。从那以后,他就不待见加拿大那套“医疗当生意做”的规矩,觉得“这哪是治病,是把人分成三六九等”。
后来他去了趟苏联,看见那边工人看病不花钱,孩子生下来就有医生管,心里更不是滋味。回国就加入了共产党,在蒙特利尔搞“给失业者免费看病”的活动,结果得罪了不少医院老板,丢了工作。他跟朋友说:“我当医生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让人活得像个人。”所以1937年听说中国在打日本,他几乎没犹豫——在他眼里,西班牙反法西斯,中国反侵略,都是一回事:“都是弱者在跟强权拼命,我不能看着。”
在晋察冀的日子,他活得像个“上了弦的陀螺”。1939年齐会战斗,炮弹在离他五里外的地方炸,震得他所在的破庙房梁直掉土。他就在那庙里,连续69个小时没合眼,做了115台手术。中间有人劝他躲躲,他眼都没抬,手里的手术刀没停:“你们在前线能死守阵地,我在手术台就不能死守?”有次给一个战士取子弹,炮弹碎片溅到他胳膊上,他抹了把血,继续开刀:“这点伤算啥,战士肚子上还开着口子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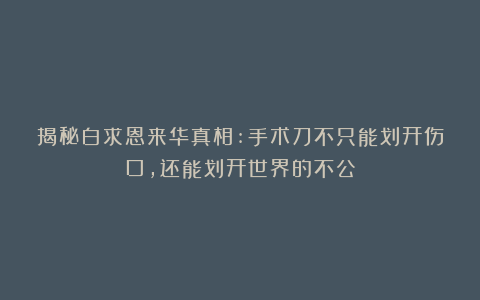
他不光救人,还琢磨着怎么让更多人会救人。办培训班,教当地护士怎么消毒、怎么包扎;把带来的药配方写下来,让他们照着配;还自己画图,设计了个“卢沟桥”药驮子,马一驮就能走,里面啥器械都有,战士们管这叫“会跑的小医院”。就这么折腾了一年多,晋察冀的伤员死亡率,从原先的三成降到了不到一成。
有人说他傻,放着加拿大的好日子不过,来中国遭这份罪。他每月有党中央特批的100块津贴,在那会儿是笔巨款,可他一分没动,全给了医院买药品。自己穿的军装补丁摞补丁,跟战士们一起吃黑豆窝窝头。警卫员偷偷给他煮了碗鸡蛋面,被他劈头盖脸骂了一顿:“我是来当医生的,不是来当老爷的,战士们吃啥我吃啥。”
1939年10月,他给一个丹毒患者做手术,不小心被手术刀划了个口子。那时候条件差,没当回事,结果感染了,没几天就转成败血症。躺在病床上,他还惦记着医院的事,给聂荣臻写遗书,说“把我的医疗器械都留给医院,能救一个是一个”。警卫员哭着要背他转移,他摆摆手,气若游丝还在说:“别管我,快去照顾伤员……”
现在回头看,白求恩图啥?他不是为了名声,也不是为了钱。他就是觉得,医生就该站在最需要的地方,不管那地方是加拿大的贫民窟,还是中国的战火堆。就像他跟医疗队的人说的:“咱们手里的手术刀,不光能划开伤口,还得划开这世界的不公。”
这种人,放到哪个年代都稀罕。他用自己的命,给咱们证明了一件事:这世上真有不图啥,就为了心里那点念想,能豁出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