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名宿罗振玉的诸多藏品中,有一件青铜簋的铭文与公号前文的史䛗簋相关,内容同样提及毕公,并且能与西周早期的黎国联系起来,即本篇的主角——献簋。
一.雪堂旧藏
献簋最早著录于清代光绪年间刊印的《梦郼(yī)草堂吉金图》一书,该书的作者正是其收藏者罗振玉。
罗振玉(1866~1940),字叔蕴、叔言,号雪堂、贞松老人,祖籍浙江上虞,生于江苏淮安,是近代著名学者、考古学家和金石学家。他早年投身教育,创办《农学报》并推动新式农业教育,1906年出任清廷学部参事,后任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辛亥革命后,他一度避居日本,专注于学术研究,与王国维并称“罗王之学”,在甲骨文、敦煌学、简牍学等领域贡献卓著,著有《殷墟书契》《三代吉金文存》等书,奠定了近代古文字学研究的基础。
罗振玉亦是近代最重要的青铜器收藏家之一,藏有商周青铜器数百件,尤其注重带铭文的器物。如今,他的旧藏部分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等文博机构,部分流散至海外博物馆及大学,另有一些辗转于私人藏家之手,偶尔会出现在国内外拍卖市场。
罗振玉《梦郼草堂吉金图》书影
献簋于晚清时期出土,出土地点却因学者疏误导致争议。《殷周金文集成》第八卷在收录献簋词条时,误将出土地标注为“近出保安(梦郼)”,以致衍生出陕西志丹县(古称保安)与河北涿鹿县(古称保安州)两种说法。然而,核查罗振玉《梦郼草堂吉金图》原书(上图红框处)可知,目录明确注写“近出保定,未著录”字样。因此,献簋实际出自河北保定一带,当无疑义。
邹安于1921年出版的《周金文存》第三卷对献簋有如下记载:“初见只残铜一片,旋成器,是否原壁不可知。铭字至佳,楷字见周棘生敦。”据此可知,该器最初仅为残片,后经修复成形,因未见实物,残存多少无法判断。从献簋旧照明显的修补痕迹,也印证了书中记述。
值得一提的是,《周金文存》收录献簋拓片旁,钤有“宸翰楼所藏金石文字”鉴藏印。宸翰楼乃罗振玉的斋号之一,是其收藏金石、校勘文献和刊印书籍的重要场所。
二.形制铭文
献簋目前下落不明,准确的尺寸也无从知晓。
西周康王 献簋
整器侈口束颈,垂腹,两侧对称环耳,底承高圈足,下设增高的边条。颈部装饰四组环柱角型兽面纹,鼻基处高浮雕外卷角龙首,展开的兽面背脊上排列羽状鳍。圈足与腹部纹饰对应,唯鼻基处作凸出的短脊。环耳饰柱角龙首,下垂长方形珥。
献簋器形与史䛗簋(史䛗簋篇)相近,纹饰和布局与禽簋(禽簋篇)基本相同,为西周成、康时期标准器。
献簋铭文拓片
腹内底部铸铭文6列52字:
唯九月既望庚寅,楷
伯于遘王休,亡敃,朕
辟天子。楷伯令厥臣献
金、车,对朕辟休,作朕文
考光父乙,十世不忘,献
身在毕公家,受天子休。
铭文大意为:九月既望庚寅这天,楷伯前去接受周王赏赐,感恩并颂扬周天子。楷伯在同一天赐给献青铜和马车,献赞美天子恩德,制作了这件祭祀父亲乙的礼器,世代铭记不忘身在毕公家受到的天子恩惠。
这里透露最重要的信息,是献作为楷伯属臣,却称自己“身在毕公家”,暗示楷伯同为毕公家的一员。这就引出两个问题,楷伯和毕公到底是什么关系?楷伯“于遘”的王是哪一位周王?
解答这两个问题就需要梳理一下黎国的历史。
三.黎国故事
在公号前文《养奚方鼎
》(养奚方鼎篇)中,提到楷国就是传世文献记载的黎国。此外,清华简中的“
(
耆
qí)”,文献中的“
(黎)”“饥”“
”等,也均指黎国。
《尚书》有一篇《西伯戡黎》,原文如下: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讫我殷命。格人元龟,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后人,惟王淫戏用自绝。故天弃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丧,曰:’天易不降威?’大命不挚,今王其如台?”
王曰:“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祖伊反曰:“呜呼!乃罪多,参在上,乃能责命于天。殷之即丧,指乃功,不无戮于尔邦!”
《西伯戡黎》中的“戡”字意为攻克、平定,指西伯征伐并灭亡黎国的史事。该篇记述了殷商贵族祖伊在获悉周人攻灭黎国后,意识到王朝危在旦夕,遂向昏庸的纣王进谏。然而纣王自恃天命在身,对劝诫置若罔闻,祖伊只能悲叹商朝灭亡指日可待。
遗憾的是,由于传世文献记载阙如,关于黎国的历史仅有只言片语。甚至篇名的“西伯”到底指周文王还是周武王历来都争论不休。这个古老方国的真实面貌,唯有依靠出土文献方能逐步揭示。
清华简《耆夜》篇的发现,将《西伯戡黎》与西周金文中的相关记载建立起确凿的联系。通过对这些材料的互证,我们得以重构黎国历史的大致轮廓。
《清华简·耆夜》书影
节选此篇并转写成通行文字为:“武王八年,征伐耆,大戡之。还,乃饮至于文大室。毕公高为客,召公保奭为夹,周公叔旦为主,辛公[言泉]甲为位,作册逸为东堂之客,吕尚父命为司正,监饮酒。王举爵酬毕公……王举爵酬周公……周公举爵酬毕公……周公或举爵酬王……”
《耆夜》详细记载了武王率领毕公、召公、周公、辛甲、作册逸及吕尚等重臣在戡黎凯旋后举行的饮至礼。其中蕴含的关键信息主要有两点:
首先,伐黎的时间。开篇明确此次征战属于武王时期,饮至礼举办地点设在文王宗庙,证实此时文王已经离世,这就更正了传统认为“西伯戡黎”为文王时期的观点。同时表明在殷商末期,“西伯”作为周方国首领的称号具有延续性,武王身为文王正嗣,自然承袭了这一称谓。
其次,军事统帅的认定。简文强调“毕公高为客”,配合宴饮礼仪中武王、周公先后“爵酬毕公”的仪式安排,充分证明毕公在此次战役中的主导地位。
据此推测,毕公高在完成对黎地的军事征服后,很可能受封获得了这片新领地。西周建立后,往往采用“身居王朝,子就封地”模式,正如周公旦与伯禽之于鲁国、召公奭与克之于燕国,即由毕公本人留在周王朝任职,而派遣其子嗣实际管理新征服的黎地。
毕公高辅佐三代周王,在成王一朝离世。献簋是成康时期的青铜器,它记载楷伯亦属毕公家的一员。从时间上推算,这位楷伯很可能就是毕公高之子,为黎国的第一任国君。
公号前篇《史䛗簋》(史䛗簋篇)写到毕公高跟武王同姓姬。如果楷伯确是毕公高之子,那有楷伯姓姬的证据么?
西周中期以后的青铜器,铭文常有为父母妻女制器的内容。苏州博物馆藏有一件西周中晚期的师趛(yǐn)盨(xǔ),是师趛为自己妻子所做的礼器。
师趛盨盖铭与器铭拓片
该器上下对铭,作4列21字。两篇铭文布局特殊:右侧铭文采用从左至右的书写方向,这与常见铭文方向相异;左侧铭文则均为反书字体。拓片呈现反字的原因有两种:其一是拓片问题,陈邦怀先生在钤印所藏拓片时误将印章钤于纸背所致;其二是器物问题,铸造过程中工匠错误地将铭文范刻反造成。
右铭释文如下:
唯王正月既望,
师趛作楷姬
旅盨,子孙其
万年永宝用。
由铭文可知,器主名叫师趛,“楷姬”为师趛的妻子。其中“楷”代表其妻子的国名,“姬”则是她的姓,表明师趛迎娶了一位来自楷国的贵族女子。这一例证充分说明,楷国与毕公高确实同属姬姓,也印证了楷伯即为毕公高之子。
这一结论也有助于甄别先秦文献的真伪。《吕氏春秋·慎大览》称武王灭商“封帝尧之后于黎”,《六韬·决大疑》言“武王封汤后于黎”,这两条战国时代的叙述均与史实不符。
毕公高与周武王同辈,其子楷伯则与成王平辈,是康王的长辈。细审献簋铭文语境,所云“楷伯于遘王休”,“于遘”即“往见”,措辞并无卑下之意,这里的“王”极可能是晚一辈的康王。由此判断献簋为西周康王器。
黎国所处何地文献上有两种说法:一说位于山西长治市西南上党区,一说位于黎城县东北,相距约一百公里。两地地理临近,可能先后做过黎国都城,也可能都在黎国境内。2006年,山西考古研究所在黎城县西关村发掘一处西周墓葬群,铭文显示作器者为楷侯之宰,即黎国国君的家臣总管。西关村墓地的考古发现证实,黎国的地望就在这一区域。
综合青铜器铭文、出土文献与传世典籍的记载,黎国的历史脉络可大致梳理如下:该方国位于今山西省东南部,殷商时期作为商王朝的重要附属国存在。商周之交,随着周人势力的扩张,周武王派遣毕公高率军灭黎,并将这片新征服的领土分封予他。西周建立后,毕公高留任王畿,其嫡长子世袭毕公爵位,继续辅佐周王朝;另一子则前往封地,成为黎国国君。西周中期以降,黎国长期面临戎狄部族的侵扰压力。至春秋早期,在狄人的持续攻势下,黎国都城陷落,黎侯被迫流亡卫国。春秋中期,晋国崛起后出兵驱逐北狄,协助黎侯成功复国。此后,势单力薄的黎国成为晋国附庸。现存金文资料显示,最晚的黎侯活动记录可追溯至春秋战国之际,此后这个古老的诸侯国便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1]。
四.释字话史
1.唯九月既望庚寅,楷伯于遘王休,亡敃,朕辟天子。
“既望”,指满月后的第一天。
“庚寅”,干支记日。
“楷”,铭文隶定作“
”,从木从虍,下方的“几”形为声符,有些构形还在“几”下加“口”字[2]。秦诏版中“皆明壹之”的“皆”,字形作上虤下口,便是由
金文
“
”演变而来。“楷[kriil]”与“皆[kriil]”上古音相同,均以“几[kril
ʔ]”为声符,与“耆[gri]”“稽[kii]”“黎[riil]”则音近可通,“楷伯”便是“黎伯”。
“敃”,铭文隶定作
“
”
,象右手之形,其上斜笔表示拇指,当为“拇”字的表意初文。古籍中常用“敏”表示“拇”,“
”可释为“敏”。
“亡
”
一词常见于金文,
“
”
用作声符,字形又写作从目从又、从目从丑或从目从
。“
”读音与“敃”接近,和金文中“亡敃”表示同一个词。同样,“敃”的字形也写作从民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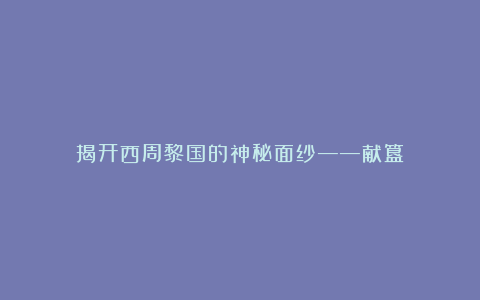
或从民从又。“
”的相关诸字在古籍中还写作“闵”“湣”或“愍”。
“亡
”即无忧之意[3]。
“朕”,甲骨文写作“
”,从舟从
,
亦为声符。“
”为双手捧针之形[4],与舟合文会意修补船缝,引申为缝隙。“朕”也用作代词,表示“我”“我的”。先秦时期,“朕”字并无尊卑贵贱之分,秦统一后,方用作皇帝的自称。
“辟”,甲骨文写作“
”“
”,从卩从
,卩为跪坐人形,
为镰刀类的工具,会意对人施刑。甲骨文人形旁的
“□”,在周初金文中写作“○”,可能象形被砍落的人头,先秦五刑中的“大辟”即砍头之刑,引申为法或执掌法的人。铭文中用作“君主”之意,即为“辟”的引申义。
2.楷伯令厥臣献金、车,对朕辟休,作朕文考光父乙,十世不忘,献身在毕公家,受天子休。
“献”,繁体字写作“獻”,与“甗(鬳)”本为一字。甗(yǎn)是古代的蒸锅,上部为甑,中间设箅,下部为鬲(器形参见2024西泠秋拍西周早期青铜甗)。鬲内盛水后加热底部,热气透过箅孔上溢,将甑内食物蒸熟。
甲骨文的“甗”写作“
”,是典型的象形字,又有增添虎字头繁化作“
”的字形,在卜辞中均用作“进献”之意。西周早期青铜甗自铭作“
”或“
”,增加了犬旁,隶定字即为“獻”,而同一时期的“献”写作“
”,两者构形相同,表明在西周早期二字尚未分化。
那么献簋铭文中,“献”到底是人名还是用作动词,表示“进献”呢?
其实,献簋铭文的后一句,一直存在两种解读。究其原因,一是“献”字词性争议,二是整段铭文用字的简省。
先说第一点。如果“献”当作动词,此句主语就变成了楷伯,铭文的大意即为:楷伯命自己的臣属进献青铜和马车,作为对周王赏赐的答谢,然后制作了祭祀自己父亲乙的礼器,世代不忘自己是毕公的家臣,受到天子恩惠。
尽管这样释读语意通顺,却与上一节考释的楷伯姓姬相矛盾。倘若楷伯的父亲为“光父乙”,表明他是采用日名的商人后裔,而非姬姓的周人。
因此,“献”应该用作人名。
再说第二点。单看“令厥臣献金、车”,句意确实模糊。若按整篇语境,“献”既然是人名,理应为受赏者,但此句在“献”和“金、车”之间缺少明确的动词。这种省略现象在周初铭文中较为常见,因而容易引发释读分歧。
“世”,铭文隶定作“枻”,左边从木,右边象树枝之形。“世”正是树叶的“叶(枼)”省去“木”的分化字,二字古音也极为相近。
“叶”,繁体作“葉”“枼
”或“枽”,甲骨文写作“
”。树叶周期性凋落重生,引申出世代之意。“叶”在春秋金文写作“
”,下半部为“木”,上半部已与《说文》小篆的“世”字形相同。本篇铭文中“枻”的右半部“世”省略了树枝上的饰笔。
“忘”,铭文隶定作“
”,为从言望声的形声字。
“身”,甲骨文作“
”,商末周初金文作“
”,指事躯干部分。铭文中引申为自身。
“受”,甲骨文作“
”,上下为手形,中间为舟,会意两人间交付物品。“舟”用作形符,也兼作声符。上古汉语中,“受”既表示接收,又表示给予,具体含义需通过语境来确定。后来,“受”分化出“授”字,用来专指给予之意。
[1]李学勤:《从清华简谈到周代黎国》,《出土文献》第一辑第1至5页,中西书局,2010年。
[2]陈剑:《甲骨文旧释“眢”和“
”的两个字及金文“
”字新释》,《甲骨金文考释论集》第177至233页,线装书局,2007年。(2025年4月18日,在题为“旧作补正两篇:重论所谓’赗’和’㲹’”讲座中陈剑修订了此前的释读。甲骨文“
”字可解读为“遍”,表示施事主语以同样的动作行为施及全体宾语,有“一一地”“逐个地”“普遍地”等含义。“
”去除饰笔后的部分,结合“
(胄)”字等,可推知为冠冕、帽子一类“首衣”。再结合“遍”字读音考虑,“
”应理解为“弁”之繁形。此外,通过一些特殊辞例,陈剑进一步将“徧遍”与“辨”联系起来,认为“
”的读法可以用“辨”字来统一,其词兼具“周徧遍”与“分辨”两义。)
[3]陈剑:《甲骨金文旧释“尤”之字及相关诸字新释》,《甲骨金文考释论集》第59至80页,线装书局,2007年。
[4]裘锡圭:《释郭店〈缁衣〉“出言有丨,黎民所
”——兼说“丨”为“针”之初文》,《裘锡圭学术文集》第2卷第389至394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
黄毫金(愙斋)
80后,出生广东雷州
中国舞台美术学会会员
广东省舞台美术研究会会员
湛江市书法家协会会员
雷州市书法家协会副秘书长、理事
《书法雷州》编委会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