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4日傍晚,广州城刚刚换上崭新的红旗。南郊一块稻田里,40军指挥部的油布帐篷被秋风吹得猎猎作响,韩先楚正端着一碗并不热的米饭,朝南面深色的海平线瞟了又瞟。照理说,这是值得痛快庆祝的时刻,可他眉头依旧紧锁。原因很简单——再往南五百多里就到琼州海峡,岛上的国民党第十二兵团仍在负隅顽抗,广东解放只是阶段性成果,战斗远未结束。
几天后,一份加急电报从北京送到帐篷里。毛泽东要求华南战场在1950年春季解决海南问题,最好不晚于夏至。指挥权落在第四野战军邓华和韩先楚身上,时间紧,任务重,外加一个不容忽视的新变量——金门战役的失败刚过去不到一个月,部队情绪明显受挫。
韩先楚没有在嘴上多说,他先到驻地各团连走访。行军锅里的南瓜饭、潮湿海风里的盐碱味、士兵想家的低声叹气,都被他听在耳里。彼时许多部队已经接到复员指标,连队里关于“革命到站”的议论毫不掩饰。更要命的是,对否能渡海成功的怀疑像感冒一样蔓延:没大型舰艇、没制空权、金门刚刚失利——“硬闯海南就是以木舟碰驱逐舰”,有人这样形容。
为了摸清基层真实想法,军部按照惯例下发《渡海登陆人员初步编成表》,让师、团填报。名单回到司令部那天,是1950年2月8日。翻开第一页,韩先楚愣了十几秒:所有登陆营、登陆连的“主官”栏清一色空着,只在“副”字后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名字。简单说,没有一个正职敢在“抢滩第一批”那一栏写下自己。
夜已深,帐篷里只剩煤油灯噗嗤噗嗤的声音。韩先楚把名册往桌上一摔,站起身捋了捋袖子。他的声音不算高,却透出压不住的火气:“既然都不想上岛,我这个军长先写!”说罢,他提笔在第一行“正职”一栏写下“韩先楚”三个字。随行参谋想劝,话刚出口就被一句低沉的“别吭声”堵了回去。整段对话不足十秒,却像一记炸雷传遍军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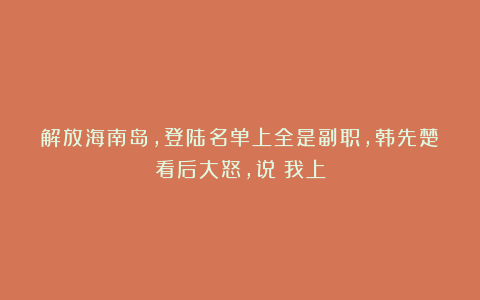
第二天名单复议。看到军长带头,原本犹豫的师、团主官纷纷补签。一上午,空白的“主官”栏被填得满满当当。人心向背的转折有时就在一瞬,该场面后来在40军回忆录里只留下寥寥一行:军长怒笔,众将失色,随后各自落款。
将士的情绪缓过来,还得解决“船从哪里来”这个棘手问题。中央海运部门嫌准备仓促,希望再拖半年,韩先楚心里明白:拖下去,海峡季风变化,敌人也会构筑更强岸防,况且大批老兵等着复员,一旦再延宕,战意只会更低。于是他干脆自作主张,把借船的任务摊派到团一级:渔船、木帆船,甚至盐商的舢板,只要能装下一个排就算数。两广沿海渔民家家点着桅灯,一周之内交出大小船只三百余艘,葫芦岛式“人民海军”再次成形。
3月末,登陆演练紧锣密鼓。参照台湾海峡之败,部队做出三条硬规定:靠夜暗突击、靠分散编队、靠超近距离火力压制。火炮几乎全是缴获自国民党的美械,射程有限,只能等到距离岸线两公里内再同时开火。参谋们测算后得出一个大胆方案:夜里19时启航,潮流自北向南,凌晨1时最顺,3时许接敌。天一亮就要拿下最近的两处滩头,否则飞机起飞,木船将寸步难行。
1950年4月16日傍晚,雷州半岛数十处渔港灯火尽熄。19时30分,第一组信号弹划破夜空。40军、43军两万五千余人分乘三百余艘木帆船,向琼州海峡南岸驶去。韩先楚身穿普通作训服,立于旗杆旁,右臂因旧伤抬不高,仍死死握着望远镜。炮火照亮海面时,船只之间只能靠口令和手电指挥,浪头打湿衣襟,咸味直灌嗓子。
凌晨1时45分,国民党海防舰队发现目标,射来第一轮照明弹。敌舰排炮过后,木船起火十余艘,但编队没有乱。渡海部队一边靠舢板灵活迂回,一边用92步兵炮和50迫击炮贴近反击,竟然在短短半小时内逼走了对方。2时30分左右,第一梯队抵近新盈、白马井两段海岸,数百条木船同时抛锚搁浅,官兵跳入齐腰深的海水,扛着枪炮往岸上冲。
6时整,天色微亮,40军全部登陆完成。岸防暗堡被爆破筒逐一点名,一线守军连成建制的抵抗都没来得及组织便后撤。全天战斗,解放军阵亡与失踪不足五千,岛上守军三万余人被歼灭或俘虏,大部分战斗在三周内结束。5月1日,海南岛宣告解放。
战后北京发来贺电,毛泽东仅一句“幸不我迟”,感慨已尽在不言中。军内统计,如果海南拖至夏季,美第七舰队极可能由台湾海峡南下侦巡,届时再打就不是这般代价。韩先楚出色完成任务,却并未在部队停留;6月,他又奔赴东北,为即将到来的抗美援朝备战做准备。
这位出生于1913年湖北黄安的篾匠之子,十四岁扛锄头,十六岁拿猎枪,二十出头带游击队转战大别山。定边破城、鞍山反攻、新开岭布防,从白山黑水打到南海波涛,他的打法一直保持同一准则:主官先行,士气最重。渡海名单上的那三个字,只是这种风格再平凡不过的体现。
自此,海南不再是地图上的灰色区域,而成为新中国南疆稳固的一环。不足千字的作战命令、几百条渔船、两万多名敢死将士,加上一位敢把名字先写在登陆名册上的军长,足以改写那段海峡两岸的格局,这也正是解放海南战役最值得铭记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