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者如父
作者:曹国东
(上图来自网络)
初三那年,我转入涟水河对岸的苏坡中学就读。
语文老师姓谭,中年男人,高大魁伟,据说是学校教导主任,却不是我们的班主任;头堂课是数学课,进教室的也是个中年男人,没有谭老师魁梧,也不矮小,走路一颠一颠,一高一低,原有腿疾,嘴唇厚实,有些外翻。听说唇厚之人福厚寿高,不知然否?
大约我是插班生,初来乍到,学校陌生,老师陌生,同学陌生,一切不熟悉,怯生生地,有点孤独地,一个少年男儿瑟瑟缩缩地蜷在教室角落。数学老师也不介绍,只说他是班主任。同学们或习以为常,我从后来的打探中才知他姓谢。
语文是我的强项,上课便精神亢奋,想象如潮;历史也是我的强项,曾被授课的彭老师夸赞为“历史标兵”;谢老师的数学课教得好哇,课堂活跃,让我这个对数学了无兴趣的少年儿也趣味日浓,信心倍增,更兴奋的是,让我这个“代数几何,想破脑壳”的偏科儿,中考数学竟考了86分(百分制)。这不能不赖谢老师的教学方法和潜移默化。当然,这是后话。
或许,让我轰动全校的是那一次,让谢老师真正认识我的也是那一次。
(上图来自网络)
寒冬腊月,白霜凝地,我与同学阳春一起去上学。走到涟水河边,蓦然见一个女的在水中沉浮挣扎。我的脑袋一片空白,迅速脱掉棉袄,跃进水中,把人给救了上来。
寒风一吹,全身顿起鸡皮疙瘩,这才觉出刺骨的冷。让同学一个人先渡河去上学,我抄起衣服书包跑回家去。母亲问了情况,心疼不已,让我赶紧躺床上,盖了两床棉被,仍在瑟瑟发抖,牙齿上下打架。
迷糊中醒来,心系上学,赶紧穿衣,一溜烟似的跑到学校。已是第二节课,我透过窗玻璃望见谢老师正挥舞着三角板讲几何。我犹豫了一下,壮胆轻轻推开门,喊了声“老师”,站在门口,没敢走向自己的座位。
谢老师眼神如利箭,射了我一眼,狐疑着诘问:“怎么迟到这么久?干什么去了?”我的脸刷地红了,心扑扑地跳,不知如何回答。同学阳春噌地站起来,说:“老师,他从河里救人去了。”谢老师似乎不可置信,愣怔了一下,眼中满是赞许,“好,快去坐吧!”
课间,谢老师把我和阳春叫去他的办公室详细了解情况。然后,消息便像长了翅膀一样,迅速传遍了全校的旮旮旯旯。
第二天上午,学校在操场召开全校师生大会。谢老师站在主席台上,慷慨激昂,振臂高呼:同学们,我们经常在书本上学英雄,敬英雄,现在,活生生的真英雄就在我们身边……在雷鸣般的掌声中我被请上台。谢老师把我拉到他身边,示意我抬头,像展示至尊镇校之宝。
放学后,谢老师执意与我同行。他要干嘛?趁热打铁?家访?相伴至河边,涟水悠悠,自西向东。虽隔河”千里″,谢老师单独到我家做了一次家访。
不久,我成为班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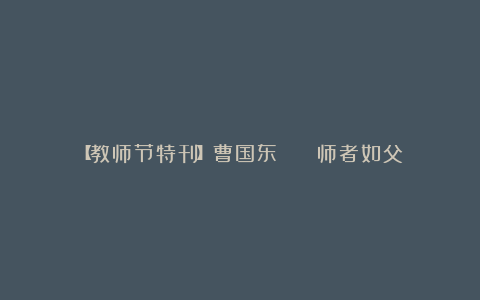
又过了一些时间,我被推选为校学生会主席,带领一班学生干部做得有条有理,风生水起。当年,我被评为湘潭市”优秀学生干部”,这在升学考试中有加分项的,尽管我没有考入心仪的高中,但前前后后,谢老师的帮助应该是无以言喻的。
谢老师的家和谭老师的家同在一个山冲里,很平常的土砖平房。屋后屋侧,茂林修竹。初中毕业后,我去过两次,受到谢老师和师母的热情款待。之后,我便如断线的风筝,和谢老师失去了联系。似乎我不懂感情,人啊,有时身不由己。
之后,我亦执鞭三尺讲台,与谢老师成了同事。但他在涟水河南岸中学,我在涟水河北岸中学,鲜有交集。我甚至不敢主动去搭话,去拜访,一是敬畏,二是内心的自卑吧,认为自己没有大出息,有负谢老师的厚望。
1996年,镇上创建虞唐文学艺术社,并创办《银河》杂志。谭社长和谢老师是创社创刊元老(谢老师当过几届主编,为乡镇文学的繁荣与发展呕心沥血,立下了汗马功劳),盛邀我参加。在填写职业一栏时,我没有丝毫踌躇挥笔写下“农民”二字。当时特邀参会的李副市长填的是“农民的儿子”。这一情景一时传为佳话,为虞唐文化圈所津津乐道,谢老师亦在多篇文章中作美谈提及。
后来,我俩的交往便多了起来。他对我的关心与日俱增。
世纪之交,姐夫入股的船舶桥梁出事,我们得凑钱了难。而我刚失去女儿,人财两空,欠下一屁股债。焦头烂额之下,冒昧向谢老师借钱。谢老师接了电话,爽快地邮寄八百块钱给我,解了我的燃眉之急。这于只拿不高的退休工资的谢老师,该是多么看重他的学生,多么深厚的情意啊!
谢老师退休后搬到了城区居住,我三番五次地去打扰。他知道我嗜酒,每次都拿出最好的米酒,给我倒上满满一杯,自己的则仅仅盖住杯底。我们边喝边聊,谈教育,谈文学,谈虞唐文艺社,谈兴勃发。有时,他又感叹:唉,囿于体制,教育界失去了一位优秀的老师,亏了你。
他指的是,我迫于生计,弃教南下淘金。
我惊讶于谢老师对文学有这么深的造诣,他不是数学老师么。谢老师同样诧异,“我还教过你们数学吗?”他原是文理兼优的老师!
我开办作文工作室,谢老师写了两副对联赠我,其一:灵系双文正,情倾两故乡;其二:九峰文脉来衡岳,涟水甘醇汇洞庭。我恭恭敬敬地裱好,挂在办公室。
谢老师的书法字里行间,都透露出大家风范。他工于诗词联赋,散文小说亦多有涉猎,出过《银河流淌》和《真情无价》两本文学专著,令人侧目。我的文章他多有赞誉,偶尔也挑挑刺,这实属难得。
谢老师对我的关心是全天候的。他常常过问我的工作室能否支撑;失业了该咋办,这些年对我的呵护与关怀远非师生,如父,如山。
或者自古穷困是书生?早几年,我生意失败,借了四千元高利贷回老家陪母亲过春节,利息追得我屁滚尿流。谢老师知晓了这事,责怪我没跟他说,叫我以后别干这等傻事。只差没开骂了。那时我想啊,谢老师,我真得衔草涕零。
去年腊月二十七,我回老家陪母亲过年。特意从乡下搭车去城里看望谢老师。他特别高兴也特别意外,在小区门口的餐馆点了四五个菜,又回家拿来珍藏多年的一瓶药酒。一如既往,给自己倒了浅浅一杯底,推给我,“全是你的了,干掉!”爷俩边喝边侃,说不尽的话,降不下去的意兴。末了,他盛留:住一晚吧,我好想与你彻夜长谈。但我不能,虽然给他有点小失望。
我几次想去买单,都被他制止了,甚至愠怒了。
谢老师已年届八十五,早过了杖朝之年。难道唇厚之人福厚寿高是真的?我愿意是真的!
有些事,如白云苍狗;有些人,值得一辈子交往和尊敬,比如谢老师。
作者简介
曹国东,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湖南省教师作家协会会员,岳阳市作协会员。大半辈子当中小学教师,从事教育工作。乐耕于讲坛、书本。岳阳市采风学会会员。
图片: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