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歆益
作者为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教授,本文基于2024年春在慕尼黑大学的演讲整理而成,内容有删减增添。授权刊发。
“努尔人在他们的语言中没有与我们所谓’时间’相当的表达,因此他们不能像我们那样,把时间当作一种真实存在的东西来谈论——会流逝、会被浪费、可以被节省,诸如此类。我认为他们从未体验过那种与时间对抗的感觉,也无需把诸活动与某种抽象的时间流逝去协调,因为他们用来参照的主要是活动本身,而这些活动通常从容不迫……努尔人是幸运的。”
埃文思-普里查德 1940,《努尔人》
(E. E. Evans-Pritchard 1940, The Nuer)
周而复始与逝者如斯的时间
关于时间,我们通常有两种体验:一种是重复、有节律的时间:诸如季节、月相、昼夜,周而复始。另一种是不可逆的时间,如生命由生至死,沧海桑田,逝者如斯。
1961年,人类学家李奇(E. R. Leach)在一篇题为《两篇关于时间象征性表达的短文》(Two Essays concerning the Symbolic Representation of Time)中指出,这两种关于时间的体验没有一定的内在联系,不需要统一在一个名为“时间”的观念之下。他以缅甸克钦语为例,“时间”可以由多种词汇分担其意义。克钦语中,长的时间、短的时间、现在、春天的时间、马上要来临的时间、维多利亚女王治下的时间、钟表上的时间,这些观念由彼此无关的词汇表达,并无统一的抽象概念。
圣体钟(Corpus Clock),剑桥大学圣体学院
克钦人对时间的态度不是特例,很多社会都缺少与英语“time”(或中文“时间”)对等的词项,例如本文开头所描述的努尔人。法语亦然,以至于《英/法词典》中关于时间的词条是全书最长的,可见“时间”在法语中的多样性,以及英语在此类表达上的贫乏。古汉语也不以一个抽象的总词统摄万象,而是以许多分化的词项去描绘“时间”的不同侧面。例如,与社会契约相关的:期、限、会、约、正朔、历、元;与物候节律相关的:侯、春、夏、秋、冬、孟、仲、季、雨水、清明等。
作为抽象范畴,“时间”是在近代才在汉语中固定下来的。同许多近代词汇一样,源自近代日语,是对“time”的翻译。古英语中“tīma”,源自古日耳曼语,一般追溯到两个印欧语根“temp-”,意为“拉伸”,“da-”,意味“分割”。“时”与“间”,是对这一词汇恰如其分的翻译。
希腊语 chronos(χρόνος)指“时序、时段”,成为现代英语中“年代学/计时”(chronology)诸词根。神名克洛诺斯 Kronos(Κρόνος,对应罗马农神萨图尔努斯 Saturnus)并非同源,但二者自古常被并置。克洛诺斯神话:泰坦十二神的领袖,盖亚之子,宙斯之父。李奇认为,希腊人以此神话来隐喻摆荡式的时间观:克洛诺斯以镰刀阉割乌拉诺斯、吞子又吐子,宙斯逃脱,以及黄金时代将逆转而归的母题,都把时间表述为在父/母、生/死两极间的吞/吐式往返。
这便使克洛诺斯成为时间的象征。后世出现了“手持镰刀”的时间老人形象,将周而复始与逝者如斯统一起来。
假鼻子与黑礼帽
两篇短文的第二篇,《时间与假鼻子》讲述社会如何通过节日庆祝把抽象的“时间”制造出来。一些文化将多样的“时间经验”归纳成单一的观念,将“周而复始”与“逝者如斯”统一:暗示时间并非自然自明,而是人类以社会目的投射到世界的观念。在缺乏精密历法和测时仪器的社会中,年度经济/宗教活动的连续与停顿,构成神圣/世俗的交替,从而把连续的“时”分割为有名的“间”(如周、月、季、年),并使时间呈现为反复对立的间断式的连续而非线性流逝。
一个意料之外的问题随之出现:为什么人类的节庆活动体现出普世结构?世界上不同的文化都以类似的方式来庆祝节日:假面、狂欢、角色反转与日常礼法的松懈。
以古罗马的农神节(Saturnalia)为例。农神萨图尔努斯(Saturnus)是前文提到希腊神克洛诺斯(Kronos)之罗马化,罗马最古老的神祗,掌管农业与时间,英文中的土星(Saturn)与星期六(Saturday)都以此神命名。节日在每年的12月17-23日举行,以萨图尔努斯神庙的献祭与公共宴饮开场,解开神像脚上的羊毛束缚,象征暂时的解禁。庆祝的核心是秩序反转与暂时的自由:主人为奴隶服务,允许奴隶顶嘴;人们穿上彩衣,戴象征自由的帽子;平日禁止的赌博在节日期间合法;家宴会推举“无序之主”,发布滑稽命令;法庭与学校停摆,整个城市弥漫着玩笑与戏仿的气氛。
类似的节庆方式在中世纪至近世的欧洲十分常见:主显期(Epiphany)前的第十二夜,人们推举“无序大王”(Lord of Misrule),发布滑稽命令;教会有“男孩主教”(Boy Bishop)的戏仿仪式。大斋前(Lent)的狂欢节(Carnival)期间,面具游行,角色颠倒、日常礼法中被禁止的行为暂时合法化。
在尼日利亚,伊博人(Igbo)的新薯节(New Yam Festival),歌舞与公共宴饮模糊了日常礼法与戏虐游戏的边界。墨西哥的亡灵节,人们在墓园守夜,家中供灵台以期祖先回访,将生/死暂时并置。印度洒红节,抛洒彩粉、泼水与街头歌舞,暂时消解阶层与性别隔离;火堆仪式焚烧“旧恶”,标记季节复生。日本“节分”(Setsubun),人们在门前撒豆驱邪,面具扮鬼与笑闹构成可控的越界。藏地的羌姆(Cham),僧俗佩戴神魔面具舞蹈,演示死亡/再生业报反转的叙事。中国传统节庆仪式中也不乏此类例子,如上元灯节,开禁夜市、士庶同游、百戏杂耍有日常礼法暂时松懈和“狂欢化”的趋势。社火与打春牛的仪式亦有假面、越界、逆转的循环结构。
为什么毫无历史联系的文化用相似的方式投射时间观念?这是一场贯穿很多世纪的讨论。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已对希腊与埃及的节庆对照讨论。比李奇更早的人类学家弗雷泽(James Frazer),在《金枝》中将“收割-牺牲-复生”的周期视为人类仪式的普遍结构,源于古代世界对魔法的尊从。但这种共源性的说法很难解释跨文化的普遍现象。
李奇写作的60年代正是结构主义盛行的时代。结构主义者相信在明显的文化多样性之下,有某种“泛人类”普遍原则,共享的文化密码。他认为节日庆祝的本质是人们通过共同的规范来创造并编序时间流。经典框架来自范·热内普(Van Gennep)1909年的著作《过渡礼仪》(Rite of Passage):任何由一种社会身份向另一种身份的转变(如出生、命名、入学、成年、婚姻、就职、葬礼等)都遵循“三段式”原则:分离(Separation)/阈限(Liminality)/聚合(Incorporation)。李奇认为人类的节日仪式行为遵循类似的三段式原则:礼制化/假面化/角色反转。19世纪欧洲男性戴黑色礼帽(男女正装)参加葬礼,人们戴红色的假鼻子参加生日会或渡过新年,是一种时间的“过渡礼仪”:通过礼制/庄重、假面/狂欢两级的转换,角色反转,许可社会失序,暂时成为“他者”,主仆/尊卑/生死倒置。以使时间重置,将逝者如斯转化为周而复始,或者反过来。
现代社会仍见这种古老结构的影子。李奇的同代人,早夭的帕特里奇(Burgo Patridge)有一本著名的《狂欢史》(A History of Orgies, 1958)传世,记录欧洲自古至20世纪狂欢活动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意涵。世界各地的节日庆祝常以庄重的仪式开始,结束于假面式的狂欢,或者是反过来。勒卡雷(John le Carré)1974的小说《锅匠、裁缝、士兵、间谍》(Tinker Tailor Soldier Spy)中,有一场重要的圣诞聚会,聚会中,英国情报部门“圆场”的头目带领手下高唱苏联歌曲,在冷战背景下显得滑稽而疯狂。歌声中出现的一场“亲密关系”,成为阴谋之下的阴谋。当观众惊奇于如此不可理喻的场景时,李奇大概会说:神圣时间降临,秩序反转。
李奇的观察不可不谓深邃。但另一些学者认为时间“过渡礼仪”的想法,过于学究气,错过了问题的重点。例如,《万物黎明》(The Dawn of Everything)的两位作者,格雷伯(David Graeber)与温格罗(David Wengrow),持此反对观点。
他们认为值得注意的是各文化节庆中,明显的无政府主义色彩。例如,欧洲中世纪充斥着节庆期间社会被以另一种组织结构以戏谑的方式所接管的记录:除了前面提过的“无序大王”、“男孩教主”之外,还有“青年修道院”(Youth Abbey)、“五月女王”(Queen of May)、“非理性神父”(Abbot of Unreason)和“醉鬼王宫”(Prince of Sots),这些人在节日期间接管了正式的宗教与行政职能,以戏谑、玩笑的方式发号施令。
在欧洲之外,节庆/季节性社会治理反转的人类学材料屡见不鲜:莫斯与伯谢(Marcel Mauss & Henri Beuchat)观察因纽特人在夏季分散成小型家户、由年长男子掌家;而冬季聚居于公共屋,财富与伴侣共享、权威软化,呈现夏、冬相反的双重社会形态。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的纳姆比夸拉(Nambikwara)材料显示:雨季定居:首领权力与礼制上升,旱季分散:权力下沉。这种双重形态允许人们把政治视为可“开关”的人造物。博厄斯(Franz Boas)在加拿大西北海岸所见亦然:冬季宫殿、等第与“散财宴”(potlatch)高度等级化,夏季转回松散的小群体,甚至换用不同姓名以标记身份时段。罗维(Robert Lowie)则描述北美大平原的夏末/秋季群猎营地:临时推举“野牛警察/战士社”行使鞭笞、罚没、甚至杀戮等强制权,待猎季与“日舞”(Sundance)结束即解散,并在次年轮换执权者。形成一种季节主权的暂时接管与反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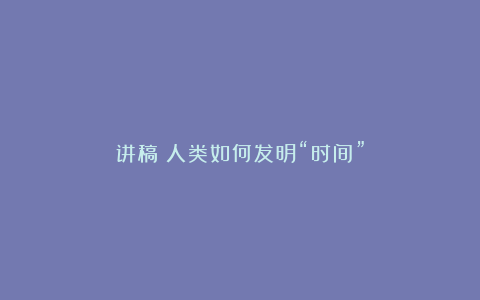
在这些人类学的记录中,“过渡礼仪”不再是社会对个人的单向规训,而是群体在“分离/阈限/复归”的窗口期进行制度想象与道德辩论:谁有权命令?共有财产如何分配?惩罚是否必要?下一阶段的社会组织以何面貌出现?答案可以随季节、随场景而变。 “他者”社会不仅仅在智力上不输于现代的“我们”,很可能在视野、雄辩、政治手腕上与我们旗鼓相当。
“黑礼帽”和“假鼻子”是另一种社会可能性的象征。这种可能性既是仪式性的,也是在不同季节激活新的社会组织的必要功能;可以通过假面、狂欢与反转制造出来,投射到世界上。
多个季节
上述的人类学材料为我们描绘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在更漫长的历史中,人类社群并不像今天一样,被限制在某一种固定的社会制度和政治框架下。多种社会制度并存,并随季节转换。人们通过节日庆祝来完成这种季节性的制度过渡,使之平稳、可控、并能在不久之后的下一个季节再次逆转。从莫斯到列维—斯特劳斯、罗维到博厄斯,弗雷泽、埃文思-普里查德到李奇,格雷伯与温格罗,二十世纪人类学家们惊人一致的观察(尤其考虑到他们不同的学术立场)让这种可能性超远超假设的范畴,接近历史真实。
下面我们考察考古学的证据,以探讨人类学认识的深层历史根源。
格雷伯与温格罗将多季节的政治生活与前农业时代采集狩猎人群的考古证据联动。指出末次冰期(Last Glacial Period, 11-1.2万年前)考古材料中,人们对待死者不寻常的方式,指向某种组织多样性,迁徙与季节性狩猎而引发的季节性集、散组织。欧洲旧石器时代的猛犸象骨圈(例如位于捷克的维斯特尼采Dolní Věstonice),土耳其哈兰平原全新世早期的大型石制建筑群哥贝克力(Göbekli Tepe),北美密西西比河流域巨型封土遗址“贫困点”(Poverty Point)等。在格雷伯与温格罗的论述中,这些材料共同指向:前农业社会常在不同季节切换治理模式。权力可以是季节性的,节日庆祝并非再生产现有秩序,而是在反转的游戏中制造新的秩序。
然而,这样的假说很难解释采集狩猎人群之间巨大的文化鸿沟,以及这种差异性如何会演变成一致的“泛人类”礼仪范式。如同弗雷泽的“古代魔法”起源说一样,难以解释普世性。“魔法”是多样的。
二十一世纪考古学的一个进展是对人类生业发展阶段的再思考。狩猎/采集、游牧、园耕与农耕之间的边界逐渐模糊,也非线性的发展阶段。人们可以同时是猎人、农人、采集或游牧者,不同生业形态在同一社群并存是历史常态,以多种方式组合,并与持不同生业方式(组合)的人群比邻而居,长期共存。对生业模式的选择,既是在特定环境下的被动经济选择,也是主动的社会与政治策略。
发生于公元前第三和第二千纪(5000-3000年前)的农业全球化把旧大陆原本分散的农业传统汇集到一个体系中。这一过程对分布于各地的社群带来两个影响。一是冬、春两个农业体系的结合:驯化于西南亚洲的谷物(大、小麦、燕麦、黑麦、豌豆、小扁豆、鹰嘴豆)都是冬季作物,因为中东地区水、热不同步,冬季并不特别严寒,形成秋种(第二年)夏收的农时;因受夏季风影响,非洲、南亚与东亚的早期谷物均为夏季作物。早期中国的农业系统施行春播秋收(粟、黍、水稻、大豆、小豆等)。青铜时代农业传播给欧亚大陆和非洲北部带来的两个农业季节,其影响高潮应在四千年前后。公元前第二千纪(4000-3000年前)的考古学记录中,起源于不同农业中心的冬、夏两种作物共出一地的情况十分常见。各地古代文献中也都出现两个农业季节的记载。
另一种影响同样显著。除了谷物传播之外,起源于西南亚洲或黑海北岸的驯化动物(黄牛、山羊、绵羊、马),也在距今四千年前后传播至欧亚非的不同区域。生活在这个区域的古代社会进入一个农/牧并举的二元(或多元,同时伴有仍然重要的采集/狩猎经济成分)经济时代:农业以耕作为纲(播种、除草、灌溉、施粪等高劳动投入的集约化),牧业则以放牧与圈养为要(依赖草场幅度与迁徙范围的粗放化)。于是,一年被分化成两种(或多种)“时”:农时与牧时;同一社群同时并重或多种价值标准:集约偏好近聚、可控的投入/产出与劳力动员(堤渠、谷仓、赋役);粗放偏好远疏、弹性的边界与伙伴式协商(草场轮牧、季节交易)。不难想象,两个或多个随季节变更的社会组织不仅是可能,而是一种生存必要。在季节转换处通过节庆、会盟与礼仪完成制度切换,以期平稳过渡。
某种意义上,马尔萨斯(Thomas R. Malthus)所议“人口增长-技术变更-崩溃”的历史循环在四千年前已具雏形。但更可能是以纪而兹(Clifford Geertz)或博塞拉普(Ester Boserup)所描绘多种政治/经济的钟摆选择,而非历史宿命的形态出现。
最近的考古学的进展表明多种经济组织共存和博弈的情况广泛存在。例如,在辽西河地区,粟黍农业与山前牧养长期并置。孙宇峰与同事们观察到跨夏家店下层文化、上层文化、西汉的标本显示作物在“人口扩张/耕地外展”阶段单位面积劳动投入下探,反映施肥由集中/分散/再集中,与冬牧通道、圈肥回流的季节性协调相互牵扯。东天山绿洲—山地体系中,田多与同事们讨论大麦的田间杂草与氮同位素揭示“灌溉/施粪/除草”的集约麦作与游牧并轨运行;当牧业上升或劳力外移时,管理从“精耕”转向“外展/粗放”。西南亚洲城邦/绿洲地貌中, 斯特林(Amy Styring)观察到城市谷物供给多依赖远城的雨养土地和单位面积投入偏低的“粗放”形态,而精作区域被压缩在近城园圃与渠灌区;收获季强动员与征粮集中权力,出收后又回落到家户与牧群伙伴之间的协商秩序。三地共同说明:古代社会由多季节/多经济形态/多社会组织构成,内部存在结构性冲突,需在不同季节中激活新的社会治理,完成周期性调整与再平衡。
努尔人与时间的纪念碑
埃文思-普里查德在笔下的《努尔人》即生活在如此多季节/多组织形态的“农/牧”环境中。值得注意的是努尔人对“时间”的态度。努尔人将“时间”分为两条互补的轴线:生态时间(ecological time)与结构时间(structural time)。前者是以环境与生计为参照的“任务时间”:雨季与旱季、更替的牧场与营地、放牧与乳制品生产、捕鱼与迁徙等节律;日常安排依附这些活动节点展开。因此努尔人很少说“几时几晌”,而是说“挤奶的时候”、“牛回圈以后”、“河水落到可以涉渡时”等。月份与季节的命名也与可感的生态事件绑定(草发、洪峰、虫害、收割),与古汉语中的时令、节气并无二致。时间像一串串生产、仪式、迁徙的段落,被事件本身“刻度化”,而非被独立、抽象的“时间”刻度化。
结构时间则是以亲族谱系与政治关系来“量度”的历史时间。努尔人通过追溯共同祖先的“深浅”来定位事件与群体关系:与其计算“距今多少年”,更常说“在某祖辈时代”、“在某分支分化之前/之后”。这种谱系化的时间是可伸缩的:在需要团结时强调共同祖先的“浅”(缩短时间距离),在争执或分节时拉长世代深度以区分彼此。
努尔人并非没有抽象的时间观念,他们让活动、关系、环境本身成为时间,在季节与制度间摆动。在无法或无需用文字表达这种秩序的社会里,是否存在某种物质文化的传统,重现季节性社会的摆动与重置呢?
内布拉星象盘(Nebra Sky Disc),距今3800-3600年。藏于德国哈雷博物馆
约四千年前后,欧亚大陆多地几乎同步地出现将季节/时间“物质化”的考古学证据:英国索尔兹伯里的巨石阵(Stonehenge)最早的建筑年代可追溯到距今五千年左右,但今日所见的石阵是4000-3600年前的作品,石柱构成可穿行的视线廊道,对准夏至日出与冬至日落;山西陶寺“观象台”以辐射状观测口与城址轴线扣合,标定春、秋分、夏至和冬至,年代在距今4100-3900年间;德国内布拉星盘(Nebra sky disc)以金箔呈日、月与昴星团,并加两道“地平弧”指示冬至与夏至方位,应是距今3800-3600年前的青铜制品;同时期古代中国的“玉璇玑”等玉礼器,将天象、方位与节序合一,虽最早见于新石器时代,但在四千年后更为流行。
值得考虑的问题并不是这些考古材料是否存在统一的含义,而是它们为什么集中出现在公元前第二千纪(4000-3000年前),而不是此前的几千年中,地理分布又如此之广。答案也许正隐藏在发生在四千年前后那次波及甚广农业全球化历程,以及此时普及的多季节社会/经济轮替系统。
埃文思-普里查德将努尔人的“生态时间/结构时间”观念描绘视为一种前现代的奇特例外。与今日的我们截然不同。对此历来不乏批评之声:那种以生态与社会关系为标尺的“努尔式”时间观,在现代世界仍广泛存在,并与抽象的“钟表”时间共存。历史学家汤普森(E. P. Thompson)认为近代工业社会通过工时制度、钟表与时薪将“时间”货币化,将抽象的“时间”具象成钟表的形象,使之可以流淌、被浪费、被节省。使我们有与时间对抗的感受。但并未抹去“努尔式”时间的影子:现代海港仍“听潮而作”,农事依然围绕播种、出穗、收获编序,家庭照旧围炉谈论祖先,国家以庆典、代际与纪念日“结构化”时间。节日礼仪中仍保有假面、狂欢、反转的记忆,无论何种文化,时间仍在周而复始和逝者如斯之间反复摆动。
到最后,我们都是努尔人。
(标题为编者所加。)
#artContent h1{font-size:16px;font-weight: 400;}#artContent p img{float:none !important;}#artContent table{width:100% !import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