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中的贾科梅蒂
第二天我到那里时,阿尔贝特不在工作室。蒂亚戈告诉我说,他去了莫洛(Mourlot)的印刷厂,为特里亚德(Tériade)要在明年出版的大开本校稿。大约一个半小时后他回来了。他径直走进工作室,没有与我和蒂亚戈多说一句。我跟在他身后进去时,他正在角落里忙着翻阅放在那的四五本大画册。他没注意到我,实际上他甚至没意识到这里不止他一个人。他不耐烦的从画夹中抽出一叠画在石板转印纸上的画,外加一些黑色的转印纸,还有一些画在普通纸上的画。他把这些画都扔到了地上。
“你到底在干什么?”我忍不住问他。
“我要扔了这些东西。”他说。
“别,别,别!”我抗议道。
“我就要这么做,你看着。”他大声喊道。
他抓起地上的一叠画走了出去,穿过走廊去到蒂亚戈工作室旁的垃圾桶边。把它们扔在了地上,随手抓起一把然后开始将它们撕成碎片。我抓住他的胳膊试图拦下他。“等等,”我争辩道“我们先看看它们吧。”
“不,不。”他大叫道,又抓起一把画作撕碎了。
我对此无能为力。而且,这些画怎么说都是他的,如果他愿意,他有权毁了它们。而我从认识他以来,也至少还有过一次相似的经历。所以我也只好从这一叠画的最上面抓了几张后回到了工作室。他没有马上回来,而是跟蒂亚戈谈了一会儿。我支起画架,把画放在上面,把凳子和椅子摆好位置,然后等他过来。过了一会他回来了,我问他为什么要毁了那些画,至少有二三十张。他解释说在莫洛那,他发现他一直在用的石版转印纸已经太旧,而无法再转印画了。因此他才想毁了这些达不到他预期的版画。他显然被这一技术上的意外搞得十分烦躁。我说他根本不用毁了这些画,无论它们那能否转印成石版画,画面已经是成立的了。但他一句也听不进去。他早想把它们都毁掉,就是这么回事。他的感受似乎充满了怨恨,好像这些画本身得罪过他一样,而他的所作所为则是在通过它们报复他自个儿。我提醒他,他还毁掉了一部分画在普通纸上面的的画。他却说“无所谓,它们也不好,无论如何,我很高兴把它们毁掉了。”很明显,这些也好,那些也罢,在他把这些画从他的画夹中抽出来的时候他几乎没有看他们一眼。我没有再坚持,我想起了塞尚在对自己所做的事有所不满时也有变得狂躁并且砍自己画布的习惯。这种做派太常见,没什么惊奇的。
他开始工作了,像往常一样,又把注意力放在了头部上。我想他至少这么做了二三十次了。但不一会儿他就说:“必须把所有东西都毁了。我要全部从零开始。”
一会儿他又一次提到了昨天说过的那本书,那本书里对照片和绘画进行了比较。他说其中有一页在写丢勒,同时还有一幅拉斐尔画的红衣主教画像,一张传统风格的福煦将军(Marshal Foch)的肖像。他说他更喜欢福煦将军的肖像。他又补充说“无论如何,要重现一个人所看到的东西是不可能的。”
“那么一张照片就能真实再现一个人所看到的东西吗?”我问他。
“不,而且如果照片不能,那一副画就更做不到。最好的就是用眼睛去看。另外,要达到肖似的效果是不可能的。例如,当我在制作猫的雕像时,我做的并不像那只猫现实中的样子,因为我是做不到的。”
“那你是怎么做的?”我问他。
“我经常在早上起床前看到蒂亚戈的猫穿过卧室跑到我床上,它已经清晰的印在我脑子里了。而我要做的就是把它做出来,但只有头部称得上像它,因为我最常看到它的正面,看着它向我走来。”
“那只狗倒是比猫更像一些”我说。
“你是说口鼻部分,是的,但后腿完全不是,后腿纯粹是想象的。”
“你是怎么做出这只狗的?”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脑海中一直萦绕着我曾在某处见过的一只中国狗的样子。然后有一天,我正冒着雨紧贴着建筑物的墙壁低着头走在瓦芬斯街上,或许有一些伤感,我觉得那时的我就像一条狗一样。于是我就做了这个雕像。但它并不是一个真实的形象。只有它悲苦的口唇部位有一些相似之处。无论如何,人们之间才是真相似。我从未疲于观察他们。在我去卢浮宫时,如果我关注到的是人而不是那些绘画和雕像时,我就完全无法再去欣赏那些艺术作品了,而我也只得离开。”
说起安妮特即将从伦敦返程这件事,我们又聊起地理,欧洲,六大洲,而最后话题落到了日本。我曾说过我对中国人和日本人都不太熟悉,但在过去的几年里,他和矢内原伊一直相处的不错,一位日本教授,他在某段时间内为他许多绘画和雕塑作品做过模特。我想知道他是否会觉得自己与矢内原伊有什么差异,在本能的态度或反应上有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差异,这种差异可能由于不同的生活背景,国家又或者种族而形成。
贾科梅蒂《矢内原伊像》(1960)
“完全没有,”他说。“他就像第二个我一样。实际上,我之所以把他作为某种人的范本,是因为我们相处的太久了。我们总是在一起,在工作室,在咖啡厅,在圆顶酒吧,在夜总会。那些天我们总是在一起,有一天我还因此有了一次奇特的体验。矢内原伊正在给我做模特的时候,杰内特突然来工作室了。我觉得他看起来非常奇怪,脸又圆又红,嘴唇也肿着。但我什么也没说。然后蒂亚戈也来到了工作室。我也有同样的感觉,他的脸也又圆又红,嘴也肿着。我不理解这是为什么。然后我意识到我在看蒂亚戈和杰内特的时候在将他们与矢内原伊作比较。我已经在矢内原伊的脸上专注了太久,以至于他的脸对我来说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就是在这很短的一瞬间,这个印象只在我脑海里维持了很短一会,我知道了在非白人的眼里,白人是什么样子的。
当贾科梅蒂讲述这类故事和那些更长更具个人色彩的故事时,他似乎会完全投入其中,他说的很快,即使他的手还在继续画,但他的大脑似乎已经忘记了画画这件事。他明显享受着与自己的模特交谈。有一次,在他正兴致勃勃的说话时,我却在担心这可能会干扰他绘画的进程,我建议他安静一会。而他却说“对我来说,闭嘴实在太难。这种胡话全部都是因为我不可能真正做成任何事才有的。”然而,当他不用画画,比如和别人坐在咖啡馆的时候,他却常常是一言不发的凝视着天空。我觉得工作时和模特交谈会使他分心,这种持续不断的焦虑是因为他坚信他无法在画布上表现出他所希望能看到的东西。这种焦虑常常以忧郁的叹息,愤怒的脏话和偶尔愤怒或痛苦的大声哭喊表现出来。确实,他一直在煎熬。
贾科梅蒂雕塑《杰尼特》(1954)
珍·杰内特(Jean Genet)曾回忆,贾科梅蒂倾向于与自己的模特发展起情感关系,对他们而言是一种近乎浪漫的情感。至少在我看来,这种情感是相互的。对于这种情感的存在也不用惊讶。贾科梅蒂以一种特别而又彻底的方式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中。这种创作冲动永远不会从他身上消失,永远不会让他有片刻的宁静。我记得他说过很多次,每天早上醒来后他脑子里出现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还有工作在等着他去做,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那些绘画和雕像还在等他完成。他说,伴随着这噩梦般的绝望无助想法,就像是他的脸被狠狠按在墙上而无法呼吸。怀着同样的情绪,他有时会满怀憧憬的谈起可以永远停止工作的那一天,当他能有一次可以成功的表现出他所看到的东西,以具体可感的方式表达出所看到的真实。当然,这是不可能的,而他也确切的知道这一点。衡量他创作力强弱的依据就在于他深深渴望着有一天能够摆脱这种束缚。这种强力的情感自然也会传递给他周围的人,特别是那些与他生活紧密相连的人,而这些人在任何时候都是他的模特——他的妻子、兄弟和认识已久的朋友们。给贾科梅蒂做模特的体验对我来说意义非凡。一方面,他说了很多,不止是他的工作还有他自己和他的人际关系,而模特也会被推动去做同样的事。这样的交谈可能很容易创造一种超乎寻常的亲密感,这种感觉是在那种充满互动而几乎超自然的氛围中诞生的,也正是模特和画家所特有的。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有时候甚至让人有些难以承受。这是一种模特与艺术家之间的密切关系,经由绘画而渐渐变得独立出来,而双方以各自的方式共同维护这个状态,以完全对等地方式,着实令人惊讶。
这种身份上的认同感通过我在做模特时发生的两件事得到了证实。有一天他的脚无意中碰到了画架,导致画布突然下降了一二英尺。“噢!抱歉,抱歉!”他说道。我绷不住笑了,我说他道歉的样子就好像是他撞到的是我而不是那幅画。“我确实是这么个感觉。”他回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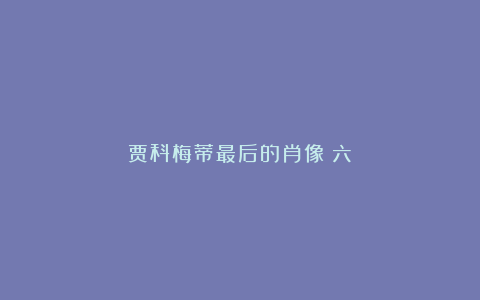
还有一次,我的左脸突然感到很痒,因为他希望模特能完全保持不动,我试着通过抽动脸颊来缓解这种骚痒而不是用手去挠。
“你怎么了?”他问我。
“我的脸很痒,”我解释说。
“为什么?”
“因为感觉你所有的小笔触都像画在我脸颊上了一样。”
“太妙了。”他笑了。
我也笑了,然后挠了挠脸。但我说的一切都是真的,并不是我开玩笑,也绝不是我故意要逗乐。我告诉他这件事,并且他也完全理解了我说的意思。
人们常说,极具天赋的艺术家能够并且尽量追求展现对象的外在形态,同时也能传达其内在特征。我不知道事实是否真的如此,但一幅肖像画能够反应出艺术家与模特之间那种有可能产生的亲密关系,这一点似乎不用惊奇。总之,创造的本能受到潜意识的驱使,这同时也决定了人类关系的具体特性。但贾科梅蒂不这么认为,他觉得肖像画与模特的个体特质之间根本就没有联系。至少在他的工作中是这样的。他说“外部的事情已经够麻烦的了,就别再操心里面的事了。”
我给他做模特时,他偶尔会问我觉不觉得累。“这让你感到不自在了吗?”他问我说。尽管他没有直说,但我还是认为他问的不止是摆姿势累不累,而是这整件事,我会不可避免的卷入他的迷惘和绝望中去。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我总是说没有,实际上这也是真心话。总体来说这是一次让人高兴的体验。但有时候成为一种徒劳努力的托词还是让我内心疲惫,这努力从一开始就知道是徒劳,但同时又坚持认为无论如何都要去努力才是有意义的。最根本的矛盾来自于现实和观念之间那无可弥补的差异,它是所有艺术创作的根源,也解释了那种在创作过程中似乎是不可避免的痛苦。就像是雷诺阿(Renoir)这样“幸福”的艺术家也不能幸免。但是很少有人能像贾科梅蒂那样,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工作中都展现出如此清晰而坚定不移的目标感。这就是某些评论家称他是一位“存在主义”艺术家的原因之一。
贾克梅蒂的作品中有一些元素会反复出现。当然,最突出的无疑是蒂亚戈的头,它似乎都成了男性面象的典型代表。我跟阿尔贝特提到过这一点,而他回复说“这很正常,蒂亚戈的头部是我最了解的东西,他为我做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模特,比其他任何人的时间都要长。从1935年到1940年,他每天都在为我做模特,二战后也持续了很多年。所以当我在凭借记忆去绘制或者雕塑一个头的的时候,它所呈现出来的样子总是很像蒂亚戈,很像这个我在过去做的最多的样貌。而同样的原因,女人的头部则更像安妮特。
贾科梅蒂《矢内原伊像》
他再次提起矢内原伊持续为他做了一段时间模特,这竟然让他对蒂亚戈和杰内特有了不同的视角,并说从那之后他就发现去辨别他人有困难,并且有时还会把他们搞混。他补充说“除此之外,有时我还会觉得一个人的面部和其他所有人其实没有太大差别,比如同样是一头金发,这个人的和那个人的都是一样的好看。我有一次对一位金发朋友说过这件事,但她完全不喜欢我这个说法。但人和人之间的差异是非常小的。举个例子来说,是什么让我可以在街上就认出你来呢?”
“我这整个人?”
“没错,但不是某个单独的细节。细节本身并不重要。是什么导致一个人能够吸引另一个人?”
“我不知道,但我敢肯定那跟传统意义上的好看没有关系。”
“当然没有。”
最后当我们在傍晚时停止工作的时候,画面已经变得混乱而又含糊。嘴巴偏向一边,下巴和颈部结合处也很含糊。“我们说话太多,”他一点也不满意。“明天我们得认真工作了。”
在离开前我跟他说“我有个礼物要给你。”然后我把下午早些时候抢救下来的那两张画递给了他。
他好奇的看了看它们,旋即笑了,他说“你是对的,它们并不糟糕。把它们放在这个画夹里吧。”
贾科梅蒂素描(1953)
译者 何雅嵘
王玠 编校
春天里的柏拉图
未经审视的生活不值得度过
在悦读中度过另一种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