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记得第一次来海云街是从哪个入口进去的了。如果从嘉禾路入口进去,首先要走过一道石板桥,桥下是黄色、黄褐色或者黑色的细水流。在上游不远的地方有一家染料厂,一家印染厂,铁锈一样的颜色就是从工厂下水道里流出来的。那时候不觉得这些铁锈颜色是脏的,就像小时候不讨厌汽车尾气里的汽油味儿一样。
过了桥,走过一根歪斜、光滑的花岗岩小石墩,有一家馄饨小铺,路对面是渔具小店,门口摆着好几捆鱼竿,最多的是插接竿,那种亮闪闪的伸缩鱼竿就是高档货了。另外还摆着一些鱼线、铅坠和一盘盘的鱼虫。匆匆走过时,一些人在挑拣着鱼虫,老大爷们坐在马扎上晒旧时光里的太阳。
向右走,就是海云街的一条主要街道。右侧是什么早已不记得。左侧有一家卖包子的小饭铺,飘着油香、肉香的包子热气儿常常飘出窗外。再往前几个门,是街上最大的一家绸布商店。
柜台上铺着成辊成辊的布料,中年妇女们在那里精挑细捡,准备割布给家人做衣服。营业员手持皮尺,在布料上快速翻量,然后哧啦一下扯开布料。有意思的是营业员填好销售票单之后,抬手就夹在一个铁夹子上,铁夹子套在铁丝上,顺势一推,夹子就顺着笔直的铁丝,滑向收款处,顾客交款后,盖了章的票单又滑回柜台。绸布店里共有十多道传送票单的铁丝,磨得铮亮。可以确信,这种好看的杂耍现在已经彻底绝迹了。
我对这家绸布店没太多的印象,一进店门,布料的气味就让人觉得脑袋热烘烘的,店内的嚣声响在近旁,却能在高处的房梁上发出回音,感觉很不真实。
绸布店外,斜对面的那条小路通向海云庵的正门。在海云庵的侧门外,是一道好多磴的台阶。这是海云庵的一间厢房建筑,看起来象这条街上的一个大户人家。门里面很宽敞,屋顶很高。
这里是小孩看连环画的一个地方,连环画封面被剪下来,用细绳栓在墙上,用毛笔写着号码。连环画封面的位置,是用一张牛皮纸粘贴的。看一本连环画,要一分钱或两分钱。我肯定进入过这间厢房,但在这里看过小人书吗?这些陈年旧账早已丢失在岁月的路上了。
清末民初的四方海云庵
海云庵后院里有一棵粗壮的老银杏,硕大的树冠撑开了好大一片空间,从院外远远地就能看到。它们的躯体里收集了一段长长的静默的岁月,褪下银杏叶,又长出银杏叶。它们会继续收集下去,但从来不说什么。
有时我是坐在公共汽车上,老银杏树不经意间就划过了窗外。现在这棵银杏还在那里。改建后的海云庵居民楼里,或许会有白发苍苍的老人在窗前认真端详着老树。老人丢失了岁月,却换来了一个从怎么也没想到过的高处视角。
在改建前的老海云街,走过海云庵西厢房,左边有一间散发着辛香气味的中药铺,再往前,是一家工商银行,银行对面,是一家国营菜店。记得这一段不宽敞的土质路面时常是湿漉漉的,这可能和周日集市和菜店门口不打扫的剩菜叶有关系。冬天的时候,土路上的自行车印、鞋印和小水洼被冻硬了。一阵风吹来,目光就不由自主地随着风看向远处街口。
有一年,我在读《福尔摩斯探案集》中的某段街景描述时,忽然想起和海云街的这段街景是相似的,北风凛冽,路面僵硬,脚步声响,有路人裹紧大衣快速走过。这个阅读经验,使一条记忆中的本土街道和虚构中的异国街道,暗暗地开始较上了劲,相互比喻,相互联合,相互生长。日常记忆,常常就在这样的误读之下产生并获得加强。
如果没记错,前面有三条街口岔道。一条岔道往北,通往国棉三厂方向的一片老居住区,这里曾住着我的一个远房表姐,表姐在“反右”时遇到难关,得到了我母亲的很多帮助。一条主岔道往东,通往海云街河水的上游居住区。一条短的岔道往南,南边百十米处就是海云街河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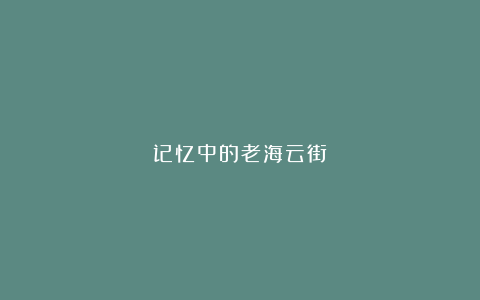
从我母亲那里听到,河沟沿岸这里叫“庙沟沿儿”,小时候我一直是理解成“苗沟沿儿”,因为这里有一个苗圃。所谓苗圃,其实只是一座圆形立面的小矮房,看起来有点象一个小型碉堡。这个小碉堡外面的地上,摆放着好多盆花,碉堡上有好多个窗口,窗台上摆满了盆景那么大的绿色植物。房子后面可能还藏着一个小院落吧。窗台上的小盆景在微风中绿油油地摆动着,远远地看去,觉得很羡慕。
小时候我经常想象,苗圃里应该有一位笑眯眯的种花老人,既种且卖,或者仅仅是因为一种经年累月的趣味而乐此不疲。我从没见过这位想象中的老人。
庙沟沿儿旁边有一个国营理发店,对理发师的印象,有很多是从这里获得的。室外是冷嗖嗖的冬天,室内有暖烘烘的火炉子、弥漫着热汽和肥皂味儿,六七个人坐在火炉边的长椅上排号。理发椅是那种金属制的专用椅,有放脚的脚蹬,有圆形底座。如果是小孩儿理发,理发师会拿出一个搓衣板垫在扶手上。小孩儿坐上了搓衣板,就开始哭。
电动推子的嗡嗡声象催眠曲一样,有的顾客能静悄悄地眯上一小觉。在这段舒服的时间里,时光竟然真的象不运行了似的。
那时的理发店隶属于饮食服务公司,理发师大约也是干了小半辈子的理发活计,如果有六十多岁老理发师,那可能是退休之后在这里补差。店里的日光灯也是白色的。现在的理发店进步多了,很多已经换成了粉红色的日光灯。那种亮着红灯的理发店里,甚至可能连一件理发工具都没有。
顺着庙沟沿儿往上游走,是一些看起来一模一样的老房,在靠近桥的地方有一家油煎锅贴铺。在桥那一边,还有一家国营饭店,排油烟机出口总是挂着黑乎乎的半风干油渍,再往前就是青岛染料厂门前的大路了。这里已经离开了海云街,我们暂且不管它。
一直往前走,还有一座用单条水泥预制板横担在沟两岸的小桥。我们就叫它一座桥吧,尽管走起来颤巍巍的,但大多数人都能走过去。桥那边是加油站,加油站马路对过,就是曾经说起过的那块神秘的三角地。内有一小院落,没有窗,院墙很高,院门紧锁,没人进去,也没人出来。不禁让人怀疑这是台湾特务布置的一个秘密联络点。
在水泥预制板桥的这头,对面是一家铁质院门的稍大的院落。这是当时街道办事处或居委会下设的一个劳动服务站,他们承揽了外贸工艺品公司草编制品的对外加工活儿。主要加工品是草篾篓包,是用压制好的草篾条缝成的,带两个提把儿,草篓上用染好的彩色苘麻缝着红花,用珠线缝着绿叶,一枚彩色纽扣就是花芯儿。缝这样一个草篓包费工费时,但加工费大概不会超过两毛钱,甚至可能更低。我母亲当年缝了很多这样的草篓包,清新的干草篾味儿让人记忆犹新。我家里现在还保留着一个这样的草篓,很好看,那是对母亲付出的辛劳的永远纪念。
沿着服务站门外往前走,向左拐弯,是一条非常窄小的胡同,弯弯曲曲的直通往海云街另一头。在本地拆除全部棚户区之后,这么窄的胡同只能从记忆中寻找了。这样的小巷,让人想起北京的耳朵眼儿胡同和鸡肠子胡同。
胡同半腰的一个院子里,住着我的一个卞姓同学。
这个院里还住着本地区有名的“小静”,或者叫“小颈”、“小镜”,我看到她时,她大约四十多岁,总是苦楚着脸。在四方区,她和“八一”是齐名的。“老四方,三个宝,八一、小静、嘎肉好”,现在大概没有人知道他们命运中的秘密了。几个干枯、瘦小的生命,被欺凌与被侮辱的人,现在已经变成越来越远、越远越不清晰的符号了。这座城市生养了他们,这座城市又将他们遗忘。
一些奇特的人总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在海云街附近的国棉三厂三舍,住着一个让我费解的老头儿。有时早晨上学能遇见他,他提着一根一头细一头粗的大棒槌,没人注意的时候,就拿出棒槌朝自己的肚子狠狠地打去,然后捂着肚子,一边干咳一边痛苦的蹲在地上。我不断地回头张望,直到他重新站起来为止。他这是在干什么?是治病还是练抗击打能力?或是在惩罚自己?不好说,但肯定不是练“铁布衫”。
走出了这条胡同,是一条勉强能跑汽车的坑坑洼洼的土路,左边高高的水泥墙里不知是什么单位,右边的红砖墙已经变成了黑褐色,红砖都快锈透了。前面有一个水龙台,附近居民常来挨号挑水吃。还有一家印染厂的车间,有时能看见两个工人推着沉甸甸的手推车,车上装着厚重的帆布布料。他们脏兮兮的工作裤很短,还不穿袜子。这是冬天,印染车间内部蒸汽很足。他们把布料车推过街道,推进对面的院子里。院子里地势很低,也是一片荒凉。
资料图片(杨勇摄影)
回过头来,看着这片有些荒芜的道路,视野显得有些远,有些开阔,景物变得有点缩小,有点深邃起来。对这条路总是记忆很深,但说不清原因。
前方左边是汇源宾馆。右边是几家居民小院落,院子旁边,隐藏着一口自用水井。
再往前,到了金华路,就不属于海云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