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间原野飘来的一缕清风
图 片:选自网络
最近三天连续编发了江华女士的五篇散文,这些文章都是从她刚出版的散文集《把村庄带回家》里选取的,都是描写亲情和乡情的。它就像是从乡间原野飘来的一缕清风,散发着泥土的芬芳,让人心旷神怡,清爽舒畅。
江华的老家在盐城东郊南洋镇原镇潭大队,就是她的散文里倾注了满腔热情回忆和描述的叫做顺潭港的地方。她所在的大队和我五十多年前插队的镇星大队是一河之隔。我不但对那里的乡土人情很熟悉,而且和她的父亲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我们一起做教师,一起演过现代京剧《红灯记》。不过他扮演的是英雄人物李玉和,我扮演的是日本宪兵队长鸠山。虽然台上是死对头,但台下是好朋友。一转眼五十多年过去了,今天读到他女儿的散文集,心情特别激动。
江华的散文文字朴实无华,文笔细腻优美,就好像一个邻家女孩叙述着她美好的童年,展现她纯洁的心灵,把她和祖母,和母亲,和好朋友的故事娓娓道来。她的一篇篇散文又把我带回到了那熟悉的村庄,又看到了一片绿油油的草地,一片金灿灿的麦浪,又闻到了清清的稻花香,特别是又看到了和蔼可亲、纯朴善良的父老乡亲,回忆起和他们一起同甘共苦、战天斗地的艰苦岁月,感到特别温暖,特别亲切。
《陪祖母看戏》以深情质朴的笔触,为我们勾勒出一段充满烟火气与温情的童年回忆,展现出祖孙间深厚的情感以及特定时代下的乡村生活风貌。
文章一开始提及父亲与戏曲的渊源,但重点迅速落在与祖母看戏的经历上,情感脉络清晰且集中。陪祖母看戏这一行为贯穿全文,从一同前往镇上剧场的路途,到在二叔家借宿看戏,再到因看戏逃课引发的“小风波”,每一个情节都流淌着对祖母的眷恋与依赖。
祖母舍不得浪费山芋,带着葵花籽赶路等细节,生动展现出老人的节俭与对生活的热爱。而“我”因逃课心急责怪祖母,祖母却只当笑谈的情节,更凸显出祖母对“我”无条件的包容与溺爱,祖孙间这份纯粹而深厚的情感,引发了我的共鸣,让我沉浸在温暖的情感氛围之中。
文章还原了特定时代背景下的乡村生活场景,为故事增添了浓厚的历史感与真实感。生产队场头作为舞台、村里文娱宣传队演唱现代小淮戏,反映出当时乡村文化生活的独特风貌,又让我回忆起自己和知青组朋友在场头演戏的有趣情景。夏天夜晚父亲教人唱戏、唱片机播放经典唱段等细节,展现出乡村在娱乐方式上的质朴与简单。去镇上看戏需走十里路、剧场每场戏爆满、三台戏接连上演等情节,体现了当时交通不便、娱乐资源匮乏但人们对戏曲充满热情的社会状况。这些时代元素相互交织,使我们仿佛置身于那个充满烟火气的乡村世界。
《祖母的小屋》还是写的祖母的故事,不过又是另外一个主题:祖母对小屋的依恋。这座“一窗一烟囱”的砖土小屋,既是祖母的栖居之所,更是情感与记忆的深厚寄托。
小屋诞生于家庭变迁之际。老宅拆迁,兄弟间因分家产生矛盾,寡居的祖母坚持独居,用有限的拆迁费在堤脚下建起砖土结构的房子,敷上草皮,开启独自生活。尽管儿孙满堂,小屋却满是孤独。然而,祖母并未真正远离家人。农忙时,她早出晚归,为儿子一家操持家务;寒暑假,作者和弟弟会来小屋陪伴她。在这里,祖母讲述着家族故事、戏曲故事,她的声音承载着岁月的痕迹与浓浓的爱意,拉近了祖孙间的距离,也传承着家族的记忆。
小屋见证了祖母的坚韧。祖父早逝,为治病家中耗尽积蓄,祖母含泪卖掉珍贵嫁妆,却仍未留住祖父。此后,她独自面对生活的艰辛,抚养子女长大。她性格要强,即便与儿媳偶有矛盾,也默默承受。比如她和儿媳争吵后会憋气不来,但作者的母亲,即祖母的儿媳最终还是会让作者送水饺给祖母。这一送一接之间,展现出家庭关系的复杂与微妙,也体现了祖母对亲情的珍视与包容。
随着时间流逝,作者全家搬到镇上,祖母也离开了小屋。但小屋在作者心中的地位从未改变,它成为记忆中深刻的“胎记”。祖母虽已习惯新的生活,可她仍会念叨庄上先她而去的老人,怀念那给予她温暖与自由的小屋。因为小屋是她生活的一部分,是她与过去连接的纽带。
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人的记忆里也有这样的“小屋”,可能是故乡的老屋、儿时的庭院,它们承载着我们的成长、亲人的关爱,是情感的栖息地。无论我们走多远,这些地方永远是心灵的归处。就像作者对祖母的小屋的眷恋,即便时光流转,那份情感也永不褪色。
《娘家亲》写的是作者的姑奶奶对娘家人的关爱和深情,同样也感动了我。姑奶奶住在城里,但对家在农村的娘家人特别亲,特别关怀。他们每次进城来到姑奶奶家,都得到了热情的接待和关怀。“娘家亲“三个字,在盐城乡下孩子的童年记忆里,化作一件借来的红色确良衬衫、一支清凉的棒冰、一本新华书店的小人书,更化作姑奶奶那双布满皱纹却温暖如春的手。
这篇饱含深情的回忆散文,以孩童视角勾勒出一幅城乡互动的温情画卷,更在不经意间揭示了中国乡土社会中一个永恒的文化命题——”娘家亲”所承载的血脉亲情与文化基因,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持着惊人的生命力。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娘家”概念,远非一个简单的地理方位词。在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中,一个人以自己为中心,像石子投入水中形成的波纹一样,按亲疏远近划分人际关系。而”娘家”正是这波纹中最为特殊的一环——对女性而言,它是永远的精神原乡;对家族而言,它是血脉交织的证明。文中姑奶奶虽已嫁入城市多年,却始终保持着对顺潭港娘家人”掏心掏肺”的好,这种情感超越了时空距离与社会阶层的差异,反映了“中国人重家族,尤重母系”的现状,道出了中国亲情伦理的特殊构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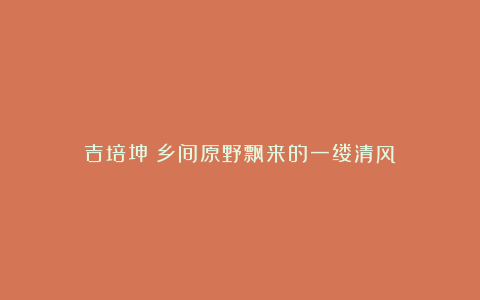
姑奶奶的形象,是传统“娘家亲”观念的生动诠释者。她虽居住在市区曹家巷,有着“洁癖”的生活习惯,却始终以娘家人的冷暖为己任。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她给予的不只是“各种罐头、点心、糖果”,更是一种无条件的接纳与认同。作者的一句话:“姑奶奶并没因我们是乡下人而有半点瞧不起“,这是一个孩童发自内心的对姑奶奶的评价。因为她肯定也看到不少进了城而疏远甚至讨厌、轻蔑乡下人的事例。
我们不是经常看到这样的例子吗?进了城,成了城里人,就自以为高人一等,就看不起至亲至爱的乡下亲戚,特别是穷亲戚。《珍珠塔》这出戏就是对这种人的无情刻画和鞭笞,教训极其深刻。现在城乡流动越来越普遍和常态化,我们希望,像作者的姑奶奶这样的好人、亲人越来越多,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
《回到最初,回到永远》这篇散文也是以细腻的笔触、真挚的情感,讲述了祖母生命最后阶段的经历,展现了祖孙之间深厚的情感以及祖母坚韧的一生,读来令人动容。
文章通过祖母从确诊肠梗阻到最终离世的整个过程,探讨了生命的脆弱与坚韧、亲情的温暖与力量。祖母在面对高龄与病痛时,展现出的对生活的无奈与对子女的牵挂,以及子孙们在祖母生命尽头的陪伴与不舍,都深刻地体现了生命的无常与亲情的珍贵。同时,祖母回顾自己一生的苦难与坚韧,也传达出一种面对生活的积极态度,即使历经磨难,依然对生活充满热爱,对子女充满深情,这种精神力量是文章主题的重要支撑。
祖母是文章的核心人物,作者通过多个细节展现了她的性格特点和生活经历。从她躺在推车上无力又伤心的话语中,可以看出她对病情的无奈和对生命的留恋;从她回顾自己一生的苦难,如“家里缺吃少穿”“最穷时招人白眼”等,可以看出她坚韧不拔的性格;从她叮嘱子孙要把自己的苦说给亲友听,可以看出她对生活的坦然和对子女深深的爱。祖母的形象立体鲜活,令人印象深刻。
作者对家人的描写也十分生动。父亲、二叔在得知祖母病情后的悲痛与无奈,弟弟开车抱祖母做检查时的忙碌,以及全家人在祖母生命尽头的陪伴与不舍,都展现了家人之间深厚的亲情。特别是弟弟说出埋藏多年的秘密,即奶奶牵着他到爷爷坟上痛哭,进一步深化了祖孙之间的情感,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
文章的语言质朴自然,没有过多的修饰,但充满了真挚的情感。作者用平实的语言描述了祖母生命最后阶段的点点滴滴,如“头发蓬乱,脸色瘦削干枯,每一根深凹的皱纹都像魔鬼的手指,根根潜藏危险”,这种细腻的描写让读者能够真切地感受到祖母的虚弱与痛苦。同时,作者在叙述过程中,也穿插了自己的内心感受,如“我竭力劝慰祖母,不怕,这里的医生也许有办法,但内心却在发慌”,这种情感的自然流露,使文章更具感染力。
《我把村庄带回家》看来是作者倾注了更多深情的一篇力作。它描写了生活中一种无奈的现代乡愁。以细腻的笔触记录了一个即将消失的村庄最后的身影,将个体记忆与集体命运交织在一起,呈现了城市化浪潮下中国乡村的生存困境与精神挽歌。
作者以“拆迁”这一极具中国现代性特征的事件为切入点,通过母亲坚守的几分自留地、被推倒的红砖青瓦老宅、即将走散的乡亲邻里等意象,构建了一幅饱含痛感的乡村消逝图景。这种痛感不仅源于物理空间的消失,更来自与之相连的生活方式、情感纽带和文化记忆的断裂。
文章中反复出现的“红砖”意象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作者特意从废墟中捡起一块红砖带回家,这个细节生动体现了物质载体对记忆的保存功能。砖瓦不仅是建筑的组成部分,更是家族历史的物质见证,承载着”父母曾用大半辈子积蓄和多少年积聚的苦力”的生命重量。
母亲与土地的关系构成了文章最动人的篇章。这位“从没有丧失对土地的信仰”的农村妇女,在脱离乡村苦力后依然坚持耕种几分自留地,其执着远超经济考量,本质上是一种存在方式的坚守。土地给予母亲的“踏实和自信”,是城市打工经历无法提供的生命确证。作者敏锐地捕捉到这种农耕文明特有的情感结构——在播种与收获的循环中,人获得与自然节律相和谐的存在感。
文章的独特价值在于坦诚面对了作者自身与乡村的复杂关系。作者不回避年轻时“发誓走出这块土地”的决绝,也不掩饰如今”城市浮萍”的迷茫。这种自我剖析揭示了现代化进程中青年人的精神困境:理性上拥抱进步,情感上眷恋传统。文章中引用艾青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来设问,实际上是对乡愁的当代重构。当土地不再是被耕种的对象而是另作他用时,爱该如何安放?作者没有给出简单答案,而是通过“愧疚之心”的自我审视,展现了城市化受益者的道德焦虑。
其实,我自己何尝不也有过这种惆怅?前几年回到我曾经插队的地方,农田不见了,知青屋不见了,熟悉的乡亲也不见了。地上盖起了20层的住宅高楼,头顶上架起了沈海高速的立交桥,汽车奔驰而过,心里产生出一种莫名的失落感。因为那里是我的第二故乡啊!这不也是一种乡愁吗?
《我把村庄带回家》最终呈现的是一种辩证的现代性体验。作者既清醒认识到“让村庄安全完整地活下去”只是一厢情愿,又坚持通过文字“把村庄带回家”的美好愿望。这种带回不是保守的带回,而是为快速前进的社会提供反思的参照点。文章中“莴苣香”的车厢细节表明,乡村并未完全消失,它以气味、味道、记忆等形式渗透进城市生活,构成现代人复杂身份认同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作者确实把村庄”带回家”了,不是作为物质存在,而是作为精神资源。
这篇散文的价值不仅在于记录了一个村庄的消逝,更在于它启示我们:在不可逆转的现代化进程中,如何通过文学叙事来安放那些无处安放的情感,如何让红砖的重量转化为思想的重量,如何使土地的体温温暖文字的体温。这或许是面对变迁最富尊严的告别方式。
感谢江华为我们送来了从乡间原野飘来的一缕清风。
(写于2025年5月17日)
点击以下蓝字,查看江华文章:
【作者简介】吉培坤,男,江苏盐城人。1948年生,1966年高中毕业,1968年农村插队,1969年开始担任民办教师,1977年恢复高考首批考取苏州大学政教系。毕业后一直在高校担任教学和教育管理工作,2008年退休。爱好文学,退休后创作了一些小说、散文、诗歌共60多万字。出版《七七级》小说散文集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