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么可能不来呢?这一整片的幽静,此刻都属于我。
满目花开的绚烂,是雕琢里的巧思,足以释然尘世的拘束,把身心张开来,扑进自然的怀抱。
我喜欢无人问津处,硕大的空无。
无波澜、无规训、无鼎沸、无虚伪,声色都是自然的模样,把生命的每一眼情衷都从容。
参天木交织成林,我听风中,有无数种声,是竹叶的狭长、是松针的细密、是梧桐的宽阔、是香樟的簌簌,就像叠翠里,是无数种绿色渐变,把生命的青涩到苍老一一描摹。
林木环绕的碧玉,锦鲤缭绕的烟波,一圈圈洇开年轮,又消散于澄澈。水草悠游的样子,不知是不是锦鲤摆弄的舒卷,清幽里含着风的冷寂,倒愈发显得苍翠。
湖心走廊隔着的山水,一半清澈见底,一半浮萍满翠。
穿过长廊,忽然听到啪嗒啪嗒的声音,是下雨了吗?我可没带伞……心里嘀咕着,眸子却被碧绿里含着烟粉的飘萍吸引,渐渐靠近,想把那氤氲的色泽看得真切些,顾不得响声愈大,雨意……
咦?没有下雨!可那声响……我侧耳贴近湖水,静静倾听,才发现,那是池中浮萍发出来的。是它们吗?啪嗒啪嗒,像芦苇裂开的声音。我被那声音迷住了,细细听着,仿佛有无数的力量在爆发,把生命的花朵一朵朵绽放。
若不是忽然有人闯入,叨扰了这一刻宁静,我还不知何时会离开。继续前行,穿过池杉密簇的小径,和草本园里的花花草草一一打过招呼,看过铁线莲的魅紫,七姊妹的明黄,忽地笑的簇拥,行过石拱桥的敦厚,踏过青苔翠染的窈窕,与林间蔓草丛生的荒芜同行,终于在湖畔烟草间,看到已成势的彼岸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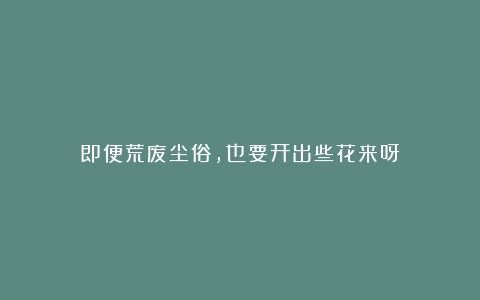
那样密簇的嫣红,一朵挨着一朵的,在静谧里开成热烈。一边是盛满树影落花的粼粼,一边是草色叠翠的荒寂,而它,开成连绵的红,连绵此岸与彼岸的交融。我是误打误撞来的看花人,有心花姿,无意叨扰,它想要的热烈与冷寂,我都不言语,只是看着,看着,看荒芜里开出艳丽来。
它是不会烫伤人的火,却灼灼眼眸。
一只在草本园就见过的蝴蝶不知何时也来了此处,它灵动、纤柔的翅膀,打碎这一刻平宁,似乎要在我彻底沉沦、化作一株彼岸花前,带我离开。仿佛世俗还有什么,是值得我归去的。
我就这样跟着它,着了迷似的,不知不觉走出了这片湖心岛,来到花径大道上。
一转身,它便消失不见了。
这世间还有什么值得我归去?
我环顾四周,大概就是这些花花草草了。好奇怪啊,投了人身,却被世俗冷漠,唯有草木相拥。就好像我的使命,便是用人类的文字记录草木的生命,就是去看树的年轮,花的旖旎,草的柔韧,看湖中波光,看竹动风来,看落花成雨,看莲开参禅。
一切风物在我眼中,在我鼻息里,在我笔墨间。
而我,也在这万物间。
是一声蝉鸣,是一片落叶,是一滴清雨,是一朵花开。引我来这尘世的蝶,是我的化身,还是我是它的化身?庄周梦蝶时,是以身外身吗?
无数答案,无数问题,能发问的生命,大抵还没有放弃生而为人的权利。屈子的《天问》不正是他对这个宇宙的无限思考吗?从太极到无极,是这小小身躯迸发的无限智慧。也是这短暂生命,对这无穷宇宙的探寻。
说到底,我们只是这人间的过客,借一副皮囊苟且,何以穷尽宇宙之思?不过一壶酒,一首诗,一蓑烟雨,一片林深,半梦半醒间,参得一点是一点,悟得什么是什么。
即便荒废尘俗,也要开出些花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