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点:
问题:在青少年早期,跨诊断多基因风险评分(PRS)、个性化功能脑网络(PFN)和总体精神病理学(p因子)之间有什么关联?
发现:在这项对青少年大脑认知发展(ABCD)研究的11873名9至10岁参与者进行的横断面分析中,成年期常见情绪相关精神病理学的PRS(PRS-F1)与青少年早期的p因子相关。p因子、PRS-F1和PRS-F2(捕捉成年期更严重的精神病性障碍)的个体间差异都与PFN(个性化功能脑网络)拓扑学相关。
意义:在这项研究中,跨诊断成年期精神病理学的多基因风险与青少年早期的p因子和PFN拓扑学都相关。本文发表在JAMA Psychiatry杂志。
摘要
重要性:功能性脑网络与行为和遗传因素都相关。为了揭示精神病理学的生物学机制,确定这些网络在发育过程中与遗传风险的空间组织关系至关重要。
目标:确定青少年早期跨诊断多基因风险评分(PRS)、个性化功能性脑网络(PFN)和总体精神病理学(p因子)之间的关联。
设计、地点和参与者: 青少年大脑认知发展(ABCD)研究是一项正在进行的纵向队列研究,在美国有21个采集点。本横断面分析包括2016年9月至2018年10月期间收集的ABCD基线数据。ABCD研究是一项多站点社区研究。样本主要通过学校系统招募。ABCD的排除标准包括会干扰研究方案和扫描仪禁忌症的严重感觉、智力、医学或神经系统问题。使用对半分组进行交叉验证,匹配了年龄、种族、家庭结构、利手、父母教育程度、地点、性别和麻醉暴露史。数据分析时间为2023年1月至2024年7月。
暴露因素: 从精神病学基因组学联盟和英国生物样本库数据集中的成年人中得出的跨诊断遗传因素F1(PRS-F1)和F2(PRS-F2)的多基因风险评分。PRS-F1指数化了与情绪障碍相关的常见精神症状和障碍的易感性;PRS-F2指数化了以躁狂和精神病为特征的罕见精神疾病形式的易感性。
主要结果和测量: 从青少年和父母报告的心理健康评估的双因素模型中得出的p因子,以及从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扫描中得出的个体特异性功能性脑网络拓扑学。
结果: 总共包括11873名9至10岁的儿童;其中5678名(47.8%)为女性,平均(标准差)年龄为9.92(0.62)岁。发现PFN拓扑学具有遗传性(影像学子样本,n = 7459;57.1%的顶点:平均h²为0.35;错误发现率校正P < .05)。PRS-F1与p因子相关(欧洲血统子样本,n = 5815;r为0.12;95% CI为0.09-0.15;P < .001)。功能性网络拓扑学的个体间差异与p因子(影像学子样本,n = 7459;平均r为0.12)、PRS-F1(影像学和欧洲血统子样本,n = 3982;平均r为0.05)和PRS-F2(n = 3982;平均r为0.08)相关。p因子和PRS-F1回归系数的皮层图相关(r为0.70;P = .003,置换检验,N = 1000)。
结论与相关性: 在这项研究中,跨诊断成年期精神病理学的多基因风险与青少年早期的p因子和遗传性PFN(个性化功能脑网络)拓扑学都相关。这些结果可能会增进我们对精神病理学发展驱动因素的理解。
引言
人类大脑皮层由支持知觉、运动、认知和情感功能的大规模功能性网络组成。网络之间和网络内部的功能连接已被证明可以解释行为和精神症状的变异性。有证据表明,这些网络是可遗传的,并与基因表达模式相关;因此,功能性网络测量可能是精神遗传风险的中间表型。标准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分析使用群体图谱,该图谱假设功能性网络在皮层结构上的空间布局——其功能性拓扑学——在个体之间是一致的。然而,最近的研究确定了功能性拓扑学中存在广泛的个体间变异,尤其是在联合皮层中。本研究使用精确功能性图谱来捕捉个体特异性的功能性神经解剖学,并研究其在青少年早期与跨诊断精神遗传风险和症状负担的关联。
精确功能性成像表明,个体的个性化功能性脑网络(PFN)拓扑学是高度可重复、稳定且能预测fMRI任务期间皮层激活模式的,为研究通过群体图谱方法无法获得的个体间拓扑差异的关联提供了新的机会。因此,发育中的PFN拓扑学已与认知和p因子(一种总体精神病理学的测量)相关联。已知成年期PFN拓扑学模式是可遗传的,但青少年时期PFN拓扑学的遗传基础及其与精神风险的关系仍不清楚。
为了描述精神症状和障碍之间的共享遗传结构,最近一项多变量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WAS)使用了基因组结构方程模型。该方法确定了两个跨诊断遗传因素F1和F2,它们解释了与欧洲血统成年人情感和精神病性精神病理学相关的大部分遗传变异。F1捕捉了与情绪障碍广泛相关的常见精神病理学,而F2捕捉了以躁狂和精神病为特征的罕见严重精神疾病形式。然而,F1和F2的多基因风险在青少年早期与总体精神病理学或大脑功能如何关联尚不清楚。
在本研究中,我们利用青少年大脑认知发展(ABCD)研究基线采集(11873名9至10岁的参与者)中包含的临床表型、基因分型、功能性神经影像学和双胞胎对富集,来研究总体精神病理学和功能性脑网络拓扑学的遗传基础。我们使用心理健康项目的一个双因素模型来定义p因子,这是一个已被证明具有可靠性、有效性和实用性的广泛精神病理学测量。基于Mallard等人的研究,我们计算了ABCD中F1(PRS-F1)和F2(PRS-F2)的多基因风险评分。与以往一样,我们使用非负矩阵分解来推导出PFN。我们假设成年期精神病理学的多基因风险在青少年早期与p因子和PFN拓扑学都相关。因此,我们试图研究:(1)p因子和PFN拓扑学的遗传性;(2)p因子与PRS-F1和PRS-F2之间的关联;以及(3)PFN拓扑学与p因子、PRS-F1和PRS-F2的关联。
方法
研究概述
本研究利用了2016年9月至2018年10月期间从ABCD脑成像数据结构(BIDS)社区收集中收集的基线样本,该样本包括来自美国21个地点的11873名9至10岁的儿童及其照顾者(补充1中的eMethods 1)。ABCD研究的参与者主要通过学校系统招募。那些有严重的感觉、智力、医学或神经系统问题,会干扰研究方案和扫描仪禁忌症的人被排除在外。照顾者提供了书面知情同意书,每个ABCD地点都获得了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一个集中委员会的机构审查委员会批准,以及每个相应机构的信赖协议或并行的本地审查。使用125个青少年和父母报告的心理健康项目,p因子通过一个双因素模型得出(图1A;补充1中的eMethods 2、eTable 1和eFigure 1)。基于Mallard等人的摘要统计数据,计算了潜在遗传因素F1(PRS-F1)(指数化常见情绪障碍形式的易感性)和F2(PRS-F2)(指数化精神病性障碍的易感性)的PRS(图1B)(补充1中的eMethods 3)。由于当前的GWAS局限性,PRS仅在欧洲血统的子样本(n = 5815)中计算,并通过回归去除前10个欧洲血统主成分进行调整。
图1. 总体精神病理学(P因子)、多基因风险评分(PRS)和个性化功能性网络(PFN)的推导
A,使用一个双因素模型捕捉了青少年大脑认知发展(ABCD)研究中9至10岁参与者的总体精神病理学,其中125个心理健康访谈项目中的每一个都加载到一个通用因子(p因子)和8个正交子因子中的一个(精神病症状[PSY]、躁狂症状[MAN]、对立违抗[OPP]、内化症状[INT]、注意力缺陷和多动[ADH]、躯体症状[SOM]、饮食失调[DSE]和创伤后应激[PTS])。 B,在欧洲血统的子样本中,基于Mallard等人的摘要统计数据计算了潜在遗传因素F1(PRS-F1)和F2(PRS-F2)的PRS,此处显示了其遗传(g)因子结构和载荷。F1概括了主要与情绪障碍相关的精神症状和障碍(精神病症状[PSY]、躁狂症状[MAN]、抑郁症状[DEP]、重度抑郁症[MDD]和双相情感障碍II型[BD2]),F2概括了主要与精神病相关的罕见、更严重的障碍(双相情感障碍I型[BD1]、分裂情感性障碍[SZA]和精神分裂症[SCZ])。
C,使用空间约束的非负矩阵分解将每个参与者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时间序列分解为个性化功能性网络(PFN),由每个参与者的一个17×59412的载荷矩阵定义,其中17对应于网络数量,59412对应于皮层顶点数量。载荷矩阵中的每个值量化了每个顶点属于该参与者某个网络的程度,我们称之为PFN拓扑学的概率性网络定义。
个性化功能性网络
神经影像数据使用ABCD-BIDS流程进行处理(补充1中的eMethods 4)。与以往的研究一致,我们连接了多达4次静息态扫描和3次任务态扫描的时间序列数据,并排除了数据不完整或头部运动过多的参与者,最终样本量为7459。为每个参与者的连接时间序列计算了平均逐帧位移,以总结扫描仪内的运动,并用作模型协变量。
个性化功能性网络(PFN)的生成与以往的研究一致。我们应用了正则化的非负矩阵分解,该方法正向加权与每个个体的连接fMRI时间序列协变的连接模式,以识别k = 17个个性化网络(图1C;补充1中的eMethods 5)。使用来自一个独立数据集中以往工作的群体共识图谱作为时间序列分解的先验。这为每个参与者产生了一个17×59412的载荷矩阵,其中17对应于网络数量,59412对应于皮层顶点数量。载荷矩阵中的每个值量化了每个顶点属于某个网络的程度,这是一个我们称之为PFN拓扑学的概率性网络定义。
统计分析
我们利用我们样本中的双胞胎对(254个同卵双胞胎和334个异卵双胞胎)来计算p因子和PFN顶点级拓扑学的遗传性,使用ACE扩展双胞胎设计模型,控制了OpenMX中的年龄、性别和地点(以及PFN模型的平均逐帧位移)。我们计算了线性混合效应模型来验证p因子、PRS-F1和PRS-F2之间的单变量关联,考虑了年龄和性别的固定效应以及家庭和地点的批次效应(补充1中的eMethods 6)。
接下来,我们对每个参与者的PFN载荷矩阵训练了岭回归模型,以识别与p因子、PRS-F1和PRS-F2评分的多变量关联。所有模型都包括了年龄、性别、地点和平均逐帧位移的协变量,这些协变量根据ABCD可重复匹配样本在两个对半分组中分别被回归去除。为了估计匹配子集之间的泛化性,使用了2折交叉验证:在一个子集中训练回归模型,并在一个未见过的子集中进行测试,然后交换训练和测试数据(补充1中的eMethods 7)。
为了进一步解释PFN(个性化功能脑网络)拓扑学与我们感兴趣的每个变量之间的多变量关联,我们分析了我们的岭回归模型的特征权重。特征权重定量地描述了每个网络载荷与感兴趣变量关联的强度和方向。正权重表示网络的载荷到顶点上与较高的评分(例如,高p因子)相关,负权重表示网络的载荷与较低的评分(例如,低p因子)相关。为了考虑特征之间的协方差结构,我们对权重应用了Haufe变换。我们在对半分组(匹配了年龄、种族、家庭结构、利手、父母教育程度、地点、性别和麻醉暴露史)之间平均了Haufe变换后的权重,并使用3种方法对其进行解释:顶点级区域重要性、网络级重要性和方向性网络拓扑学(补充1中的eMethods 8)。
结果
概述
ABCD基线样本包括11873名9至10岁的参与者(5678名[47.8%]为女性;平均[标准差]年龄为9.92[0.62]岁)。在这些参与者中,7459名符合PFN分析的影像学要求,5815名符合PRS分析的遗传学要求(欧洲血统),3982名同时符合两种标准。基于总样本中包含的254个同卵双胞胎对和334个异卵双胞胎对,我们发现p因子和PFN拓扑学都具有显著的遗传性。青少年时期由p因子指数化的跨诊断精神病理学与成年期情绪相关症状和状况的多基因风险(PRS-F1)相关。功能性网络拓扑学的个体间差异与p因子、PRS-F1和PRS-F2(捕捉成年期精神病性状况的多基因风险)相关。这些多变量关联主要由高阶联合网络的拓扑学驱动。我们发现与p因子和PRS-F1相关的个体化拓扑学存在趋同,而与PRS-F2相关的拓扑学则存在分歧。
P因子和PFN的遗传效应基础
首先,我们计算了p因子和PFN顶点级拓扑学的双胞胎遗传性(h²)。p因子的表型变异中,有相当一部分可归因于加性遗传效应(h²,0.54;95% CI,0.41-0.68;P < .001)(图2A)。共享环境(C)和非共享环境(E)效应对p因子变异的贡献较小(C,0.20;95% CI;0.09-0.30;E,0.26;95% CI;0.22-0.32)。对于PFN拓扑学,我们计算了所有非零方差PFN载荷的遗传性,并将这些值通过显著性阈值(错误发现率校正P < .05)映射出来,生成了17个网络遗传性图(补充1中的eFigure 2)。然后,我们将每个皮层顶点在17个网络中任何一个上的载荷的最大遗传性映射出来(图2B)。在这59412个遗传性估计值中,33901个(57.1%)具有显著的遗传性(最大h²的平均值 = 0.35;错误发现率校正P < .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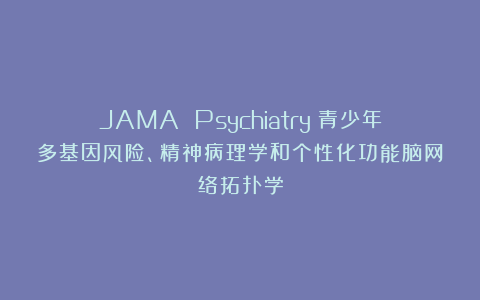
图2. 遗传效应是总体精神病理学和个性化功能性网络(PFN)拓扑学的基础
A,利用青少年大脑认知发展(ABCD)研究中包含的双胞胎数据,扩展的双胞胎设计模型揭示了p因子的加性遗传效应(A),或遗传性(h²)(h² = 0.54,95% CI,0.41-0.68,P < .001)。C表示共同环境效应;E表示非共享环境效应。误差条显示95% CI。
B,显示了给定皮层顶点在17个网络中的最大遗传性的图。在59412个皮层顶点中,33901个(57.1%)在错误发现率校正后具有显著的最大遗传性。
C,使用皮尔逊相关系数的p因子与多基因风险评分PRS-F1和PRS-F2之间的相关矩阵。
a 基于线性混合效应模型的P < .001。
接下来,我们通过检验p因子、PRS-F1和PRS-F2之间的相关性,研究了多基因风险与总体精神病理学之间的关联。我们发现p因子与PRS-F1相关(r, 0.12; 95% CI, 0.09-0.15; P < .001)(图2C),并在一个考虑了相关固定效应和批次效应的线性混合效应模型中得到验证(β, 0.11; 95% CI, 0.09-0.14; P < .001)(补充1中的eTable 2)。p因子与PRS-F2不相关(r, 0.03; 95% CI, 0.00-0.06; P = .05)(图2C);我们的线性混合效应模型的结果一致(β, 0.02; 95% CI, 0.00-0.05; P = .07)(补充1中的eTable 3)。此外,PRS-F2与任何正交子因子均不相关(补充1中的eFigure 3)。与报告的相关因子结构一致(图1B),我们发现PRS-F1和PRS-F2相关(r, 0.19; 95% CI, 0.17-0.21; P < .001)(图2C),并在我们的线性混合效应模型中得到验证(β, 0.18; 95% CI, 0.15-0.20; P < .001)(补充1中的eTable 4)。
PFN拓扑学与p因子、PRS-F1和PRS-F2个体差异的关联
为了研究PFN拓扑学与p因子之间的多变量关系,我们对参与者的PFN载荷矩阵和相应的p因子评分训练了岭回归模型,然后在未见过的数据中进行测试。模型性能,定义为实际p因子与模型拟合p因子评分之间的相关性,在对半分组A(r,0.12;95% CI,0.09-0.15)和对半分组B(r,0.12;95% CI,0.09-0.15)中都具有显著性(图3A)。
图3. 个性化功能性脑网络(PFN)拓扑学与p因子和多基因风险评分(PRS-F1和PRS-F2)个体差异的关联
A-C,使用模型性能评估了PFN拓扑学与p因子、PRS-F1和PRS-F2之间的多变量关联,模型性能定义为实际评分(p因子、PRS-F1或PRS-F2)与由PFN训练的岭回归模型产生的模型拟合评分之间的相关性。在对半分组A(SHA;rA)和对半分组B(SHB;rB)子集中,p因子(A)、PRS-F1(B)和PRS-F2(C)的实际评分和模型拟合评分之间都发现了显著的相关性。
D,模型性能的置换检验(N = 1000)显示,PFN拓扑学与p因子、PRS-F1和PRS-F2(彩色点)的关联都显著高于偶然水平。
E,重复的随机2折交叉验证(2F-CV;N = 100)显示了模型性能在随机样本对半分组中的稳定性。
a P < .01;箱形图显示了零分布。
然后,为了研究PFN拓扑学与精神病学多基因风险之间的多变量关联,我们对PFN载荷矩阵和相应的F1和F2 PRS训练和测试了岭回归模型。发现PRS-F1(对半分组A:r,0.05;95% CI,0.01-0.10;对半分组B:r,0.07;95% CI,0.03-0.12)(图3B)和PRS-F2(对半分组A:r,0.08;95% CI,0.04-0.12;对半分组B:r,0.08;95% CI,0.04-0.13)(图3C)的实际和模型拟合评分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
置换检验(N = 1000)表明,PFN拓扑学与我们每个变量(p因子、PRS-F1和PRS-F2)之间的多变量关联都显著高于偶然水平(图3D)。为确保对数据划分的鲁棒性,我们将样本随机划分为对半分组100次,证明了PFN模型在p因子(平均r,0.12)、PRS-F1(平均r,0.05)和PRS-F2(平均r,0.08)上的性能在各个子集中是稳定的(图3E)。扫描仪制造商不影响模型性能(补充1中的eFigure 4)。
驱动PFN拓扑学与P因子、PRS-F1和PRS-F2关联的皮层区域
为了识别驱动PFN拓扑学与p因子、PRS-F1和PRS-F2之间关联的重要皮层区域,我们在顶点水平评估了我们的岭回归模型的权重。将跨网络求和的权重大小映射到皮层表面,揭示了驱动PFN拓扑学与p因子(图4A,上)、PRS-F1(图4B,上)和PRS-F2(图4C,上)关联的区域,其中一部分达到了统计显著性(无阈值聚类增强,家族错误率校正P < .05)(补充1中的eFigure 5)。还推导出了单个网络的未求和权重图(补充1中的eFigure 6-8)。
图4. 驱动个性化功能性脑网络(PFN)拓扑学与P因子和多基因风险评分(PRS-F1和PRS-F2)关联的皮层区域
A-C,在每个顶点,将Haufe变换后的模型贡献权重的绝对值跨网络求和,揭示了驱动PFN拓扑学与p因子(A,上)、PRS-F1(B,上)和PRS-F2(C,上)关联的区域。显示了拟合到p因子(A,下;平均h² = 0.42)、PRS-F1(B,下;平均h² = 0.42)和PRS-F2(C,下;平均h² = 0.42)的PFN模型的前1%贡献权重顶点(对应于上排箭头区域)的双胞胎遗传性(h²)图(完整的PFN遗传性图显示在图2B中;所有图的前贡献权重顶点主要位于外侧皮层,内侧皮层未显示)。
D,3个模型贡献权重图的相关矩阵。
a 基于参与者水平置换检验(N = 1000)的P = .003;基于常规旋转检验(N = 1000)的P < .001。
鉴于发现p因子具有遗传性(图2A),并且PRS-F1和PRS-F2是遗传变量,我们预计对PFN与这些变量的关联有强烈贡献的区域也应具有显著的双胞胎遗传性。为了检验这一假设,我们研究了对p因子、PRS-F1和PRS-F2贡献最大的1%权重顶点(即最重要的特征)的PFN载荷遗传性(图2B)。与p因子和PRS-F1相关的顶部区域主要位于背外侧和腹内侧前额叶皮层。这些区域的顶点几乎都具有显著的遗传性(p因子簇:594个中有588个[99.0%];PRS-F1簇:594个中有586个[98.7%]),并且平均遗传性很高(p因子:h²,0.42;PRS-F1 h²,0.42)(图4A,下;图4B,下)。与PRS-F2相关的顶部顶点主要位于颞顶交界处,也几乎都具有显著的遗传性(594个中有573个[96.5%]),平均遗传性为0.42(图4C,下)。
如果PRS-F1与p因子之间的关联(图2C)反映在功能性脑网络组织中,我们可能会期望PRS-F1和p因子的贡献权重图之间存在共享的空间模式。我们使用参与者水平的置换检验,检验了所有3个权重图之间相关性的显著性。确实,我们发现PRS-F1和p因子的权重图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r,0.70;P = .003,置换检验,N = 1000)(图4D),在常规旋转检验中也显著(P < .001)。相比之下,PRS-F2和p因子的权重图没有发现显著相关性(r,0.23;置换检验P > .99;旋转检验P = .06)(图4D)。
驱动PFN拓扑学与P因子、PRS-F1和PRS-F2关联的网络
我们接下来试图确定驱动PFN拓扑学与p因子、PRS-F1和PRS-F2之间关联的网络。为此,我们评估了每个网络内顶点对p因子(图5A,上)、PRS-F1(图5B,上)或PRS-F2(图5C,上)模型的总体重要性,其中每个网络的求和权重值按网络大小进行归一化。p因子和PRS-F1共享了两个最重要的网络:15,一个额顶(FP)网络,和7,一个腹侧注意(VA)网络。与PRS-F2相关的两个最重要的网络是不同的:3,一个不同的FP网络,和9,一个不同的VA网络(图5D)。
图5. 驱动个性化功能性脑网络(PFN)拓扑学与P因子和多基因风险评分(PRS-F1和PRS-F2)关联的网络
A-C,上,每个网络对PFN与p因子(A,上)、PRS-F1(B,上)和PRS-F2(C,上)之间多变量关联的累积特征重要性。实心条反映了基于参与者水平置换(N = 1000)在错误发现率校正后P < .05的显著性。A-C,中,为确定与我们感兴趣的变量正相关的网络拓扑学,我们确定了每个顶点在17个网络中的最大正Haufe变换模型权重,按前10%和25 mm²聚类阈值进行阈值化,并将每个保留的顶点分配给其最大正权重对应的网络。这导致了与高p因子(A,中)、高PRS-F1(B,中)和高PRS-F2(C,中)相关的PFN拓扑学图。A-C,下,使用每个顶点在17个网络中的最大负Haufe变换模型权重,我们推导出了与低p因子(A,下)、低PRS-F1(B,下)和低PRS-F2(C,下)相关的PFN拓扑学图。
D,供参考的PFN群体图谱的硬分割。
E,显示高p因子(A,中)和高PRS-F1(B,中)图之间前额叶皮层共享拓扑的联合图。
F,显示低p因子(A,中)和低PRS-F1(B,中)图之间前额叶皮层共享拓扑的联合图。
AU表示听觉;DA,背侧注意;DM,默认模式;FP,额顶;SM,躯体运动;VA,腹侧注意;VS,视觉。
接下来,我们试图了解这些关联背后的特定网络拓扑学。为确定与p因子、PRS-F1和PRS-F2正相关的网络拓扑学,我们将对应于前10%最正权重的顶点分配给各自的网络。这导致了与高p因子(图5A,中)、高PRS-F1(图5B,中)和高PRS-F2(图5C,中)相关的PFN拓扑学图(前1%和5%显示在补充1的eFigure 9A-B,上)。值得注意的是,高p因子和高PRS-F1图之间存在大量共享拓扑(5941个顶点中有2456个共享[41.3%])(补充1的eFigure 10A,上)。共享的正拓扑主要位于前额叶皮层(图5E),包括FP网络3和17、默认模式(DM)网络1和12以及VA网络7和9。高PRS-F2图的拓扑与p因子的拓扑不同(5941个顶点中有125个共享[2.1%])(补充1的eFigure 10B,上),其中FP网络3和17、DM网络1和8以及VA网络9主要位于颞顶交界处(图5C,中)。
同样,我们将网络身份分配给前10%的最负权重,从而得到与低p因子(图5A,下)、低PRS-F1(图5B,下)和低PRS-F2(图5C,下)相关的PFN拓扑学图(前1%和5%显示在补充1的eFigure 9A-B,下)。低p因子和低PRS-F1图之间存在大量共享拓扑(5941个顶点中有1711个共享[28.8%])(补充1的eFigure 10A,下)。共享的负拓扑主要位于前额叶皮层(图5F),包括FP网络17、DM网络12、VA网络7和9以及背侧注意(DA)网络14。低PRS-F2图的拓扑与p因子的拓扑不同(5941个顶点中有269个共享[4.5%])(补充1的eFigure 10B,下),其中DM网络8、VA网络9和DA网络14主要位于颞顶交界处(图5C,下)。
讨论
在这项横断面研究中,我们应用了精确的功能性脑图谱来证明青少年早期多基因风险与功能性网络组织的个体差异之间存在关联。与我们和他人的先前研究一致,我们发现PFN拓扑学与精神病理学相关,此外,拓扑学与p因子和PRS的关联主要由联合网络驱动。p因子和PRS-F1之间的特定皮层区域和网络拓扑学趋同,而PRS-F2则不同;这与我们的发现一致,即PRS-F1与p因子相关,而PRS-F2则不相关。此外,我们的研究复制了以往的研究,显示了p因子的双胞胎遗传性,并通过证明其在发育过程中的遗传性,扩展了先前关于成年期PFN拓扑学遗传性的发现。以往的研究证明了ABCD中PFN拓扑学具有出色的重测信度(组内相关系数:0.84-0.99),支持了我们遗传性和多变量关联结果的稳健性。总之,这些发现证明了青少年早期跨诊断成年期精神病理学的多基因风险与p因子和遗传性PFN拓扑学之间存在关联。
我们的结果表明,PRS-F1,即成年人中常见精神症状、重度抑郁症和双相情感障碍II型的易感性,与青少年早期的p因子相关。这与先前的文献一致,其中成年人衍生的抑郁症和神经质的PRS与青少年的普遍精神病理学相关,包括在ABCD中描述的关联。相比之下,PRS-F2,即成年人中精神分裂症、分裂情感性障碍和双相情感障碍I型的易感性,与我们样本中的p因子或任何子因子评分均不相关,这表明精神病性障碍的遗传风险在这个发育阶段尚未在表型上可检测到,至少在一个没有富集临床高危个体的社区样本中是如此。
使用经过验证的精确功能性脑成像方法和我们机器学习模型的严格交叉验证,我们发现PFN拓扑学与PRS-F1和PRS-F2都相关。与PRS-F2的这种关联意味着精神病性障碍的遗传风险可能在临床表现之前就反映在发育中的大脑拓扑学中。驱动PFN拓扑学与PRS-F1和PRS-F2关联的主要区域在双胞胎ACE模型中都具有高度的遗传性,这与先前关于功能性脑网络遗传和多基因基础的文献一致。然而,据我们所知,本研究是首次证明精神病学PRS(多基因风险评分)与个体特异性功能性网络拓扑学之间存在关联。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关联的效应量很小。然而,先前的研究表明,小样本倾向于夸大效应量,而像本研究这样的大样本则提供更稳健的估计。
与p因子和PRS-F1相关的皮层区域和网络拓扑学非常相似,主要位于背外侧和腹内侧前额叶皮层。以往的文献发现,这些区域在神经精神疾病,包括情绪障碍中发生了改变,可能与它们在情绪调节、执行功能和奖赏相关过程中的功能有关。相比之下,与PRS-F2相关的皮层区域和网络拓扑学是不同的,主要位于颞顶交界处。先前的研究报告称,该区域在精神分裂症中发生了改变,特别是在有听觉言语幻觉的患者中,这可能与语言处理功能障碍有关。尽管存在这种拓扑学的差异,但额顶网络在p因子、PRS-F1和PRS-F2模型中都表现出最大的重要性,这与最近的证据一致,即额顶连接的中断是情感障碍和精神病性障碍的共同特征。
局限性
应该注意几个局限性。首先,PRS-F1和PRS-F2不包括神经发育障碍,例如自闭症或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未来的精确脑图谱研究应该调查包含更多样化障碍的跨诊断风险评分。其次,多基因风险可能只占PFN拓扑学总遗传性的一小部分;未来的工作应该研究与其他遗传因素(例如拷贝数变异)的关系。第三,p因子是跨诊断精神病理学的一个低维表示,它捕捉了障碍之间的高度共病性和领域级测量(例如,内化和外化);然而,未来的研究可能会表明,更细致的领域级测量与遗传风险因素的相关性更强。第四,本研究是横断面的,这促使未来的纵向研究利用ABCD后期的影像学时间点来获得更深入的因果见解。
结论
本文试图利用精确的功能性图谱来揭示精神疾病出现的生物学机制。总之,目前的结果是理解青少年早期跨诊断精神病理学遗传和功能驱动因素的一个有意义的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