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土地上的进退褶皱(小说)
作者‖听雨赏蕉
编者按:该小说告诉我们,在现代化冲击下,传统乡村面临“人地分离”的生存困境:土地荒芜与人口空心化的互为因果,折射出代际价值观断裂与乡村振兴的深层矛盾。
黄土高原夏天的清晨总是来得格外的早。当张思源老人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时,东边的天空才刚透出一丝鱼肚白。他站在院里,深深吸了一口清凉的空气,那股子熟悉的黄土味直抵肺腑——土腥里带着一点儿野草的芳香,还有远处传来的炕烟微熏的味道。
“今年这夏咋这么燥。”他自言自语,用粗糙的手掌搓了搓脸。脸上的皱纹像旱季龟裂的土地,一道一道的,刻着六十五个春秋的风霜。
大门口的太阳能路灯还亮着微弱的光,天越亮它越暗,像个守夜的老人,见着晨光便想歇息了。张思源抬头看了看那路灯杆子,心里五味杂陈。十年前村里统一装的,说是“亮化工程”,每家门口一盏。那时候还热闹,安装那天,村里老老少少都出来看稀奇,娃娃们围着灯杆转圈圈。如今,灯还在,人却少了。
水泥路从他家门口一直延伸到村口,又分出许多岔路,通到各家各户。路修得平整,可上面难得见个车印子。张思源记得修路那会儿,县里来了人,说这是“村村通”工程。要致富先修路。结果,路通了,人却跑了。
老伴王秀英从灶房出来,端着两碗小米粥:“站着发啥愣,趁热喝。”
张思源接过碗,蹲在门槛上喝起来。粥烫,他吹一口喝一口,眼睛却望着对面山坡上那一排排空房子。刘家的红铁门生了锈,赵家的窗户玻璃碎了两块,李家的院墙塌了一个角……!这些房子,大多都锁了十几年了。
“昨晚老李家的狗叫了半宿。”王秀英也蹲下来,小声说。
“怕是黄鼠狼进院了。”张思源闷声道。
“不是,我隐隐约约听着好像是……好像是有人的声音。”王秀英顿了顿,“老李一个人半瘫在炕上快半年了,有个头疼脑热的全凭小保姆照看着。这不小保姆的母亲有病,回去半个月了,但愿老李不会有什么事,一会你上山了我去看一下。”
张思源不说话了,只是喝粥的声音更响了。他知道老李的情况,三个孩子都在城里贷的款买了房,每年回来几次,带点东西给点钱,照顾不了几天就走了。老李去年中风,左半拉身子不听使唤,孩子们要接他去城里,他死活不去,说死也要死在自家炕上。没办法,就请了个远方亲戚的女儿当保姆来看护。
喝完粥,张思源扛起锄头往自家地里走。水泥路走完了,拐上土路,路两边的景象让他心里发沉。好好的梯田,一层一层的,往年这时候该是绿油油的麦苗快拔节了,如今好多地块却长满了蒿草。有些地里的草比人还高,风吹过,哗啦啦地响。
“多好的地啊……”张思源喃喃道。他记得小时候,这面坡上全是人,耕种时节,吆喝声、牛铃声、鞭子响,热闹得很。那时候北坪村三百多口人,春天往地里一站,黑压压一片。现在呢?全村剩下不到六十人,还都是些“老棺材瓤子”——这是村里人自嘲的话。
到了自家地头,张思源放下锄头,没急着干活,先坐在地埂上卷了根旱烟。火机打着的一瞬间,他注意到自己手背上凸起的青筋和深褐色的老年斑。老了,真的老了。可这地还得种,不种吃啥?虽然儿女每月寄钱,但庄稼人不下地,心里空得慌。
烟雾缭绕中,张思源望着远处荒芜的土地发呆。会宁这地方,十年九旱,可祖祖辈辈还是在这黄土地上刨食吃。如今政策好了,不用交公粮了,还有补贴,可种地的人没了。年轻人都嫌种地不挣钱,一窝蜂往城里跑。在建筑工地搬砖、在餐厅端盘子、在工厂流水线上……反正干啥都比种地强。挣了钱,第一件事就是在城里买房,贷款也要买,首付凑不够,把父母的棺材本都掏空了。
张思源的两个儿子一个闺女都在城里。大儿子建国在兰州开了个小超市,贷了三十万买的房;二儿子建军在银川跑运输,车和房都是贷款买的;闺女建梅最出息,在西安当老师,可也一样,房贷要还二十年。孩子们不容易,张思源知道。每次打电话,都说忙,都说累,都说压力大。去年过年,三个孩子都没回来,说假期短,车票难买,还要加班多挣钱还贷。
“爸,妈,你们也来吧,在城里享享福。”孩子们总这么说。
张思源和王秀英去住过。在兰州大儿子家住了两个月,在银川二儿子家住了两个月,在西安闺女家住了一个月。哪都待不惯。楼太高,人太挤,空气里有股怪味。进门要换鞋,上厕所用马桶,吃的肉没有个肉味。最难受的是没个说话的人,儿子儿媳上班,孙子孙女上学,老两口整天对着电视,像两台值班的机器。
“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狗窝。”王秀英说。
张思源深以为然,再破的窑洞也是自己的。开门是河川,抬头是蓝天,想蹲哪就蹲哪,想喊啥就喊啥。可这话他不敢跟孩子们说,怕伤他们的心。孩子们也是为他们好,觉得老家穷,条件差,接他们去城里是尽孝。
一根烟抽完,张思源起身开始锄洋芋地里的草。自家的十亩地,他种了两亩麦子,两亩胡麻 ,两亩洋芋。年纪大了,种不了太多,剩下的地流转不出去——没人要。村里像他这样还种地的老人不超过二十个,加起来种的地也就百十来亩。北坪村原来有三千多亩耕地,现在十之八之九都荒着。
锄了没一会儿,张思源听见远处有人喊:“思源叔!思源叔!”
他直起腰,看见村支书王有福骑着电动车从路上过来。王有福四十出头,算是村里的“年轻人”了。他本来也在银川打工,三年前老支书去世,镇上找他谈话,让他回来当支书。他犹豫了很久,最后回来了,因为父母老了,孩子要上学,城里花销太大。
“有福啊,啥事?”张思源问。
王有福停好车,走过来,脸色不大好:“老李……走了。”
张思源手里的锄头“哐当”一声掉在地上:“啥时候的事?”
“就昨晚。保姆走了半个月了,早上他邻家去送饭,敲门没应,翻墙进去,人已经硬了。”王有福掏出烟,递给张思源一根,自己点上一根,“得安排后事。”
两人沉默地抽着烟。黄土高原的风吹过,卷起细细的沙尘。远处,一轮红日正从田岔梁上升起,把天地染成一片橘红。这景象张思源看了六十多年,可今天觉得格外苍凉。
“他的孩子们通知了吗?”张思源问。
“电话通知了,老大说今天下午赶到,老二和闺女在上海,赶回来到明天了。”王有福吐了口烟圈,“问题是……抬棺的人凑不齐。”
张思源心里一沉。按会宁的风俗,老人去世要停灵三天,出殡时要八个“抬重人”抬棺,显得此人一生劳苦功高。以前这事不难,村里青壮年多,谁家有事一招呼就来。现在呢?全村六十来人,一半是老头,剩下的是老太太。最年轻的也六十了,还有像老李这样瘫了的,像刘老五那样肺气肿走几步就喘的……
“能凑几个?”张思源问。
王有福掰着手指头数:“你,我,老赵,老刘,老马……满打满算五个。还差三个。”
“从外村请?”
“请了,都难。周围村子情况差不多,年轻人都进城了。镇上倒是能雇人,可要钱,电话上沟通过老李孩子们愿意出,但……”王有福没说下去。
但什么?但钱买不来乡情,买不来那种一家有事全村帮忙的热乎劲。张思源懂。葬礼不只是把死人埋了,更是一种仪式,一种告别,一种传承。抬棺的人不单单是出力,更是送老邻居最后一程的情分。用钱雇人,味儿就变了。
“我再问问,看还有谁能搭把手。”张思源说。
“七十往上的不敢让抬,万一有个闪失……”王有福摇头,“思源叔,你说这叫啥事嘛。路修好了,灯安上了,家家户户门口能开进小汽车了,可没人了。乡村振兴,乡村没人,咋振兴?”
这话问得张思源心里发堵。他想起去年镇上开会,领导讲乡村振兴,讲产业兴旺,讲生态宜居。可没人,啥都是空谈。房子建得再漂亮,没人住;路修得再展坬,没人走;地整得再平展,没人种。北坪村像一具被抽干了血的躯体,空有一副骨架。
“先不说这个,先把老李送走。”张思源弯腰拾起锄头,“我回去换身衣裳,过去帮忙。”
回到家,王秀英已经知道了老李的事,眼圈红红的:“多好个人,说走就走了。前两天还说要吃我做的荞面浆水节节呢。”
张思源沉默地换了身深色衣裳。王秀英从柜子里翻出一块黑布,撕成两条,一条系在自己胳膊上,一条递给张思源:“老李属蛇,今年是本命年,没想到没熬过去。”
去老李家的路上,张思源碰见几个老人,都往老李家去。大家互相点点头,脸色凝重。这些老伙计,见面越来越少,不是在炕上躺着,就是在医院住着,聚得最齐的时候,往往是在葬礼上。
老李家已经有人了。邻家的几个老太太在帮忙烧水,准备事情的饭菜,几个老头给老李净身换衣。老李躺在炕上,眼睛微睁,嘴半张,像还有话没说完。张思源走过去,轻轻把他的眼睛合上。手触到皮肤,冰凉。
“老哥,一路走好啊。”张思源低声说着,泪水滴在手上。
王有福在院里张罗着搭灵棚。材料是从镇上买的现成的,几个老汉帮忙组装。要是在以前,灵棚都是自家立木头、扯白布搭的,村里男人一起上手,边说边干,一会儿就搭好了。现在人少,买的现成的省事,可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中午时分,老李的大儿子李红军赶回来了,开着一辆白色小轿车。车在水泥路上开得顺畅,一直停到老李家门口。李红军四十多岁,穿着西装,一下车就跪在院里哭:“爹啊!儿子不孝啊!”
哭声在空旷的山村里回荡,惊起远处树上的几只麻雀。张思源看着,心里不是滋味。老李半瘫快半年了,李红军回来过四五次,每次伺候一晚就走。说忙,说生意离不开人。如今哭得再伤心,人也回不来了。
李红军哭完,起身找王有福商量后事。听说抬棺人凑不齐,他皱起眉头:“钱不是问题,雇人吧。镇上不是有殡仪服务公司吗?”
“有是有,可……”王有福欲言又止。
“那就雇。八个抬棺的,再加四个换手的,都要壮劳力,多少钱我出。”李红军很慷慨。“不能让我爹走得不体面。”
张思源在旁听着,心里像堵了块石头。体面?什么是体面?一群人热热闹闹送老人上山是体面,还是花钱雇陌生人走个过场是体面?可这话他说不出口,李红军也有难处,他在兰州开餐馆,确实忙,能赶回来就不错了。
下午,陆陆续续又来了几个老人。大家坐在院里,说老李的生平,说他年轻时多能干,说他做的臊子面多香。说着说着,就说到自己身上。
“下一个不知道轮到谁。”赵老汉说。他七十八了,冠心病,每天吃药。
“轮到谁是谁,反正都是迟早的事。”刘老汉接话。他儿子在新疆,三年没回来了。
“我现在就怕死在炕上没人知道。”马老汉最直接,“我家那婆娘耳背,我要是半夜走了,她怕是天亮才知道。”
老人们说着这些,语气平淡,像在说明天的天气。张思源听着,心里一阵阵发凉。这就是他们这代人的结局吗?生在黄土,长在黄土,最后埋在黄土,可送行的人越来越少,仪式越来越简单,情分越来越淡。
傍晚,帮厨的王秀英招呼大家吃饭,做的油饼和粉汤。老人们凑在一起吃,李红军吃不下,在屋里守灵。太阳落山时,村里亮起了太阳能路灯,一盏一盏,像散落在山坳里的星星。
张思源蹲在老李家院门口抽烟,看着那些路灯发呆。多好的光啊,把路照得明晃晃的。可照给谁看呢?晚上村里根本没人走动。
王有福走过来,蹲在他旁边:“思源叔,想啥呢?”
“想曹北坪,往后咋办。”张思源实话实说。
王有福叹口气:“镇上开会,说要搞乡村振兴,搞乡村旅游,搞特色种植。可没人,啥都搞不起来。年轻人在城里买了房,贷着款,不敢回来,也回不来。咱们这些老家伙,能奈何几年?”
“娃娃们在城里也不容易。”张思源说,“建国去年跟我说,超市生意不好做,房贷一个月三千多,孩子补习班一个月两千,压得喘不过气。我说那你回来,他说回来干啥?种地?一年挣的钱不够一个月房贷。”
“这就是矛盾啊。”王有福用树枝在地上划拉着,“城里房价高,生活成本高,年轻人压力大;农村没人,地荒着,产业起不来。我们是两头难。”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山风渐起,带着凉意。张思源望着远处黑黝黝的山峦,突然想起小时候,爷爷跟他说的话:“黄土养人,也留人。走得再远,根还在这。”
可现在的年轻人,根还在吗?他们在城里出生长大的孩子,都说着普通话,还会说地地道道的会宁话吗?还知道荞麦怎么种、胡麻怎么收、谷子怎么碾吗?还记得清明上坟、十一送寒衣、腊月祭灶吗?
也许,“根”不是“地”,是“人”。人在哪,根就在哪。人在城里扎下了,根就慢慢从黄土里拔出来了。
“有福,你说咱们能不能……”张思源犹豫了一下,“能不能让年轻人回来?”
“咋回来?回来干啥?种地不挣钱,办厂没条件,搞旅游没特色。”王有福苦笑,“咱们会宁有啥?黄土、干旱、坡地。风景比不上甘南,古迹比不上敦煌,特产……就有点小杂粮,可不成规模。”
张思源不说话了。他知道王有福说得对,可心里就是不甘。北坪村是他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他的太爷爷埋在东山,爷爷埋在西坡,爹娘埋在北梁。这片土地养活了张家十几代人,如今要荒了,要空了,他心里疼。
夜里守灵,张思源和李红军一起。烛光摇曳,老李的遗像在供桌上微笑,那是他七十岁生日时照的,精神还好。
“张叔,谢谢你帮这么大的忙。”李红军递过来一支烟。
张思源接过,点上。“应该的。你爹和我是一辈子的连手。一起修过梯田,一起赶过集,一起割麦子,一起……算了,不说这些。”
“我爹常念叨你们。”李红军看着遗像,“你们这一茬人,越来越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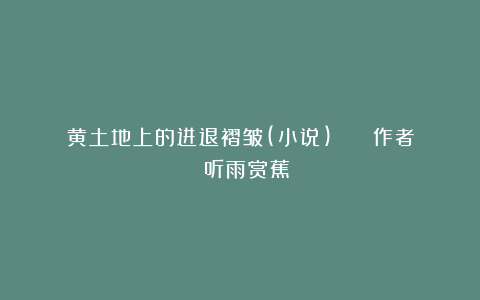
“是啊,走一个少一个。”张思源吸了口烟。“红军,你在兰州,生意咋样?”
“勉强维持。”李红军实话实说。“这两年餐饮不好做,房租涨,人工涨,但菜价不敢涨,怕顾客跑了。房贷还有十五年,想想都愁。”
“没想过回来?”
李红军愣了一下,苦笑:“回来干啥?种地?我二十年没摸过锄头了。做生意?咱们村就几十个老人,消费能力有限。孩子教育更是问题,村里小学八个老师六个学生。大多都到镇上县上读书去了。”
句句在理,句句扎心。张思源知道,不是年轻人不想回来,是回不来。城里有他们的房子、工作、孩子的学校、医院的医保……他们已经离不开城市了。就像鱼进了海,再也回不了小溪。
后半夜,李红军撑不住,在旁边的床上眯着了。张思源一个人守着,看着跳动的烛火,思绪万千。他想起了北坪村最热闹的时候,那是一九八十年代末,村里三百多口人,春天播种,秋天收获,打谷场上堆满粮食,孩子们在麦秸堆里打滚。过年时,社火队从村头耍到村尾,锣鼓喧天。谁家娶媳妇,全村人都去吃席,酒能从中午喝到晚上……
那些热闹,那些烟火气,怎么就没了呢?
是时代变了吗?当然是。时代变了,农村该何去何从?
张思源想不通。他知道国家重视农村,好政策一个接一个,脱贫了,路修了,灯亮了,网通了,可人还是留不住。问题出在哪?
也许,出在“活法”上。以前农民就一种活法:种地、吃饭、生孩子、养老。现在活法多了,年轻人想要更好的生活,这没错。可如果所有年轻人都进城,农村谁来继承?土地谁来耕种?老人谁来照顾?文化谁来传承?
这些问题像一团乱麻,缠在张思源心里,越缠越紧。
第二天,老李的二儿子和闺女都回来了,雇的抬棺人也到了,八个壮汉,开着一辆面包车来的。葬礼按程序进行,但总觉得少了些味道。哭丧时,只有自家人哭,邻里老人们默默看着;抬棺时,雇来的人喊着号子,步调一致,可脸上没表情,像在完成一项隐秘的任务;下葬时,亲戚们轮流填土,可帮忙的邻居太少,坟堆堆得不大。
张思源帮着填完最后一锹土,站在新坟前,突然感到一阵深深的疲惫。不是身体累,是心累。老李走了,下一个是谁?是他自己吗?他走的时候,会不会也这么冷清?孩子们会不会也雇人来抬棺?
送完老李回家的路上,张思源走得很慢。路过自家地时,他停下来,看着那片绿油油的麦田。麦子长得真好,今年雨水虽然不多,但够用,看样子能有个好收成。可收了又怎样?自己吃不完,卖又卖不上价,给孩子们寄去,他们嫌重嫌麻烦。
“思源叔!”有人喊他。
张思源回头,看见王有福骑着电动车过来:“镇上通知,明天有个乡村振兴调研会,各村代表都得去,你跟我一起去吧。”
“我去干啥?我又不是村干部。”
“你是老人,有见识,说说咱村的实际情况。”王有福说,“光我去说不够,得让领导听听老百姓的心声。”
张思源想了想,点点头:“行。”
第二天,张思源穿上最体面的衣裳——一件深蓝色中山装,是十年前儿子买的,平时舍不得穿。王有福开着他那辆旧电动车,载着张思源往镇上去。
路上,他们经过好几个村子,情况都差不多:高大的砖瓦新房不少,但没几户冒烟;小汽车停在院里,但蒙着灰;地里蒿草比庄稼多。偶尔看见个活物,原来是乱跑的野狗。
镇上会议室里,坐了二十几个人,都是各村代表。领导讲话,说乡村振兴是大事,要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然后让大家发言,说说各村情况,有啥困难,有啥建议。
轮到王有福时,他站起来,清了清嗓子:“我是北坪村的支书王有福。现在叫我们村的张思源老人说一说我们村的情况。”
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思源老人显得有些紧张。”我们村的情况是:路修好了,灯安上了,网通了,自来水入户了,可没人了。原来三百多口人,现在不到六十,全是老人。地荒了十之八九,房子空了三分之二。昨天我们村埋了个老人,抬棺的人都凑不齐,最后是花钱雇的人。”
会议室里一阵沉默。领导脸色凝重:“其他村呢?”
其他村代表纷纷举手,情况大同小异:人口流失,土地撂荒,老龄化严重,公共服务难以维持。
“有没有回来的年轻人?”领导问。
沉默。好一会儿,有个年轻点的代表举手:“我是大学毕业回来的,在村里搞电商,卖杂粮。但就我一个人,带动不了全村。而且……找对象都难,村里没有同龄人。”
会议开了三个小时,问题摆了一堆,但解决办法不多。领导最后说,要研究,要规划,要吸引人才回流,要发展特色产业。
散会后,张思源和王有福往外走,碰见那个搞电商的年轻人。他叫陈明,二十八岁,戴副眼镜,文质彬彬。
“张爷爷,王支书。”陈明打招呼。
“小明啊,生意咋样?”王有福问。
“还行,去年卖了二十多万杂粮,但利润薄,运费高。”陈明推了推眼镜,“不过我最近有个想法,想搞认养农业。”
“啥叫认养农业?”张思源不懂。
“就是让城里人认养一块地,我帮他们种,他们可以来体验农耕,收获的粮食归他们。”陈明解释,“这样既能利用荒地,又能增加收入,还能吸引城里人来农村。我用国家的农业补贴给种地的人发工资。”
张思源听得半懂不懂,但觉得有点意思:“那得有人来种啊。”
“雇人种,雇村里人。”陈明说,“老人们种了一辈子地,有经验,干点轻活没问题,何况还有好多农业机械配合,并且还能挣点钱。”
王有福眼睛一亮:“这主意不错!思源叔,你觉得呢?”
张思源想了想:“试试看吧,总比荒着强。”
回家的路上,张思源一直在想陈明的话。认养农业,城里人认养土地,老人帮忙种……这能让年轻人回来吗?恐怕不能。但至少能让地不荒,让老人有点事做,有点收入。
可这还是治标不治本。农村的根本问题不是经济,是人。没有人,一切都是空谈。可怎么才能让年轻人回来呢?
张思源想起孙子张浩。浩子在西安读大学,去年暑假回来住了一周,整天抱着手机,说家里的网不好,没外卖,没电影院,无聊。浩子说,毕业后肯定留在城里,不回农村。
“爷爷,不是我不爱老家,是老家没有我的未来。”浩子的话像针一样扎在张思源心上。
什么是未来?高楼大厦是未来?车水马龙是未来?还是这片黄土、这些窑洞、这些梯田也是未来?
张思源想不通。他只知道,如果所有年轻人都这么想,农村就真的没有未来了。
晚上,张思源睡不着,坐在院里看星星。会宁的星空特别亮,银河像一条银带横跨天际。小时候,爷爷教他认星星:北斗七星、牛郎织女、北极星……爷爷说,人就像星星,各有各的位置。有的星星亮,有的星星暗,但都在天上,谁也离不开谁。
可现在,农村这颗星越来越暗了。
王秀英出来,给他披了件衣裳:“又瞎想啥?进屋睡吧,夜里凉。”
“秀英,你说咱们村,还有救吗?”张思源突然问。
王秀英愣了一下,在他旁边坐下:“咋没救?有人就有救。”
“可没人啊。”
“没人……就想办法找人。”王秀英说得很简单,“年轻人不回来,咱们就找别的法子。陈明那孩子不是搞电商吗?镇上不是要搞旅游吗?慢慢来,总会有办法。”
“咱们这把年纪,等得到吗?”
“等不到也得等。”王秀英握住他的手,“咱们这辈子,什么没经历过?饥荒熬过来了,苦日子熬过来了,现在日子好了,反倒没信心了?”
张思源看着老伴,月光下,她的白发闪着银光,脸上的皱纹像地图上的等高线,记录着他们共同走过的岁月。是啊,什么苦没吃过?一九六零年挨饿,一九七零年修梯田,一九八零年包产到户,一九九零年孩子上学,二零零零年孩子进城……一关一关都过来了。
“你说得对。”张思源握紧老伴的手,“咱们不能灰心。”
夜里,张思源做了个梦。梦见北坪村又热闹起来,地里全是人,麦浪滚滚,炊烟袅袅。孩子们在村里奔跑,笑声像银铃一样清脆。老李还在,赵老汉还在,所有老伙计都在,大家坐在村口的老槐树下,喝茶、抽烟、说古今……
醒来时,天已微亮。王秀英还在睡,呼吸均匀。张思源轻轻起身,走到院里。晨光中的北坪村安静祥和,太阳能路灯已经熄灭,水泥路泛着青灰色的光,东面的田岔梁上,一轮红日正喷薄欲出。
新的一天开始了。
张思源扛起锄头,准备下地。路过村口时,他看见老槐树的枝芽嫩绿嫩绿的,在晨风中轻轻摇曳。这棵槐树有几百年了,见证了北坪村的兴衰。它经历过战乱、饥荒、运动、改革,如今依然挺立。
树犹如此,难道人还不如一棵树吗?
张思源突然有了一个想法。他放下锄头,走到村委会,找到王有福:“有福,咱们在村里办个养老互助社,咋样?”
“养老互助社?”王有福还没完全醒,揉着眼睛。
“对。咱们这些老人,互相照顾,抱团养老。今天我去你家看看,明天你来我家坐坐。谁病了,大家轮流照顾;谁有事,大家帮忙。再请个村医定期来检查,镇上不是有卫生所吗?能不能每周来一次?”张思源越说越激动,“还有,把村里能用的房子收拾出来,搞个活动室,老人有个聚处。再搞个食堂,谁家不想做饭,就去食堂吃,交点钱就行。”
王有福眼睛亮了:“这主意好!可钱从哪来?”
“咱们自己凑点,村里出点,镇上申请点。”张思源说,“先把摊子支起来,慢慢完善。至少,让老人们有个照应,不至于死在炕上没人知道。”
“行!我这就给镇上写申请!”王有福来了精神,“思源叔,你还挺有想法!”
“活人不能让尿憋死。”张思源笑了。“咱们这代人,啥困难没遇到过?没人帮忙,咱们自己帮自己。”
从村委会出来,张思源觉得脚步轻快了许多。他知道,这只是个小开始,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但至少,能让剩下的老人们活得有尊严些,死得也体面些。
至于年轻人回不回来,那是另一个问题。也许,等他们在城里累了、倦了,会想起老家这片黄土;也许,等农村真正发展起来了,他们会愿意回来;也许,他们的孩子,会重新认识这片土地……
这天,张思源走到自家地头。晨光中,他的身影拉得很长,与黄土高原融为一体。远处,荒芜的土地上,蒿草在风中摇摆,像在给人炫耀着鸠占鹊巢的快乐。
他深深吸了口烟,缓缓吐出。烟雾在晨光中袅袅升起,融进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
这是一种尴尬,像一个人在不该出轨的年龄遇见了一位可心的情人,进一步没资格,退一步舍不得。真是进退两难呀!进是希望,退是现实。但只要还有人在这片土地上坚守,希望就不会熄灭。就像那棵老槐树,根扎得深,再旱的年景也能发出嫩绿的新芽。
张思源掐灭烟头,站起身,举起锄头。锄头落下,黄土翻起,新鲜湿润的泥土气息扑面而来。
作者听雨赏蕉,原名张志平,中共党员,会宁县杨集乡人。从事建筑管理、工程预算、造价审计工作三十多年。爱好文学创作,现居兰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