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真卿的“破”与“立”:黄庭坚为何独赞其超逸合度?
宋代书法大家黄庭坚曾有一段掷地有声的评价:颜真卿的书法奇伟秀拔,兼具魏晋隋唐以来的风流气骨,能跳出法度束缚却又暗合规矩;反观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辈,则皆为法度所困。这番话,看似是对几位唐代书法巨擘的臧否,实则道破了中国书法艺术中“法”与“意”的深层博弈。
唐代是书法法度的“黄金时代”。欧阳询的楷书如“净瓶插花”,严谨到每一笔的角度、每一字的间架都似用尺量过,《九成宫》里的横画如刀削斧劈,竖画如孤峰擎天,把“法”的精密推向极致;虞世南的字温润如玉,《孔子庙堂碑》里藏着儒家的中庸之道,笔笔合规却不露锋芒,像一位谦谦君子始终守着进退的分寸;褚遂良则如“美女簪花”,《雁塔圣教序》的线条纤细却暗含筋骨,结体舒展又不失端庄,把初唐的“瘦硬通神”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们是法度的建立者与守护者,让书法从魏晋的“率意”走向“规范”,可也正因如此,后人看他们的字,总觉得多了几分“戴着镣铐跳舞”的拘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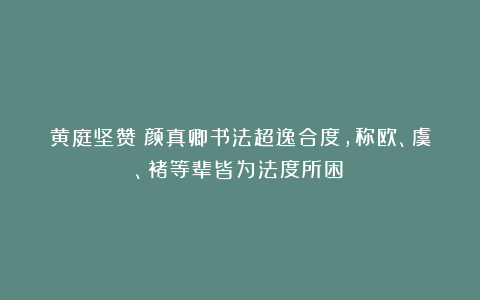
而颜真卿,恰恰是那个既能戴上镣铐,又能跳出自由舞步的人。他早年学褚遂良,也练欧阳询,对法度的熟稔不输任何人。可当安史之乱的铁蹄踏碎盛唐的繁华,当兄长颜杲卿被割舌骂贼、侄子颜季明战死沙场,颜真卿把血泪与悲愤泼洒进笔墨——《祭侄文稿》里,涂改的痕迹是心碎的裂痕,潦草的笔触是怒火的奔涌,那些看似“不合规矩”的枯笔、重墨,却比任何工整的字迹都更有力量。这哪里是在写字?分明是在用生命哭祭。
但颜真卿的伟大,不在于“破法”,而在于“破而后立”。他晚年的《麻姑仙坛记》《颜勤礼碑》,把楷书的“横细竖粗”发展成“屋漏痕”般的沉雄,结体宽博如盛唐气象,看似打破了初唐的精巧,实则暗合“中锋用笔”“力透纸背”的古法。黄庭坚说他“萧然出于绳墨之外,而卒与之合”,正是看到了这种境界:颜真卿不是不懂规矩,而是把规矩内化成了血脉,最终让笔墨跟着心性走,既超逸于法度之上,又从未脱离法度的根基。
这种“超逸合度”,恰恰戳中了书法艺术的核心。欧阳询们的“困于法度”,并非不好,而是他们的“法”太像一座精密的宫殿,后人若只敢在殿内徘徊,便难见墙外的天地;而颜真卿则像在宫殿旁开辟了园林,既保留了殿宇的根基,又让山水云烟自然生长。就像学诗,初唐的格律诗讲究平仄对仗,是“法”;到了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锤炼中藏着“转益多师是汝师”的灵活,才成就“诗圣”的境界。书法亦然,法度是阶梯,却不该是天花板。
黄庭坚自己学书,早年被周越的“俗气”所困,晚年才悟得“沉着痛快”,他太懂“法”与“意”的辩证。在他眼里,颜真卿的价值,正在于证明了:真正的书法大家,从来不是法度的囚徒,而是法度的主人。当笔墨能跟着心性走,当规矩能为情感服务,那字里行间才能既有筋骨的刚,又有血肉的温,这或许就是黄庭坚独赞颜真卿的深层原因——他在颜体中,看到了书法最本真的模样:既守得住传统的根,又放得开生命的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