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的淮海战场,寒雪如絮,覆盖着纵横交错的战壕与僵冷的尸骸。
华东野战军的包围圈像铁箍般越收越紧,国军第13兵团司令部所在的陈官庄已是弹尽粮绝,寒风中夹杂着炸药的焦糊味与伤兵的呻吟,绝望如瘟疫般蔓延。
兵团司令李弥站在临时指挥部的破窗后,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指节因攥紧望远镜而泛白。这位出身云南滇军、历经台儿庄会战的将领,此刻已没有了往日的威风,只剩下求生的本能。
他在犹豫,到底是投降还是为党国尽忠。
此时的13兵团早已溃不成军,下辖的第8军、第9军被分割成数块,连电台都无法与南京取得联系。
李弥很清楚,再守下去只有被俘一条路。
他连夜召集心腹幕僚,在煤油灯忽明忽暗的光线下,敲定了一条孤注一掷的逃亡计划。
“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冒险突围。”
他的声音压得极低,目光扫过面前几位亲信:“张师长,你带一部兵力假意与共军交涉投诚,务必拖延时间,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被点到名的第8军张师长脸上闪过一丝犹豫,却还是咬牙点头,他知道,这是给司令创造生机的唯一办法。
次日黎明,张师长带着几名参谋举着白旗走出阵地,果然如李弥所料,华野前线部队立刻将注意力集中到了谈判上。
趁着这短暂的混乱,李弥在两名护卫的掩护下,钻进了指挥部后的地窖。
地窖里堆放着几具阵亡士兵的尸体,血腥味与霉味混杂在一起,令人作呕。
李弥闭了闭眼,亲手脱下身上笔挺的将官服,换上一套从尸体上扒下来的灰布军装,又用灶灰抹脏了脸,把军帽压得极低,遮住了那双透着精明的眼睛。
“记住,从现在起,我是第8军的普通士兵李二娃。”
他对护卫交代完,便弓着腰,混在一队溃散的士兵中,朝着包围圈的缝隙钻去。
突围的路比想象中更艰难。
华野的巡逻队每隔百米就设一个岗哨,探照灯的光柱在雪地上扫来扫去,像死神的眼睛。
李弥大气不敢出,跟着溃兵趴在雪地里,冰冷的积雪透过单薄的军装渗进肌肤,冻得他牙齿不停打颤。
有一次,一队巡逻兵踩着积雪走来,脚步声越来越近,李弥甚至能听到他们腰间手榴弹碰撞的声响。
他屏住呼吸,将脸埋进雪堆,直到巡逻兵的身影消失在夜色中,才敢抬起头,吐出一口带着冰碴的白气。
就这样昼伏夜出,三天后,他终于逃出了国共交战区,跌跌撞撞地跑到了萧县境内。
萧县虽是国军控制区的边缘,但四处都是散兵游勇与还乡团,局势混乱不堪。
李弥找了个破庙落脚,正盘算着下一步该往何处去,庙门突然被推开,一个穿着破烂棉袄的汉子走了进来。
汉子看到李弥身上的军装,先是警惕地皱眉,随即凑上前来低声问:“兄弟,是从陈官庄逃出来的?”
李弥心中一紧,手悄悄摸向腰间的手枪,却见汉子连忙摆手:“别紧张,我也是被俘后刚被放回来的,我叫汪新安。”
两人攀谈起来,李弥隐瞒了自己的身份,只说自己是个想回家的士兵。
汪新安听后一拍大腿:“巧了!我表哥汪涛在这一带人脉广,不仅能搞到路条,还会化妆的手艺,帮过不少人出城,不过,费用可不低。”
李弥心中大喜,当即表示愿意出钱请汪涛帮忙。
次日,汪新安便带了个面色黝黑、眼神精明的中年汉子来见李弥,正是汪涛。汪涛上下打量了李弥一番,没多问身份,只说:“要去徐州,就得彻底脱胎换骨。费用是一条大黄鱼。”
一条大黄鱼就是一根十两重的金条,李弥咬了咬牙,摸出一根金条递过去。
汪涛取来一套补丁摞补丁的粗布棉衣,又用锅底灰把李弥的脸抹得更黑,还在他的眼角画了几道细纹,让他看起来像个饱经风霜的老农。
“走路要弯腰,说话要粗声粗气,别抬头看人。”
汪涛细细叮嘱着,又拿出一张盖着当地保长印章的路条,上面写着“萧县民夫王大春,前往徐州探亲”。
一切准备妥当后,汪涛亲自护送李弥前往徐州,
一路上遇到盘查,李弥都按照汪涛的嘱咐应答,竟真的蒙混过关。
不料到了徐州城外,两人却傻了眼。
只见城门处戒备森严,解放军战士荷枪实弹地站在岗位上,对进出城的人员逐一盘查,不仅要验路条,还要盘问籍贯、亲属信息,稍有可疑便会被带去审查。
“南下的路走不通了。”汪涛皱着眉说:“解放军刚解放徐州不久,对从北边来的人查得最严,咱们这路条到了跟前肯定露馅。”
李弥的心沉了下去,难道刚逃出包围圈,就要栽在徐州城外?
汪涛思索片刻,突然说:“要不咱们往北走,去潍县?那里还有国军驻守,或许能找到机会去青岛。”
青岛当时是国军在山东的重要据点,有海路通往上海,李弥当即点头同意,两人又掉头向北,朝着潍县方向出发。
从徐州到潍县数百里路程,两人一路上风餐露宿,不敢走大路,只能绕着小路走。
李弥从未吃过这样的苦,脚底磨起了血泡,每走一步都钻心地疼,但他不敢停歇,求生的欲望支撑着他一路前行。
半个月后,两人终于抵达潍县。潍县当时仍在国军控制下,城内秩序相对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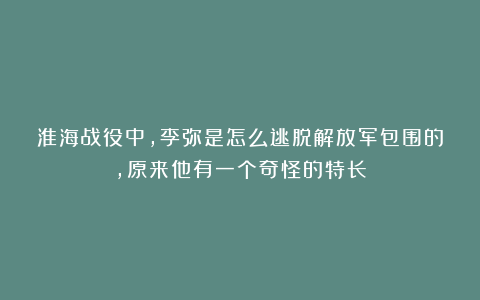
李弥知道,在这里必须找到可靠的人帮忙,他想到了一个旧交,那就是潍县富商李惠之。
李惠之早年在云南做生意时,曾受过李弥的恩惠,两人交情不浅。
李弥找到李惠之的商号,递上一张写着“故人自滇来”的纸条。
李惠之看到纸条后,连忙将李弥请进内院,见到李弥这副模样,先是大惊失色,随即感叹不已:“司令受苦了!”
李惠之连忙让人给李弥准备饭菜和干净衣服,接着说:“青岛有国军驻守,只是从潍县到青岛的路上,解放军的岗哨不少,想过去不容易。”
李惠之思索了几天,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城里有个戏班子,班主王桂合是我的好友,他们几天后要去青岛演出,或许可以让你混在戏班子里过去。”
李惠之接着说:“不过这次不能装农民了,戏班子里的人都是吃开口饭的,你得装个戏班的师傅。”
李惠之给李弥准备了一套体面的绸缎长衫,又请人给李弥修了脸,褪去了脸上的伪装,让他看起来像个温文尔雅的教书先生。
“我跟王桂合说你是我远房亲戚,早年在戏班学过老生,这次跟着戏班子去青岛谋生计。”
李惠之细细交代着,又带着李弥去见王桂合。
王桂合是个五十多岁的戏班班主,脸上带着常年唱戏留下的儒雅气质。
他见李惠之亲自引荐,便爽快地答应下来:“李老板的亲戚就是我的朋友,放心,我会照顾好他的。”
李弥连忙向王桂合道谢,王桂合笑着说:“只是路上要委屈先生了,咱们戏班子出行都是坐马车,条件简陋,而且沿途难免遇到民兵岗哨,还需要先生多配合。”
李弥连忙表示不在意,只要能到青岛,再大的委屈都能受。
出发那天,戏班子一行二十多人坐着三辆马车,浩浩荡荡地从潍县出发。
李弥坐在中间一辆马车上,身边放着一个装着戏服的箱子,王桂合特意给他准备了一把胡琴,让他装作戏班的琴师兼老生师傅。
一路上还算顺利,遇到几次小规模的盘查,王桂合都凭着戏班子的演出证明和自己的口才蒙混过关。
李弥也渐渐放松了警惕,偶尔还会和戏班子的人聊聊天,听他们唱几段戏。
可就在走到昌邑石埠镇时,意外发生了。
只见前方路口设着一个民兵岗哨,四名民兵战士端着枪站在路中间,拦住了马车。
“例行检查,所有人都下车!”一名身材高大的民兵班长喊道。
王桂合心里一紧,连忙下车陪着笑脸:“老总,我们是潍县的戏班子,要去青岛演出,这是演出证明。”
说着递上证明文件。民兵班长接过文件看了看,目光却扫向了马车上的李弥。
李弥连忙弯腰下车,尽量低着头,可他常年身居高位的气质却难以完全掩盖,再加上心里紧张,神色难免有些不自然。
那民兵班长一眼就注意到了他,指着李弥问道:“他是谁?怎么看着面生得很?”
王桂合连忙上前一步,挡在李弥身前:“老总,这是我们戏班的老生师傅,姓王,平时不太爱说话,所以看着腼腆。”
民兵班长皱了皱眉,盯着李弥说:“既然是老生师傅,能不能唱两嗓子让我们听听?也让我们这些庄稼人开开眼。”
这句话像一道惊雷,炸得王桂合脸色发白。
他根本不知道李弥会不会唱戏,刚才只是情急之下编的谎话,这要是唱不出来,肯定会被当成可疑人员审查。
王桂合额头上冒出了冷汗,正想找借口推脱,却见李弥突然抬起头,眼神中竟没了丝毫紧张,反而透着一股镇定。
他整了整长衫,走到路边的一个土坡上,清了清嗓子,开口唱了起来:“昔日有个三大贤,刘关张结义在桃园。弟兄们徐州曾失散,古城相逢又团圆……”
这一段《珠帘寨》唱得字正腔圆,韵味十足,尤其是唱到“关二爷马上呼三弟”时,李弥不自觉地挺直了腰板,眼神中透出几分武将的豪情,隐隐有几分名家风范。
民兵们都看呆了,原本紧绷的神色渐渐放松下来。
那民兵班长也跟着节拍点了点头,等李弥唱完,他笑着鼓起掌来:“好!唱得真好!果然是名师出高徒!”说着挥了挥手:“放行吧!”
马车重新启动,李弥坐在车上,后背已经被冷汗浸湿。
王桂合凑过来,心有余悸地说:“王先生,您可真是深藏不露啊!刚才我都以为要露馅了。”
李弥笑了笑,眼中带着几分志得意满:“年轻时在云南老家,跟着戏班学过几年老生,没想到这爱好今天竟救了我一命。”
在国军将官中,很多人都喜欢听戏,但能够上台唱戏的人却不多,李弥算是其中的一个。
他望着窗外渐渐远去的岗哨,心中感慨万千。从陈官庄的绝境到如今的一线生机,这一路的逃亡,每一步都如在刀尖上行走,而自己多年前的爱好,竟成了最关键的救命稻草。
接下来的路程再无波澜,戏班子顺利抵达青岛。
李弥在王桂合的护送下,找到了国军青岛警备司令部。
当他表明身份后,警备司令又惊又喜,连忙安排他休息,并上报南京。
几天后,一艘军舰从青岛港出发,驶向上海。李弥站在甲板上,
望着茫茫大海,心中百感交集。这场历时一个多月的逃亡,让他亲历了人间冷暖,也让他深刻体会到,在绝境之中,任何一丝技能都可能成为求生的希望。
寒风吹拂着他的脸颊,他知道,这场惊心动魄的逃亡,终将成为他一生中最难忘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