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明代画坛,在这片以工整雅驯为主流的文人山水氛围中,却骤然迸发出一股墨气淋漓、情感奔涌的力量——那便是徐渭。
袁宏道《徐文长传》称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正揭示其艺术与生命之间的张力根源。
一、从生前寂寥到身后扬名,命运跌宕的徐渭
徐渭(1521–1593),字文长,号青藤道士,浙江山阴人。据《明史·文苑传》载,其“六岁受《大学》,日诵千余言”,九岁能文,乡里誉为“神童”。然而科举之路却屡遭挫败,自二十岁至四十一岁间“八试不售”,终身未得举人功名。家道中落、生父早逝、嫡母严厉、妻室早逝等一系列打击,使本就敏感孤高的徐渭“胸中磊块,酒浇不尽”。中年入抗倭总督胡宗宪幕府,代撰《进白鹿表》获嘉靖帝称赏,稍展才略;然胡氏因涉严嵩案倒台,徐渭惧祸及己,精神崩溃,竟至“锥耳折肋,九死辄苏”,更因疑妻不贞而误杀张氏,身陷囹圄七载。牢狱之中,他将绝望淬炼为笔墨,疯癫便成了他对抗世界的最后姿态。
陶望龄《徐文长传》记其狱中“益愤激无聊,所有尽斥卖,得钱辄沽酒”,而“作为诗画,往往深致悲郁”。
二、以狂草入画、以浓墨泼画,“泼墨大写意”的徐渭
徐渭最重要的艺术贡献,在于开创并完善了泼墨大写意花鸟画风。其画学思想深受王阳明心学影响,主张“心外无物”“画为心印”。他将草书的笔势、节奏与墨法融入绘画:葡萄藤如惊蛇走虺,荷叶似泼浪崩云;石榴、南瓜等皆以饱含水墨的笔触一次写成,运用破墨、积墨诸法,营造出墨韵氤氲、气势磅礴的视觉张力。传统花鸟讲究形似与气韵的平衡,徐渭却将疯癫注入笔端,以“不求形似求神似”的狂放,让水墨挣脱摹写自然的桎梏,成为抒发内心郁愤的直接载体——那些扭曲的枝蔓、淋漓的墨点,都是他灵魂挣扎的痕迹。
故宫博物院所藏《墨葡萄图》轴堪称其代表作:墨渖飞动,藤蔓纠缠,题诗更直抒胸臆: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
诗画相映,既是物象写照,更是自我生命的投射。徐渭曾自评“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然后世却将其画奉为“青藤画派”源头,八大山人、石涛、扬州八怪乃至吴昌硕、齐白石等皆深受其影响。郑板桥曾刻“青藤门下牛马走”一印,以示敬仰。
清代戴熙《习苦斋画絮》评:“青藤白阳,一扫秾丽旧习,真写意开山手。”
三、人格反叛和美学追求,又狂又癫的徐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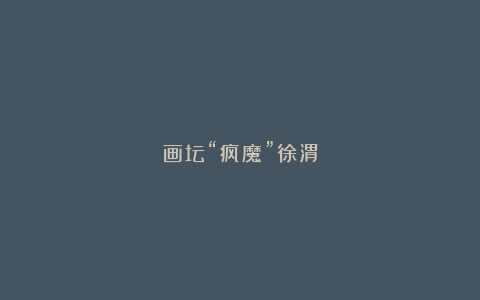
徐渭的疯癫,本质是人格的极致率真与美学的彻底叛逆。他拒斥温柔敦厚的士人形象,亦不屑于精工细丽的职业画风。其《杂花图卷》(南京博物院藏)以十余种花卉草木连缀成卷,牡丹以破笔写其秾艳背后的衰飒,菊石以焦墨凸显其孤高倔强,处处彰显“法自我立”的创作态度。
袁宏道在《徐文长传》中感叹:“先生数奇不已,遂为狂疾;狂疾不已,遂为囹圄。古今文人牢骚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
狂疾与囹圄构成了徐渭生命经验的两极:愈受压抑,愈要爆发;愈遭排斥,愈要张扬。由此,他将传统文人画的书卷气推向血脉偾张的情感强度,使写意不再仅是物象的提炼,更是主体精神的彻底释放。
结语
徐渭生前寂寥,身后却声名日隆。八大山人承其冷逸,石涛取其豪纵;齐白石曾叹“恨不生三百年前,为青藤磨墨理纸”。美术史家陈传席在《中国绘画美学史》中称其为“大写意绘画的真正奠基者”,认为“后世凡作大写意者,鲜有不染指青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