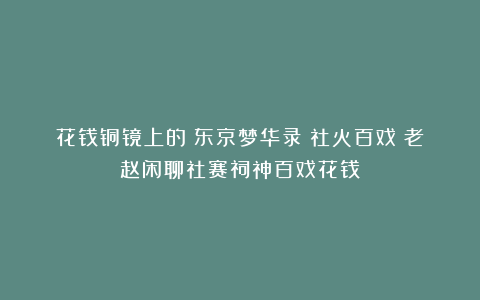|
花钱铜镜上的《东京梦华录》社火百戏
老赵闲聊神怪中的二郎系列五一
之前我们聊到,二郎神从唐代尚未成型,到两宋显赫一时,五代是其转型的惊人一跳,并且提炼了二郎神作为蜀神之所以能够坐大,唐宋时期神灵的地方化是一个十分要害的因素。在此过程中,毗沙门天王非常可能影响过二郎神的发展轨迹。之后,专题从民俗视野聚焦了二郎神的川主现象。以及社火的文本整理,参见:
今天我们继续沿着社火的路径往前探索艺术图像,我们就从一枚奇特的花钱说起:
1、驯狮豹花钱与诸军百戏
在宋代花钱与铜镜中,存在一个有意思的品类。其中存在驯狮豹、舞旗帜等要素,具有综合形态,那么,它到底是指的什么内容与风俗呢?见下图所示:
滴水泉藏品
第1面,穿上主尊,穿下狮子,左右两个侍卫手持檛或骨朵,在驯服狮子。就跟文殊菩萨的狮奴、唐代壁画中驯豹奴类似。见下图所示:
第2面,穿下虎豹,右侧是胡人以鞭驯服猛虎之类的猛兽,他手持的长形物件,呈现斑节的特点,要么是抓住了老虎的尾巴,要么是手持节鞭之类的打击器具。左侧为童子持旗帜,在招呼来者。见下图所示:
狮虎豹同存的艺术图像不多,可以参照一下以下稷山青龙寺水陆壁画中,狮虎同在的情形,见下图所示:
其实,参照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第七卷《驾登宝津楼诸军呈百戏》中诸军百戏的陈述,对本花前的内涵,就似乎有了有趣的解读路径。
这一节是讲三月一日这一天,在金明池和琼林苑开展的活动。金明池在顺天门街北,有面北临水殿,皇帝御驾先幸临水殿宴请群臣。席间观看木偶表演、水上表演、秋千表演。之后驾幸琼林苑、驾幸宝津楼宴殿,宝津楼之南有宴殿。驾临幸,嫔御车马在此。皇上在宝津楼观看百戏。所谓诸军百戏,则可以比照军队的总郑文工团表演,为了标明类别,我特作了割断分段处理,原文是连贯一起的:
驾登宝津楼,诸军百戏,呈于楼下。先列鼓子十数辈,一人摇双鼓子,近前进致语,多唱’青春三月蓦山溪’也。唱讫,鼓笛举一红巾者弄大旗,次狮豹入场,坐作进退,奋迅举止毕。
次一红巾者,手执两白旗子,跳跃旋风而舞,谓之《扑旗子》。
及上竿、打筋斗之类讫,乐部举动,琴家弄令,有花妆轻健军士百余,前列旗帜,各执雉尾、蛮牌、木刀,初成行列;拜舞互变’开门夺桥’等阵,然后列成’偃月阵’。乐部复动’蛮牌令’,数内两人出阵对舞,如击刺之状——一人作奋击之势,一人作僵仆。
出场凡五七对,或以枪对牌、剑对牌之类。忽作一声如霹雳,谓之’爆杖’,则蛮牌者引退。
烟火大起,有假面披发、口吐狼牙烟火如鬼神状者上场,着青帖金花短后之衣,帖金皂裤,跣足,携大铜锣随身,步舞而进退,谓之《抱锣》。绕场数遭,或就地放烟火之类。
又一声’爆杖’,乐部动《拜新月》慢曲,有命涂青碌,戴面具金睛,饰以豹皮锦绣看带之类,谓之《硬鬼》——或执刀斧,或执杵棒之类,作脚步蘸立,为驱捉视听之状。
这是一次御驾登宝津楼观看文工团演出的特别场景。皇上亲临,文艺工作者自然第一得格外卖力,第二,得把所有的精彩表演菜单一并呈现。在这次表演中,开场的清音完毕之后,第一个出场的,就是“鼓笛举一红巾者弄大旗,次狮豹入场“,可见,这是非常难得的出场戏,其目的就是要抓住皇上的眼球,让他老人家眼睛一亮,精神一振。
而下图花钱中,两个画面的穿下,正是一个狮,一个豹,两面合并观察,正是”狮豹入场,坐作进退,奋迅举止毕。“之生动描述。
也就是说,皇上看表演的第一道菜,就是上的马戏团的猛兽表演,驯兽师对于狮豹进行训练表演,让它坐就坐,让它起就起,让它进就进,让它退就退,一会儿作出威猛的姿势,一会儿又静止得像个猫咪。皇上看了,一定是龙颜大悦。
在这次表演中,”鼓笛举一红巾者弄大旗,次狮豹入场,坐作进退,奋迅举止毕。“是说,狮豹入场之前,就有一个举红巾者开始弄大旗,然后才是狮豹入场,而狮豹表演一结束,又来了一个着红巾者,”手执两白旗子,跳跃旋风而舞,谓之《扑旗子》“。
也就是说,这是三个环节,第一,持旗召狮豹等表演者入场,第二,狮豹入场表演,第三,手持两白旗的扑旗子表演环节。
狮豹入场,本身是一种非常少见的演出要素,狮豹表演是为了献演于尊者,《东京梦华录》中所描述的观赏尊者,是北宋皇帝。而在本花钱中,也有对应的观赏尊者的存在。可见两者结构上的完全合拍对榫。
可见,本花钱中的狮豹要素,其实也就契合着《东京梦华录》中所描述的狮豹入场的表演状态。
由于本钱上在豹子画面左侧正好有一个举旗之童子形象。本身也没有持两面旗的状态,所以花钱上的举旗童子其实大体就是在狮豹入场之前,举旗召唤狮豹入场的“弄大旗”者。
而《东京梦华录》所描述的狮豹入场表演随后的表演环节中,“烟火大起,有假面披发、口吐狼牙烟火如鬼神状者上场,着青帖金花短后之衣,帖金皂裤,跣足,携大铜锣随身,步舞而进退,谓之《抱锣》。绕场数遭,或就地放烟火之类”;
”又一声’爆杖’,乐部动《拜新月》慢曲,有命涂青碌,戴面具金睛,饰以豹皮锦绣看带之类,谓之《硬鬼》——或执刀斧,或执杵棒之类,作脚步蘸立,为驱捉视听之状“。
而在下图花钱画面中,穿左右两人,也正是披发,执杵棒,作脚步蘸立,为驱捉视听之状,由于钱币空间有限,估计很多因素都综合揉杂了,下图左右两人,不仅解决了抱锣表演的披发问题,也解决了硬鬼环节的执棒站立问题,还兼顾了驯兽的问题。因为由于狮豹分属两个空间,在艺术表现中,一面既然是胡人驯兽,另一面则无法继续重复,有限的空间也不允许如此奢侈浪费。从艺术效果看也不能简单重叠。
同样,下图中不仅有狮豹入场前的举旗召唤要素,也有狮豹入场的正式呈现,右边的戴胡帽的胡人,一手拉着虎尾巴在承担驯兽的功能,另一手还举着宝贝,似乎在兼顾着回回献宝的其他戏份。
吴自牧撰《梦粱录》中百戏社火描述。吴自牧,仅知约宋度宗(1240年—1274年)年间人,生平亦无考。《梦粱录》为追忆南宋临安盛况。卷一“元宵”中写道:
“今杭城元宵之际,州府设上元醮,诸狱修净狱道场,官放公私僦屋钱三日,以宽民力。舞队自去岁冬至日,便呈行放……此岁岁州府科额支行,遮几体朝廷与民同乐之意。姑以舞队言之,如清音、遏云、掉刀、鲍老、胡女、刘衮、乔三教、乔迎酒、乔亲事、焦槌架儿、仕女、杵歌、诸国朝、竹马儿、村田乐、神鬼、十斋郎各社,不下数十;更有乔宅眷、旱龙船、踢灯、驼象社。官巷口、苏家巷二十四家傀儡,衣装鲜丽,细旦戴花朵披肩、珠翠冠儿,腰肢纤袅,宛若妇人。
南宋周密《武林旧事》所述“舞队”事象中也有”诸国献宝“、”六国朝“、”四国朝“等名目。
《水浒传》中在宋江招安之后,皇上亲驾与民同乐庆贺演出的时候,也有很多百戏歌舞。其中描述到:
须臾间,八个排长簇拥着四个金翠美人,歌舞双行,吹弹并举。歌的是《朝天子》《贺圣朝》《感皇恩》《殿前欢》,治世之音;舞的是《醉回回》《活观音》《柳青娘》《鲍老儿》。
可见,胡人形象要素,在百戏中是有很多戏份的,既可以作为诸国献宝的主角,也可以是醉回回的猎奇欣赏,假设是醉回回主题,那么,本花钱上的回回,左手向上抱着的,也许就是酒葫芦了。见下图所示:
明代《上元灯彩图》是展现民间元宵习俗的作品画作。画作要描绘了明朝中晚期南京地区元宵节期间的街市景致,画中人们逛街赏花灯、年轻女性结伴赏灯。等等,其中就有胡人舞狮的花灯要素,见下图所示:
胡人舞狮,不仅是一种域外风情,还是万国来朝的政治正确,所以在各种场合十分凑趣,比比皆是。下图中宋代陶模中的胡人戏狮,狮子背上还有一个舞者。
明《宪宗元宵行乐图》局部
胡人驯狮花钱 胡坚供图
3、狮豹花钱主尊是谁?
花钱的两面谁是正面,谁更重要,谁更呈现主题,这个问题可以由铜镜来回答,因为花钱有两面图形可呈现,而铜镜只有一面可呈现画面。
网络资料
由于铜镜中目前只发现这一个画面入境,而缺少花钱上的另一个画面的存在,所以,我们大致可以认同,铜镜上所呈现的画面,在花钱上属于正面,属于更主题,更核心的表达。
现在,画面左右以及下方的要素似乎都可以得到合理推导,那么上方的主尊到底是什么人物呢?同样,铜镜为什么在两个画面中只选取这一画面,很大可能也是因为有一个主尊的存在。他可能就是狮豹、扑旗、硬鬼、献宝这些表演的观赏者,供奉的对象主尊。
这个穿上主尊呈现一个游戏坐姿,也就是大家俗称的二郎腿。身子两侧为云纹装饰。头戴盔身着甲。按照供奉对象的逻辑,应该是一个神王。
由这个坐姿,与布局的结构,让我们联想到了二郎神花钱中非常重要的七圣刀系列。七圣刀题材目前所见有两种,其一如下图所示:
胡坚藏品
二郎花钱 田丰藏品 老赵旧藏
在花钱中,还有一枚二郎神七圣刀主题花钱,我们姑且命名它为七圣刀第二品。上述此品暂时命名为七圣刀第一品,在第二品这枚花钱上,由于设计的关系,人物的动作更加饱满。完全可以更加鲜明充分地去理解第一品七圣刀花钱的要素佐证。而且,也具有主尊端坐要素。见下图所示:
二郎七圣刀花钱 陆昕藏品
从狮豹花钱的布局与七圣刀花钱的布局的类似来看,主尊都是在观赏表演,也就是,画面主题都在用精彩的表演供奉主尊神灵,也就是迎神娱神。
他们的区别,无非是一个是狮豹扑旗硬鬼回回在呈现戏份,而另一个则是七圣刀组合在呈现戏份。而两枚钱的主尊都是戎装而游戏坐姿。手中也同样持有棍状类物。彼此结构类似。
4、狮豹花钱主尊会是二郎神吗?
既然狮豹花钱主尊与七圣刀花钱主尊,在接受供奉的意趣,迎神表演的主题,都是二郎腿的相同坐姿,手中都持长物等要素上呈现某种趋同性,那么,狮豹花钱上的主尊有没有可能就是二郎神呢?
我们来进行一番有趣的探索。除了上述的目力可见的艺术图像要素的类似,还有哪些可供参照的要素呢?
文章开头我们阐述了狮豹扑旗的文本援引自《东京梦华录》第七卷《驾登宝津楼诸军呈百戏》中诸军百戏的陈述,巧了。上述引文之后,其实还有下半段陈述,也就是皇上御驾亲临所观赏的节目还没有结束。后面有什么节目呢?
又’爆仗’一声,有假面长髯、展裹绿袍靴简如钟馗像者,傍一人以小锣相招和舞步,谓之《舞判》。
继有二三痩瘠以粉涂身、金睛白面如骷髅状,手执软仗,各作魁谐趋跄,举止若排戏,谓之《哑杂剧》。
又’爆仗’响,有烟火就涌出,人面不相睹;烟中有七人,皆披发文身,着青纱短后之衣、锦绣围肚看带;内一人金花小帽、执白旗,余皆头巾、执真刀,互相格斗击刺,作破面剖心之势,谓之《七圣刀》。
忽又’爆仗’响,又复烟火,出散处以青幕围绕,列数十辈,皆假面异服,如祠庙中神鬼塑像,谓之《歇帐》,
又’爆仗’响,卷退。次有一击小铜锣,引百余人,或巾裹,或双髻,各着杂色半臂,围肚看带,以黄白粉涂其面,谓之《抹跄》。
由此可见,在皇上御驾亲临所观赏的精彩表演中,开头是狮豹扑旗,后来出现的是七圣刀,也就是说,狮豹表演,七圣刀都是供尊者欣赏的精彩表演系统序列的一部分。
皇上既然能同时观赏狮豹表演与七圣刀表演,那么,作为更为尊贵的神灵,从逻辑上,也理所当然可以同样欣赏狮豹表演与七圣刀表演。
况且,花钱上已经存在了七圣刀表演供奉二郎神的画面,现在假设再次出现狮豹表演供奉二郎神,从逻辑上也同样是可能的。
其实,皇上亲临观看的高级表演,也是从民间风俗中提炼而就,并非无源之水,狮豹演出在宋代祭赛风俗中,也是一个经常闪现的要素。
宋代,社日大致即是农村的“狂欢节”,不仅有鼓乐祭神、占卜祈农、社聚宴饮等活动,还有社舞社火百戏表演等大众喜闻乐见可以参与的快活条目,杨万里《观社》中就曾写道:“作社朝祠有足观,山农祈福更迎 年。忽然箫鼓来何处?走煞儿童最可怜!虎头豹面时自顾,野讴市舞各争妍“。
这是说,在南宋社赛风俗中,存在儿童戴着狮子豹子的面具参与的状况。
元中书左丞吕思成在至正十三年(1353)为其家乡平定州(今山西平定县)所作的碑文《灵瞻王庙记》中给我们提供了有关赛社活动的十分有价值的信息:
四月四日献享庙上。前期一日迎神,六村之众具仪仗引导,幢幡宝盖,旌旗、金鼓与散乐、社火层见叠出,名曰“起神”。明日牲牢、酒醴、香纸既丰且腆,则吹箫击鼓,优伶奏技。而各社各有社火,或骑或步,或为仙佛,或为鬼神,鱼龙虎豹,喧呼歌叫,如蜡祭之狂。日晡复起,名曰下神。神至之处,日夕供祀惟谨。岁以为常。
在这里,吕思成所阐述的社火,是与金鼓、散乐并称的,所以社火中也许就并不包括金鼓、散乐。而社火的形态,或骑或步,或为仙佛,或为鬼神,鱼龙虎豹,喧呼歌叫,如蜡祭之狂,充满浓郁的装饰气息,装扮奇幻,而声音喧闹,而且在第一天的演出中,以社火迎神,称为起神,而在第二天的演出中,神灵下降,称为下神。所以,社火是与祭赛神灵,是与神降,神巡相关的要素。而且其中的表演就有狮豹。
同样,在明代嘉靖《池州府志·风土篇》“逐疫”条中,我们可以发现其中包含了与元宵舞队表演事项男女竹马、狮豹相类似的事项: “凡乡落自十三至十六夜,同社者轮迎社神于家,或踹竹马,或肖狮象,或滚球灯,妆神象,扮杂戏,震以锣鼓,和以喧号……“
南宋时期农村社祭活动中的虎头豹面的面具形态,元代社祭赛神风俗中的社火狮豹表演,明代池州地区的元宵逐疫活动中的模拟狮象,都在为《东京梦华录》中北宋皇家观赏的狮豹表演,做着更为深入的民间、社会风俗性的、乃至源流性的诠释。更不去说更为古早的傩仪中的模拟虎豹熊罴之类的动物表演传统。
可见,北宋皇家观赏的狮豹表演,源头乃是宋代社会赛社祭神风俗中的迎神表演。元代山西平定祭的是灵瞻王,而狮豹表演就是用于第一天的迎神环节中。
可见,狮豹表演在北宋京城,被选择而被修饰剥离了风俗的特定土壤,而被装扮得更加华丽,成为一种特定的供都市消费的特定演出,而被皇上也笑纳了。比如,开头我们所引述的北宋东京为皇上表演的诸国献宝、扑旗、装鬼、抱锣以及狮豹,也赫然被记载在了《武林旧事》所述“舞队”事象中,舞队表演,都是被剥离了原先生存的风俗土壤,而可以为任何节庆进行配套的专业商业演出。
该书记述了“舞队”七十余种,计有:
大小全棚傀儡、查查鬼、李大口、贺丰年、长瓠脸、兔吉、吃遂、大憨、粗旦、麻婆子、快活三郎、黄金杏、瞎判官、快活三娘、沈承务、一脸膜、猫儿相公、洞公嘴、细旦、河东子、黑遂、王铁儿、交椅、夹棒、屏风、男女竹马、男女杵歌、大小斫刀鲍老、交衮鲍老、子弟清音、女童清音、诸国献宝、穿心国入贡、孙武子教女兵、六国朝、四国朝、遏云社、绯绿社、胡女、凤阮嵇琴、扑蝴蝶、回阳丹、火药、瓦盆鼓、焦槌架儿、乔三教、乔迎酒、乔亲事、乔乐神、乔捉蛇、乔学堂、乔宅眷、乔像生、乔师娘、独自乔、地仙、旱划船、教象、装态、村田乐、鼓板、踏跷、扑旗、抱锣、装鬼、狮豹、蛮牌、十斋郎、耍和尚、刘衮、散钱行、货郎、打娇惜等等。
可见,狮豹、扑旗、诸国献宝的表演,从艺术表演门类中归属舞队,而在宽泛的文艺类别中可以统称为百戏。或者两者之间未必一定存在严格的界限。
它其实跟社火的含义一样,既根植于社祭娱神、新年逐疫驱祟的傩仪等风俗活动,又逐渐进入都市之后,成为经过了精心修饰的、可以剥离原始风俗对应关系的、为市井乃至达官贵人消费的、可以根据文化需求调整演出格调与配菜成分的文化表演。
而在其源头,在其还在风俗层面的存在中,狮豹表演乃至七圣刀表演就是一种迎神的娱神表演。他可以去迎元代社赛中的西瞻王,也自然可以去迎宋代社赛中频频可见的二郎神。
我们再次引用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对二郎神生日祭赛时的社火描述:
“(六月)二十四日,州西灌口二郎生日,最为繁盛。庙在万胜门外一里许,敕赐神保观。二十三日,御前献送后苑作与书艺局等处制造戏玩。如球杖、弹弓、弋射之具,鞍辔、衔勒、樊笼之类,悉皆精巧。作乐迎引至庙,于殿前露台上设乐棚,教坊钧容直作乐,更互杂剧舞旋。太官局供食,连夜二十四盏,各有节次。至二十四日,夜五更争烧头炉香,有在庙止宿,夜半起以争先者。天晓,诸司及诸行百姓献送甚多。其社火呈于露台之上,所献之物,动以万数。自早呈拽百戏,如上竿、跃弄、跳索、相扑、皷板、小唱、斗鸡、说诨话、杂扮、商谜、合笙、乔筋骨、乔相扑、浪子、杂剧、叫果子、学像生、倬刀装鬼、砑皷牌棒、道术之类,色色有之,至暮呈拽不尽。殿前两幡竿,高数十丈。左则京城所,右则修内司,搭材分占上竿呈艺解,或竿尖立横不列于其上。装神鬼、吐烟火、甚危险骇人,至夕而罢。”
上述的二郎神祭赛表演,是都市的,皇家的,而二郎神祭赛的民间标本,却精彩地存在在至今的青海地区。有意思的是,狮豹表演还与二郎神的祭赛风俗有关。
在青海也存在一种名叫“於菟”的驱邪求祥仪式,每年农历十一月初八、十一、十四、十九日举行献给二郎神、玛卿神、大日加神的“邦”会活动,活动于晚间举行。议程包括:请神、祭神、赞神、拜神等敬神仪式,对答、对唱、卜卦、舞蹈、求子等娱人娱神神仪式。
农历十一月二十日,被认为是最不好的日子,年都乎城内外村民清晨要彻底打扫院子庭屋,并将垃圾清扫出门。活动当天,由7名於菟,上身裸露,下身裤腿卷到大腿根部,由法师拉瓦用煨桑灰涂抹全身,并在身上用墨汁画上虎豹斑纹。用白纸条扎起头发,向上竖立,两手各持一根两米半长的松柏枝,枝顶以刀劈缝,大“於菟”手持棍上插以“库鲁”,小“於菟”棍上插以“克特日”,用白纸条捆绑,腰间系上红腰带,并佩藏刀。在拉瓦单皮鼓的伴奏下,装扮好的於菟在二郎神庙前跳吸腿垫步舞。沿路作戏,家中有病人的人家会让於菟从俯卧在地的病人身上跳过,以驱除或减轻病人的疾病痛苦。於菟将收集到的、预示不祥的看子等物品丢入山下河流之中,用水冲走,以示驱逐邪恶和疾疫。同时於菟还需在河边自己或相互泼水清洗,寒冬时节裸体清洗,不仅与西亚风俗相仿,也与泼胡乞寒游戏中的”裸露形体,浇灌衢路、裸体杂足,挥水投泥“类似。关键是,其中也供奉二郎神,这与七圣刀活动的裸体作法与祆俗舞蹈仪式存在某种要素层面的相似性。而於菟,楚国的时候就有“老虎”的意思,可见屈原作品。
青海省博物馆非遗厅资料 乐艺会资料
可见,既然狮豹表演与七圣刀表演,都是祭神风俗供神的表演,花钱上保存了七圣刀表演供奉二郎神的实况,非遗中保存了狮豹表演供奉二郎神的遗存。而七圣刀表演与狮豹表演又同时被记录在北宋笔记中,作为供奉皇上观赏的表演要素。
可见,无论是花钱上,还是文献中,还是风俗遗存中,圣上尊者、神灵尊者比如二郎神,都可以享受狮豹表演与七圣刀表演,都事实上在享受过狮豹表演,则二郎神花钱上出现狮豹表演要素,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狮豹花钱上的方穿,在铜镜上演化为了一个四边装饰的方形状,在刻意的装饰之后,似乎在表达他的某种需要观者注意的特殊型,它也许就是《东京梦华录》二郎神生日祭赛社火活动的表演场地——露台的显示(其社火呈于露台之上,所献之物,动以万数)。当然,也可能是金泰和丁卯(南宋开禧三年1207)山西平定治西镇《昭惠灵显王感应碑记》二郎神社赛仪式中的坛仪的那个坛。(坛所群情精神,灌灌忻然…..神归庙所,顷刻云叇)。
网络资料
我们在上述阐述中阐明,二郎神在逻辑上可以享受狮豹表演,在风俗事实上也享受过狮豹表演,在艺术布局上狮豹花钱与二郎神七圣刀花钱惊人相似,但是,狮豹花钱上的主尊到底是不是二郎神,依旧缺乏最关键的落实,问题的最后一环,就纠缠在了主尊的装扮上。
如果主尊是二郎神的招牌装扮,比如头戴三山帽,身着黄衫服,手持弓箭,黑犬跟随,那么,就毫无争议了。现在这个主尊,戴头盔,项顿翻卷,全身类似全副戎装。这个二郎似乎就不那么典型。
当然,你也可以说,二郎神在南宋《墨子道宝》中形象,以及自此之后在《搜山图卷》中的形象,也屡次出现盔甲戎装之形象,而且,所有的戴盔甲的二郎神形象均是游戏坐姿,手持宝剑。与狮豹花钱铜镜上的主尊基本一致。
明代郑重《搜山图》(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中的天王式金盔二郎神。如下图所示:
以及云南省博物馆藏明代本《搜山图》。本长卷绢本设色,纵44.3厘米,横606厘米,无款,无收藏印记,题跋。定为明代中晚期摹本。如下图所示:
网络资料
至于狮豹花钱中主尊所持之物,我们也可以从宋代将钱中,同样游戏坐姿的大将手中的持物宝剑形态得到参照佐证,因为其中有的宝剑斜持,跟搜山图中的二郎神一样,比较明显,有的则平持,类似一根短棍,而与狮豹花钱之戎装神王类似:
前一阵,花钱收藏圈出现了一枚珍贵罕见特殊造型的神怪花钱,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不久,又出现了一枚同样内容造型的神怪花钱,真是要么无踪迹,要么扎堆来,可见他们也是有灵性的。
本花钱正面上为主尊,游戏坐姿,坐于山石之上,穿左人物手持棹刀,也就是二郎神著名的三尖两刃刀,右侧人物手持旗帜。穿下一人在进行似乎颇有难度之表演。显得吃力而卖力。
明刻本 武经总要 掉刀
大家要知道,棹刀不仅是民间传说中二郎神的专职兵器,也是宋代蜀地在二郎神祭赛中模拟神兵而操持的特定道具,《宋会要辑稿·刑法二》载:“大中祥符五年七月十日,知益州李士衡言永康军村民社赛,用棹刀为戏,望行禁止”。所以凡是迎二郎神的祭赛社会表演,其中必得有棹刀为戏。
在花钱的另一面,穿上,左右为三个基本平级的人物,分别持游戏坐姿坐于山石之上,穿左人物手持短刀,穿上穿右人物伸手比划。穿上人物头饰不明,左右之人则呈现浑裹状态,与正面的左右下侍从杂耍人物类似。而与花钱正面主尊不同。本钱主尊细看,与狮豹花钱主尊一样,都是头戴头盔,项顿翻卷。
奇妙的是,在《东京梦华录》中皇上御驾观赏的表演中,除了开头的狮豹入场,中间的七圣刀表演,其实还有后续表演环节,我们继续往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