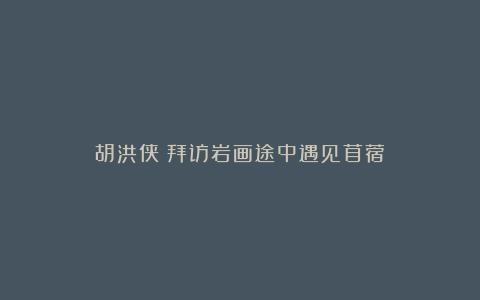|
1
在通往贺兰山岩画的路上,我和导览范师傅聊天,聊田野里的玉米,聊进口的大型收割机,聊西梅、红枣与酸枣。“苜蓿呢?”我问,“你们这儿种不种苜蓿?”
“种着哩。”他说,“春天上长第一茬,叶子嫩着的时候人可以吃……”
“苜蓿芽,我吃过。”
“……开花的时候好看着呢。”
“对,紫色的花。”
我们俩一来一往聊苜蓿,像回忆一个共同认识的老朋友。“哎哎哎,”他忽然指着左侧的农田说,“那里就种着苜蓿,绿绿的那一片就是。”
我看过去,但什么也没看清,汽车已驶离那片绿。“能不能停车?”我急忙说,“我要到苜蓿地看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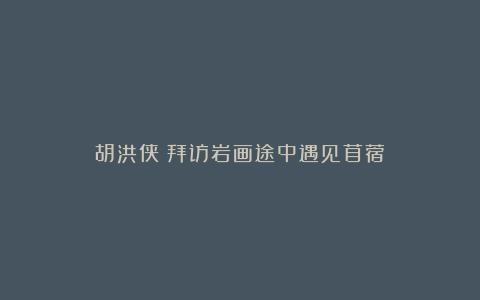
2
我终于又站在了苜蓿地里。
是早晨九点多,天仍是层层叠叠地阴着,没有阳光。前天抵埠,接我们的李师傅说,他们这里难得下雨,天天阳光好得很,谁知第二天就阴雨绵绵。这第三天的上午,笼罩着苜蓿地的,依然是灰蒙蒙的天空。
可这有什么关系!我一脚就迈进了苜蓿地。走了几步才意识到,苜蓿叶子上崭新的露珠,已经把鞋打湿了。
得有多少年,鞋子没有给露珠打湿过了?
这时地头上传来喊声:“紫色的苜蓿花!”我也弯腰在周围一片绿色中细细寻找,手中很快有了一小把挂着紫花的苜蓿。眼下还不是苜蓿花盛开的季节,但我脑中立刻补足了大片紫花怒放的画面。那是四五十年前的画面了,但仍然是彩色的:盛夏,干燥的阳光,茂密的苜蓿地,远远望过去,是紫色的烟雾;走进细看,还有蜜蜂,有蝴蝶,有踩到一脚松土引发的心颤……。
至少有四十年没有双脚踩进苜蓿地了。小时候,村东北那几块苜蓿地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们看着苜蓿发芽,看着紫花盛开,看着晒干的苜蓿运进牲口棚。
我最喜欢的其实不是紫色的苜蓿花,而是嫩绿的苜蓿芽。1970年代,春天里粮食和蔬菜青黄不接时,苜蓿芽会招来人们贪吃的目光。知道苜蓿地是生产队的集体财产,而苜蓿又是喂牲口的饲料,可是,和榆钱、马勺子菜(马齿苋)和苦菜一样,苜蓿芽也是好吃的东西。偷偷地摘一把,回家让母亲将之洗净,拌上一点棒子面(玉米面),在锅里蒸熟,撒上盐,淋上蒜汁,那就是上好的美食了。村里管这种饭食叫“Na gou”,我至今说不准这两个字该怎么写。
今天站在银川郊外的苜蓿地里,心里仍有要偷摘一把苜蓿芽的念头闪过。
范师傅说,现在苜蓿种植已经农场化、机械化了。收割、晒干之后,苜蓿干草会打成一吨一个的大包,卖给养牛场做饲料,产牛奶。
苜蓿不是华夏本土农作物,其传入中国的历史,是一段绵延两千多年的中外农业文化交流史。史书上说,苜蓿原产于伊朗高原(波斯)、外高加索、中亚地区(如大宛,即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等地,约公元前113年-前104年间经由后世所称的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且是与大宛马同时引入。
更明确的说法,应该是汉武帝喜欢西域大宛名马,而大宛马喜食苜蓿,于是,使者们自大宛国等地将苜蓿种子带回,先是种植在长安附近的离宫别馆旁边,以满足宫廷苑囿中饲养来自西域“天马”之需,后来,苜蓿由宫廷走向民间,特别是在明清时期,为保障军事需求(如军马饲料),卫所屯田中广泛种植苜蓿,这就使得苜蓿渐渐传播到边疆地区与漕运沿线等地。
我们那个村子就在漕运沿线。我们那个村子还是明永乐年间新增的“军屯”,属德州左卫辖制。如此说来,我们村东北的苜蓿地,当年乃是一“军事设施”,专为战马配备。这其中或有更大的故事正等待讲述。
今天的一路之上,贺兰山岩画固然让我心旷神怡又心存疑团,即这看起来并不震惊人世的牛马饲料苜蓿,也在我这里新增不少疑问。今日和岩画和苜蓿的相遇何等偶然,而其中待解的谜团却俯拾皆是。明乎此,对未来悲观也罢乐观也罢,又有多重要。不如就在偶然中坦然面对岩石上或田野里的谜面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