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珍贵藏品中,藏着两件跨越三百年的康熙瓷魂 —— 郎窑红釉穿带直口瓶与郎窑绿釉水丞。
前者红釉浓艳如霞,釉面莹润透亮,瓶身刻有乾隆御题诗,字里行间满是后世帝王的推崇,如今常展于展柜之中,供观者驻足品鉴;后者绿釉翠嫩似竹,满身开细碎冰裂纹,酱色口沿暗藏时代印记,虽存世稀少,其收藏于故宫的身份亦确凿无疑。
这一红一绿两件珍品,皆出自康熙朝著名督陶官郎廷极主持的 “郎窑”,它们的诞生,既有宫廷审美驱动的必然,也藏着窑火淬炼的偶然,共同谱写了清代颜色釉瓷的巅峰篇章。
郎窑红:奉旨仿古中的 “有意突破”
康熙一朝,制瓷业迎来复兴高峰,帝王的审美偏好往往主导着御窑厂的烧造方向。康熙皇帝对明代永宣时期的宝石红釉情有独钟,那款 “色如宝石、光莹剔透” 的红釉瓷,因烧造技艺复杂早已失传。
为复刻这份古瓷之美,康熙下旨命时任江西巡抚兼督陶官的郎廷极主持仿烧,这既是宫廷的明确需求,也是郎窑的核心使命。
郎廷极本身酷爱古陶瓷,对宣德红釉的工艺特征颇有研究。他召集景德镇顶尖工匠,反复钻研配方与烧造火候,在仿烧宣德 “祭红” 的基础上不断调整。
不同于宣德红釉的温润醇厚,郎窑红最终呈现出更为浓艳奔放的特质 —— 釉色鲜红如牛血,玻璃质感极强,光照之下仿佛能映出火焰流动的光泽。
清人刘廷玑在《在园杂记》中记载:“郎窑所烧之红釉,华而不俗,艳而不妖,几可与宣德红釉相媲美”,直白印证了其仿古成功的口碑。
郎窑红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其 “脱口、垂足、郎不流” 的典型特征:器物口沿因釉层稀薄呈现出自然的白边,俗称 “脱口”;釉汁在重力作用下向下流淌,却终不漫过器足,形成 “垂足” 之态;整体釉面虽有流动感却无杂乱溢出,尽显工艺掌控的精妙。
故宫藏的郎窑红釉穿带直口瓶,便是这一特征的完美诠释 —— 直口微撇,瓶身修长,红釉从瓶身蔓延至足际,色泽由浅及深自然过渡,口沿的白边与足际的红釉形成鲜明对比,搭配乾隆御题 “晕如雨后霁霞红,出火还加微炙工” 的诗句,更显其作为宫廷珍品的艺术价值。
这款红釉瓷虽为仿古而生,却在工艺与审美上实现了突破,成为独树一帜的 “郎窑红”,既满足了康熙对古瓷的慕恋,也开创了清代高温铜红釉的新范式。
郎窑绿:窑变意外中的 “有意留存”
如果说郎窑红是 “奉旨创新” 的必然成果,郎窑绿的诞生则充满了窑火赋予的偶然。高温铜红釉的烧造,对窑内气氛的控制极为严苛 —— 必须维持稳定的还原气氛,铜离子才能呈现出纯正的红色。
一旦窑口密封不当、火候调控稍有偏差,空气便会进入窑内,还原气氛转为氧化气氛,原本的铜红釉就会自然转化为铜绿釉。
在郎窑红的烧造过程中,这类 “失败品” 本是要被舍弃的残次之作,却因郎廷极的审美眼光,意外成为流传后世的名釉。
郎廷极在检视窑品时,发现这些转化为绿色的瓷器,并非杂乱无章的次品:釉色莹润通透,或如嫩竹新绿,或似翡翠凝光,满身细密的开片纹如同冰裂,与酱色口沿、露胎足际的火石红相互映衬,形成独特的视觉层次。
这份 “无心插柳” 的美感,让他不忍舍弃,转而组织工匠研究其烧造规律,将偶然的窑变转化为可控的工艺,最终定型为 “郎窑绿” 这一特色品种。
这一定型并非主观臆断,而是有坚实的实物与学术佐证。瓷器鉴定大家耿宝昌在《明清瓷器鉴定》中明确指出:“绿郎窑(苹果青),又称绿哥瓷,与郎窑红釉并存,与之同类器的胎、型、足等方面基本一致,只是里外釉面均为青绿色”,并补充其 “釉面凝厚、开细碎的斜片纹,映出五彩光泽,俗称’苍蝇翅’” 的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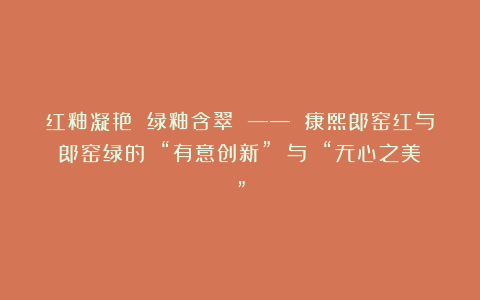
故宫博物院藏的郎窑绿釉水丞,恰好印证了这一描述:高仅 4 厘米的小巧器型,胎质坚致与郎窑红如出一辙,外壁满罩淡绿釉,开片细密均匀,口沿施酱黄釉,足内施白釉且无款识,完全符合郎窑瓷的工艺规范。
更重要的是,景德镇制瓷专家通过对传世郎窑绿器物的考证发现,尽管其存世量远少于郎窑红,但所有实物的造型、釉色、工艺细节高度统一,绝非零散的窑变残品。
这种规范性,恰恰证明郎窑绿是郎廷极有意识定型、规范烧造的品种 —— 他没有浪费窑火的馈赠,而是以督陶官的专业素养与审美眼光,将意外之美转化为经典之作。
两种名釉的 “美之共鸣”:人力与自然的和谐
郎窑红与郎窑绿,一为 “有意为之” 的巅峰之作,一为 “无心插柳” 的意外之珍,却在美学内核上达成了奇妙的共鸣 —— 两者皆是人力技艺与自然窑火的完美对话,是 “顺势而为” 的制瓷智慧的体现。
这种智慧,在郎窑红中体现为 “驭术以达意”。郎廷极遵循康熙的慕古需求,带领工匠攻克失传已久的高温铜红釉烧造技术,精准掌控配方比例与窑火温度,最终实现了对永宣红釉的超越。
这里的 “人力”,是对制瓷工艺的极致追求,是 “差之毫厘便谬以千里” 的严谨;而窑火的稳定燃烧、釉料的自然流淌,则为这份人力注入了自然的灵性,让每一件郎窑红的釉色过渡都独一无二,成就了 “艳而不燥、亮而不浮” 的审美境界。
在郎窑绿中,这份智慧则表现为 “识美而顺势”。当窑火意外改变釉色,郎廷极没有固守 “烧红” 的既定目标,而是敏锐捕捉到铜绿釉的独特美感,顺应窑变的自然规律,将偶然转化为必然。
这里的 “自然”,是窑火无常的变数,是釉料在不同气氛下的本能反应;而人力的价值,在于发现这份变数中的美,并用工艺规范将其固定,让 “次品” 蜕变为 “珍品”。
这种人力与自然的和谐,恰与宋代钧窑的窑变美学一脉相承 —— 钧窑 “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是对自然窑变的敬畏与接纳;郎窑则在承接这份敬畏的同时,更添了一份主动创造的魄力。
郎廷极没有被动等待自然的馈赠,而是以精湛技艺为基础,既 “驭火以烧红”,又 “顺势以存绿”,让两种截然不同的釉色,共同诠释了清代制瓷业 “天人合一” 的审美追求。
从宫廷需求驱动的郎窑红,到窑火馈赠催生的郎窑绿,郎廷极用一双慧眼、一份匠心,为康熙朝制瓷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两笔。
左为郎窑红釉穿带瓶 右为郎窑绿釉水丞
这一红一绿两件故宫珍品,不仅承载着清代制瓷工艺的巅峰水准,更藏着中国人对 “美” 的深刻理解 —— 美既可以是精益求精的人为创造,也可以是顺应自然的偶然所得,而真正的经典,往往是两者最和谐的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