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曾听闻,那源自上古、蕴藏天地至理的河图洛书,其核心十数之秘,竟有两数湮灭于时间长河,千年难觅?
传说这失落的玄机,并未彻底消亡,而是以某种不可思议的方式,隐匿于人身。
不在别处,恰在人体两处至为关键的要穴之中。
此乃千古之谜,亦是无数智者皓首穷经亦不得其解的绝响。
直至一位看似与这宏图伟卷毫不相干的落魄书生,命运悄然转向。
冥冥之中,一卷残破古卷落入他手,其上星点勾连,竟与失传的古数隐隐相合。
无人知晓,这微弱的星火,将点燃何等惊世的秘密。
那两处沉睡的穴位,又将如何被唤醒?
洛京城深秋的寒气,已能穿透单薄的窗纸。城南陋巷尽头,“积古斋”的匾额漆皮斑驳,几乎被岁月蚀尽。店主陈砚之伏在冰冷案几上,鼻尖几乎要蹭到那册残破不堪的绢帛。油灯如豆,将他清癯的面容和那册古卷一同浸在昏黄的光晕里。他伸出枯瘦的手指,指尖微颤,小心翼翼拂过绢帛上那些早已褪色、却仍透着神秘力量的星点与奇异勾连纹路。
“河图洛书……十数之秘……” 他喃喃自语,声音干涩沙哑,带着长久孤寂浸染的痕迹。这册意外在旧书堆底层刨出的古卷,残得只剩寥寥数页,却像一把无形的钩子,死死攫住了他全部心神。那些星点排布,隐隐与流传后世的河图洛书图式相似,却又在核心处显出令人心惊的断裂与缺失,仿佛被硬生生剜去了心脏。一丝微弱的、源自血脉深处的悸动,莫名地在他心口轻撞了一下。
陈砚之这个名字,在洛京士林早已是明日黄花。他曾是名动一时的金石考据新锐,锋芒毕露,却因过于执着于考据古物本源,质疑了几位当朝大儒奉若圭臬的“定论”,触怒了学宫权威。一场蓄谋已久的攻讦之后,他声名扫地,被冠以“离经叛道”、“妄言惑众”的罪名,逐出了清贵的学宫门墙。昔日门庭若市,如今只剩这间靠典当与替人誊抄勉强糊口的“积古斋”,以及满屋散发着陈旧纸墨气息、鲜少有人问津的故纸堆。世态炎凉,他早已尝尽,心也渐渐冷硬如斋中那些冰冷的铜器。
然而此刻,案上这册残破的绢帛,却像投入死水潭中的一块巨石,在他沉寂多年的心湖里掀起了滔天巨浪。那上面古老、残缺的星图纹路,仿佛带有某种沉睡万年的呼吸,正透过冰冷的绢丝,一下下撞击着他近乎枯竭的求知欲。一种久违的、近乎灼热的亢奋,自指尖蔓延至全身。他猛地坐直身体,眼中爆发出与这破败书斋格格不入的锐利光芒。
接下来的日子,“积古斋”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彻底紧闭。陈砚之如同疯魔,一头扎进了古籍的瀚海。他翻遍了斋中所有关于河图洛书、上古星象、乃至医家经络的残本、抄本。案几上堆积如山的书卷几乎将他淹没,只余一盏油灯顽强地亮着。饿了,啃几口硬如石头的冷炊饼;渴了,灌几口凉透的粗茶。布满血丝的双眼死死盯着那些蝌蚪般的古篆和玄奥的图示,手指在虚空中不断勾画、推演。他试图从浩如烟海的典籍碎片中,拼凑出那失落两数的蛛丝马迹。
“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他反复咀嚼着这句古老箴言,指关节因用力而发白,“十数应天地,合阴阳,通五行……缺其二,则天地之枢机断,阴阳之流转滞……这缺失的两数,究竟是何?又为何会失落?” 无数个夜晚,他枯坐灯下,对着那残卷上断裂的星图纹路,苦思冥想,几乎呕心沥血。残卷上几处模糊的墨迹,总让他觉得并非随意涂抹,而是指向了某种人体方位。
一个微雨的清晨,陈砚之裹紧洗得发白的青布长衫,顶着料峭寒风,踏着湿滑的青石板路,来到了洛京城西郊外、香火寥落的“玄微观”。道观破败,墙皮剥落,殿宇倾颓,只有几株古柏还顽强地透出些绿意。他此行的目标,是观中那位同样落魄、据说年轻时曾痴迷于古星占的老道士——云松子。据说这位老道年轻时也曾惊才绝艳,后因钻研太过“幽玄”,不为世人所容,便在此隐遁。
推开吱嘎作响的偏殿木门,一股浓重的尘土混合着劣质线香的呛人气味扑面而来。昏暗的光线下,一个须发皆白、身形佝偂如虾的道士,正蜷在蒲团上打盹,破旧的道袍沾满油渍。陈砚之恭敬行礼,说明来意,并小心地展开了那页随身携带的残卷摹本。
云松子浑浊的老眼在触及那摹本上星点勾连的瞬间,猛地爆出一丝奇异的光彩,仿佛沉睡的火山骤然苏醒。他枯枝般的手指猛地抓住陈砚之的手腕,力道大得惊人,喉咙里发出嗬嗬的痰音:“这…这纹路…小子,你从何处得来?此乃’天星隐络图’的残片!传说中,它直指河洛十数本源,更暗合人身小宇宙之秘钥!” 老道的声音因激动而颤抖,“十数缺二,非天亡,乃地藏!藏于人身两大’天地根’之中!其形隐,其位秘,非大机缘、大慧根者不能见!”
“天地根?” 陈砚之心中剧震,急忙追问,“敢问道长,所指何处?是穴位么?”
云松子布满老年斑的脸上掠过一丝复杂的神色,有狂热,有恐惧,更有深深的忌惮。他猛地松开手,剧烈地咳嗽起来,身体抖得像风中的枯叶,眼神重新变得浑浊迷茫,喃喃低语:“不可说…不可妄测…妄测者…必遭天谴…触怒神明…不得善终…咳咳…” 他仿佛瞬间耗尽了所有气力,蜷缩回蒲团,对陈砚之后续的任何问题都充耳不闻,口中只反复念叨着含混不清的呓语。
线索在希望乍现的刹那骤然断裂。陈砚之站在阴冷破败的道观里,望着状若疯癫的老道,心头沉甸甸的。那句“天地根”和“藏于人身两大天地根之中”的断言,却如同烧红的烙铁,深深印刻在他的脑海。人身穴位?天地根?他失魂落魄地走出道观,冷雨打湿了单薄的衣衫,寒意刺骨,内心却有一团火在燃烧、在追问。残卷、星图、老道的惊惧之语…碎片在他脑中疯狂旋转碰撞。他下意识地抚上自己的小腹下方——脐中深处,医家谓之“神阙”,道家尊为“生门”;又反手按向后腰正对之处,命门之火所居,阳气之根本。这两处,难道就是云松子惊惧所指的“天地根”?那失落的河洛两数,竟会藏匿于此等血肉之躯的要穴之中?这想法本身,就足以颠覆他过往所有关于“数”与“理”的认知。
回到积古斋,陈砚之的探寻并未因云松子的缄默而停止,反而更加执拗。他将所有能找到的经络图、穴位注疏都摊开,与那残卷上的星图纹路反复比对。夜深人静,他盘膝坐在冰冷的砖地上,摒弃杂念,尝试按照云松子那语焉不详的提示,以及自己对古卷的领悟,调整呼吸,意守丹田(神阙深处),同时将一缕微弱的意念缓缓引向命门区域。起初毫无异状,只有秋虫在窗外断断续续的鸣叫。然而,就在他心神几乎沉入一片空寂的某个瞬间,仿佛极其遥远的地方,传来一声极其轻微的、如同玉石相叩的“叮”的轻响,微弱得几乎以为是错觉。
陈砚之猛地睁开眼,心脏在胸腔里狂跳,背脊瞬间被冷汗浸透。刚才那是什么?是幻听?还是…穴位深处真的发出了某种回应?他低头看向自己的双手,指尖竟在不受控制地微微颤抖。一种难以言喻的、混合着巨大恐惧与极致诱惑的战栗感,瞬间攫住了他。
自从那夜,陈砚之在枯寂的积古斋中,于空冥之际,隐约听闻体内脐下与后腰深处传来那一声微不可闻、却又清晰得令人心悸的玉石叩击之音后,一切都变得不同了。
那声音如同投入深潭的石子,涟漪却在他整个生命里无限扩散。
他眼中的世界仿佛被悄然擦拭过,蒙尘的古籍文字下,开始流淌出从未见过的、闪烁着微光的奇异纹路,它们蜿蜒如活物,指向身体深处那两处被点亮的秘藏。
洛京城寻常的街巷,在他脚下延伸出无法理解的几何脉络,仿佛整个城市都笼罩在一张巨大的、无形的河洛星图之下。
更令他惊惧的是,暗处似乎有冰冷的视线粘附在背,如影随形,带着贪婪与不祥的窥探。
这突如其来的“天启”,究竟是开启千古奥秘的钥匙,还是引他踏入致命漩涡的诅咒?
那失传的两数,真能在他体内这两穴中寻回吗?
那声源自身体内部的玉石清音,彻底撕裂了陈砚之认知的帷幕。他像一个骤然被抛入陌生水域的溺水者,周遭熟悉的一切都呈现出令人眩晕的异样。积古斋中那些原本沉默的古籍,在他眼中焕发出妖异的光彩。书页上沉寂千年的墨迹,此刻仿佛拥有了生命,无数细微的、散发着幽蓝色微光的奇异纹路从字里行间、从插图边缘流淌出来,如同拥有自我意识的溪流。这些光纹并非杂乱无章,它们彼此勾连,汇聚成网,最终无一例外地指向他身体内部——脐下神阙穴的深处,以及后腰命门穴的核心。那感觉无比清晰,仿佛有两条无形的、炽热的线,一头连着书卷,一头深深扎入他的脏腑。
他惊骇地抚摸着书页,触感依旧粗糙冰冷,但那流淌的光纹却固执地存在于他的视觉之中。他猛地合上书卷,光纹瞬间消失。再打开,它们又悄然浮现,如同从未离开。这不是幻觉!陈砚之感到一种冰冷的战栗沿着脊椎爬升,但随之而来的,是一种近乎狂热的求知欲。这“视界”的异变,正是那两处穴位被某种力量初步唤醒的明证!失落的河洛两数,其踪迹,正通过这些古籍,向他发出召唤!
他强压下心头的惊涛骇浪,目光如鹰隼般扫过斋中浩如烟海的典籍。那些曾经翻阅过无数次、只觉艰深晦涩的医家宝典、道家丹经、甚至记载着古老祭祀仪礼的残篇,此刻都成了蕴藏密码的宝库。他不再需要逐字逐句推敲,只需凝神静气,将意念微微沉向神阙与命门,眼前书页上的幽蓝光纹便会自动流淌、汇聚,指向关键的信息节点。
在一卷几乎被蠹虫蛀空的《黄帝内经》古抄本残页边缘,一行曾被历代注家忽略、认为是无意义涂鸦的细小墨痕,此刻在陈砚之意念沉入命门穴的瞬间,骤然亮起!幽蓝的光纹瞬间将其勾勒、放大,显示出它并非涂鸦,而是一个极其古老、形如火焰升腾的象形符号!旁边,几个几乎褪尽的蝇头小篆在光纹的映照下也清晰起来:“命门者…火种之源…其数应离…藏而不显,动则燎原…” 离!八卦之中,离为火!这火焰符号,正是离卦的古老变体!陈砚之的心脏狂跳起来,失传的两数之一,其象为火,其位在命门!
他立刻转向神阙穴。当意念沉入脐下那片温暖而深邃的“生门”时,另一卷讲述大地坤德、万物滋生的道家残篇《地元纪》上,几处看似描述土壤厚德的文字,其笔画间竟也浮现出幽蓝光纹。光纹扭曲、聚合,最终在书页空白处,清晰地显化出一个厚重如山岳、中心蕴含旋涡的土黄色符号——坤!八卦之坤卦,象征大地、承载!“神阙…生门…纳坤元…厚德载物…其数应地…隐于渊默…” 另一段相关的文字也在光纹作用下显现。坤!失落的另一数,其象为地,其位在神阙!
火与地!离与坤!命门与神阙!陈砚之豁然开朗,一股巨大的明悟如同洪流冲刷着他的灵魂。河图洛书十数之秘,并非抽象的数字,它们对应着天地间最本源的力量与法则!失传的“七”与“八”两数(此为虚指),正是象征“火”的离之精要,与象征“地”的坤之厚德!它们从未真正消失,而是如同种子,深藏于人体这两处沟通天地的枢纽大穴之中!
然而,狂喜尚未褪去,一股冰冷的寒意瞬间攫住了他。就在他全神贯注于古籍光纹的刹那,一种被毒蛇盯上的阴冷感毫无征兆地从积古斋那扇破旧木门的缝隙外渗透进来。极其轻微,却带着赤裸裸的贪婪与窥探。陈砚之猛地抬头,目光如电射向门外。窗外是深沉的夜色,只有风吹过陋巷的呜咽。但那种被窥视的感觉,如同跗骨之蛆,久久不散。云松子那惊恐的“妄测者必遭天谴…触怒神明…不得善终”的呓语,再次在他耳边响起。他意识到,自己触碰到的秘密,引来的恐怕不只是“天谴”,更有“人祸”!觊觎这千古之谜的,绝不止他一人!
洛京城的空气骤然变得粘稠而危险。陈砚之发现自己无论走到哪里,身后总坠着几条甩不脱的影子。有时是街角一闪而过的灰衣人,有时是茶馆里看似闲坐、眼神却锐利如鹰的陌生面孔。他们如影随形,却又保持着微妙的距离,如同在等待猎物力竭的豺狼。一次去城中药铺购买常见草药的途中,一条僻静窄巷里,两个面相凶悍的汉子一前一后堵住了他。
“陈先生,” 前面那个脸上带疤的汉子咧开嘴,露出黄牙,声音沙哑,“我家主人对先生近日钻研的古物,甚感兴趣。想请先生过府一叙,共参玄机。” 他眼神扫过陈砚之紧捂着胸口(那里贴身藏着摹本和关键笔记)的位置,贪婪之意毫不掩饰。
陈砚之心头一凛,面上却极力维持镇定,拱手道:“在下不过一落魄书生,整理些故纸堆混口饭吃,实在不知尊驾所言何物。恐怕是误会了。”
“误会?” 后面那个精瘦的汉子冷笑一声,手指有意无意地按在了腰间的短刀柄上,“云松子那老牛鼻子,临死前可没少念叨先生的名字和什么…’天地根’…先生真当我们是瞎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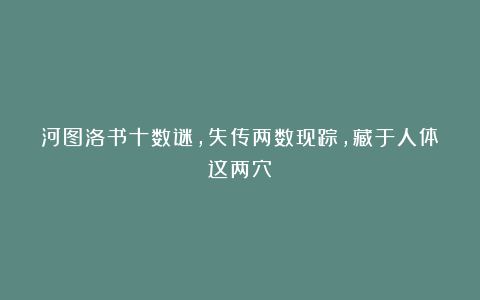
云松子死了?!陈砚之如遭雷击,一股寒意从脚底直冲头顶。老道惊恐的警告犹在耳畔,转眼竟已遭了毒手!这些人的狠辣与势在必得,远超他的想象!他下意识地后退一步,后背抵住了冰冷的墙壁,无路可退。冷汗瞬间浸透了他的内衫。怎么办?硬拼无异于以卵击石!他脑中念头急转,目光瞥向巷子一侧堆放的杂物和头顶狭窄的天空。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巷口突然传来一阵嘈杂的吆喝声和车轮滚动声。一支运送夜香的粪车队伍,正骂骂咧咧地拐进巷子,浓烈的气味瞬间弥漫开来。堵路的两个汉子被这突如其来的搅局者弄得一愣,下意识地皱眉掩鼻后退。
机会!陈砚之几乎没有任何犹豫,趁着对方注意力被转移的瞬间,猛地矮身,从带疤汉子腋下空档处如同游鱼般滑了过去!他用尽全身力气撞开一个推粪车的苦力(引来一片叫骂),头也不回地扎进旁边一条更窄、更污秽的小岔路,在迷宫般的陋巷中亡命狂奔。身后传来气急败坏的怒吼和追赶的脚步声,但他不敢回头,心脏在胸腔里擂鼓般狂跳,肺叶如同火烧。
不知跑了多久,直到确认彻底甩掉了追兵,他才瘫倒在一处堆满破箩筐的阴暗角落里,大口喘着粗气,冰冷的恐惧和劫后余生的虚脱感交织在一起。云松子的死讯和刚才的险境,如同两盆冰水,彻底浇灭了他因破解部分秘密而产生的兴奋。他知道,积古斋是再也回不去了。那里已是龙潭虎穴。
下一步该去哪里?线索指向了神阙与命门深处,但如何真正“唤醒”或“引出”那藏匿的两数?仅靠意念感应和古籍光纹的指引,似乎还远远不够。老道临死前的话提醒了他——云松子年轻时曾遍访名山大川,搜寻河洛遗迹。他猛然想起,在与云松子那次仓促而诡异的会面中,老道精神恍惚间,似乎无意识地用枯瘦的手指,在积满灰尘的地面上,反复划过一个模糊的图案,像是一座塔,又像是一个特殊的山形标记。当时他并未在意,此刻在生死危机的刺激下,那图案却异常清晰地浮现出来。
“城北…七十里…伏龙…塔…” 陈砚之喘息着,拼凑着记忆中老道含糊的呓语碎片。伏龙山!洛京以北确有此山,山势如龙伏卧!传说山中曾有一座古观,早已荒废,但从未听说有什么塔!难道那就是云松子暗示的、与河洛之谜相关的遗迹所在?这是他目前唯一的、也是最后的希望!
趁着夜色深沉,陈砚之如同幽灵,潜回积古斋附近。他不敢靠近,只远远地、借着夜色的掩护,看到几个模糊的身影在他斋外逡巡。他心如刀绞,那里有他半生的心血,有他视若珍宝的古籍,但此刻都只能舍弃。他咬紧牙关,凭着对地形的熟悉,绕到斋后一条堆满垃圾的臭水沟旁,摸索着扒开几块松动的墙砖——一个他早年为了存放最珍贵古籍而偷偷挖出的、仅容一人的小小暗格。里面静静躺着一个油布包裹。他迅速取出,紧紧抱在怀里,如同抱着最后的火种。包裹里,是那页关键残卷最精细的摹本,以及他这些日子呕心沥血记录下的所有关键笔记和推演。
没有丝毫停留,陈砚之转身融入无边的夜色,朝着北方伏龙山的方向,开始了他的逃亡与追寻。深秋的寒风刀子般刮在脸上,身后是虎视眈眈的追兵和未知的凶险,前方是渺茫的希望与深埋山中的千古之谜。他孑然一身,唯有怀中紧抱的油布包裹,和体内那两处隐隐灼热、如同在呼唤着同源的“天地根”穴位,支撑着他踽踽独行。
伏龙山如其名,山势连绵起伏,在深秋的萧瑟中宛如一条蛰伏的苍龙。陈砚之跋涉了一日一夜,避开官道,专挑人迹罕至的险峻小路,才抵达山脚。山中古木参天,落叶堆积如毯,更显幽深死寂。按照模糊记忆和仅有的方位推测,他朝着山脉中段一片尤为陡峭、形似龙首的断崖区域艰难攀爬。荆棘划破了他的衣衫和手臂,冰冷的山石磨砺着他的手掌,饥饿与疲惫不断侵袭,但他心中的那点星火却愈发清晰——神阙与命门深处,那两股微弱却顽强的气息,仿佛与山中某个未知的存在隐隐呼应着,如同归巢的指引。
就在他精疲力竭,几乎要迷失在莽莽林海之时,前方密林深处,一片断崖的环抱之下,赫然出现了一片被巨大藤蔓和荒草几乎完全覆盖的废墟!残垣断壁,依稀能辨出曾经殿宇的轮廓。而废墟最深处,紧贴着陡峭如削的崖壁,一座完全由巨大青石垒砌而成的、造型极其古朴甚至有些粗犷的石塔,沉默地矗立着!塔身不高,约莫三层,布满了厚厚的苔藓和岁月的裂痕,塔顶早已坍塌,透着一股洪荒苍凉的气息。塔身上,没有任何文字或佛像雕刻,只有一些极其简单、却透着力度的几何线条和凹槽。这绝非后世常见的佛塔或风水塔!
“伏龙塔!” 陈砚之心中狂呼,几乎要落下泪来。云松子没有疯!这深藏山中的遗迹,就是最后的线索!他跌跌撞撞地冲向石塔。
石塔底层入口早已被坍塌的乱石和茂密的藤蔓堵死大半。陈砚之奋力清理出一个仅容一人侧身挤入的缝隙。塔内空间狭小而幽暗,弥漫着浓重的土腥味和腐朽气息。空气仿佛凝固了万年。塔心并非中空,而是由一块巨大的、未经雕琢的天然青石作为核心基座,基座表面布满了深浅不一的沟壑和凹点。借着从缝隙透入的微光,陈砚之只看了一眼,全身的血液便瞬间冲上头顶!那基座上的沟壑与凹点的排列组合,虽然粗犷原始,但其核心结构,与他怀中摹本上的“天星隐络图”,以及他意念中由古籍光纹所指向的神阙、命门两穴的气机流转路径,竟有着惊人的神似!这分明是一个巨型的、实体化的河洛星图模型!而塔基中央,正对着穹顶(虽已坍塌)的位置,有两个拳头大小、深不见底的圆形孔洞,一左一右,散发着难以言喻的古老气息。
陈砚之颤抖着取出怀中油布包裹,展开那页珍贵的残卷摹本。他将摹本小心翼翼地铺在布满灰尘的塔基石面上,与基座上的沟壑凹点相互对照。摹本上断裂缺失的核心部分,其延伸的纹路,正完美地指向基座中央那两个深邃的孔洞!他屏住呼吸,将全部意念沉入体内。神阙穴(坤·地)深处,一股浑厚、承载、如大地般的气息开始缓缓升腾、流转;命门穴(离·火)核心,则是一点灼热、跃动、充满生机的火焰被点燃!这两股截然不同却又天然相生的气息,在他意念的艰难引导下,开始沿着摹本光纹和塔基石图所共同揭示的路径,在他体内缓缓运行。
起初极为滞涩,如同推动万钧巨石。每一次意念的牵引,都带来巨大的精神负荷和身体的剧烈酸痛,冷汗瞬间湿透重衣。但他咬紧牙关,死死守住心神,将全部意志灌注于那两股微弱的气息。渐渐地,气息的运行开始顺畅一丝,神阙的浑厚与命门的灼热,在体内某个无形的节点,发生了极其微妙的交融。就在这一刹那——
嗡!
塔基中央那两个深邃的孔洞,毫无征兆地同时亮起!左边的孔洞,散发出温暖、厚重、如同大地般沉凝的土黄色光晕(坤·地);右边的孔洞,则升腾起炽烈、跃动、充满生命张力的赤红色光芒(离·火)!两道光柱虽不强烈,却瞬间驱散了塔内万年的黑暗与阴冷,将整个狭小的石塔空间映照得光怪陆离!一股宏大、苍茫、仿佛来自天地初开时的古老气息,以石塔为中心,如同沉睡的巨龙苏醒般,缓缓弥漫开来!塔身那些看似无序的几何线条和凹槽,在两色光华的流转映照下,竟也次第亮起微弱的光芒,彼此勾连,形成了一幅庞大而玄奥的、缓缓运转的立体星图!星图的核心,正是那两点代表坤地与离火的光源!
成了!陈砚之心中爆发出无声的呐喊,巨大的激动和明悟让他浑身颤抖。这伏龙塔,就是上古先贤建造的,用以沟通、显化乃至封存河洛核心精义的祭坛!而唤醒它的钥匙,正是人体内那两处对应的“天地根”穴位!神阙孕坤元,命门藏离火!这失传的两数精义,并非实物,而是两种天地本源之力在人身的映射与封存!此刻,它们被这古老的祭坛所引动,显化于世!
然而,就在这天地之力显化、陈砚之心神激荡的瞬间,塔外废墟中,数道如同鬼魅般迅疾的黑影,无声无息地扑至!为首一人,身形高瘦,面覆黑巾,只露出一双狭长锐利、闪烁着极度贪婪与狠戾的眼睛。正是那日在陋巷中带人堵截陈砚之的疤面汉子!他们显然一直追踪至此,就等着这力量被引动、秘密显现的关键时刻!
“好!好得很!陈先生果然不负所望,替我们找到了这千古宝藏!” 疤面首领的声音如同夜枭,充满了压抑不住的狂喜和冰冷杀意,他死死盯着塔基中央那两点代表坤地与离火本源的光源,仿佛在看唾手可得的稀世珍宝。“现在,你可以安心去了!” 话音未落,他身后数名手下已如饿狼般扑入塔中,手中利刃在塔内流转的光华下闪烁着致命的寒芒,直取因引导力量而近乎虚脱的陈砚之!
死亡的阴影瞬间笼罩!陈砚之刚刚引导完力量,精神与体力都处于极度透支的状态,面对数名训练有素、杀气腾腾的刺客,根本避无可避!他眼中闪过一丝绝望,下意识地后退,后背重重撞在冰冷的塔壁上。
就在这电光火石之间,异变再生!那塔基石图上,因陈砚之引动神阙、命门之力而亮起的坤地(土黄)与离火(赤红)两道光华,似乎感应到了塔内骤然升腾的凛冽杀机!两色光芒猛地一颤,仿佛被激怒!塔壁上那些由光芒勾勒出的庞大立体星图,骤然加速运转!一股沛然莫御、沉重如山岳的无形压力,毫无征兆地轰然降临!如同整个伏龙山的力量瞬间凝聚、碾压而下!
扑向陈砚之的几个刺客,首当其冲。他们前冲的身形如同撞上了一堵无形的、由空气凝聚而成的铜墙铁壁!只听得几声令人牙酸的闷响和骨骼碎裂声,冲在最前面的两人如同断线风筝般倒飞出去,口中鲜血狂喷,重重摔在塔外乱石堆中,眼见不活了。后面几人也被这股突如其来的、完全无法理解的巨力震得踉跄后退,气血翻腾,脸上充满了极致的惊骇和茫然。
疤面首领脸上的狂喜瞬间凝固,化为难以置信的惊恐:“怎么回事?!这…这力量…?!” 他本能地想要后退,但那股源自整个石塔、仿佛被亵渎而苏醒的天地之威,已经锁定了他!他感觉自己如同陷入万年玄冰之中,又像被无形的巨手攥住,连呼吸都变得无比艰难,死亡的窒息感瞬间攫住了他的心脏。
而此刻,处于压力核心之外、背靠塔壁的陈砚之,却感受到截然不同的体验!那股沉重如山的压力似乎绕开了他,或者说,他体内那刚刚被引动、尚未平息的神阙(坤)与命门(离)的气息,仿佛与这塔中显化的天地之力同源共生,形成了一层微弱的保护。更让他震惊的是,当那庞大的星图因杀机而加速运转、天地之力暴动时,无数玄奥的、由光芒组成的符文和轨迹,如同洪流般强行涌入他的意识!这些信息碎片,远超他之前从古籍中拼凑的理解,直指河图洛书十数之秘的核心——天地人三才的流转,阴阳五行的生克,乃至时空变化的某种至简法则!
这些信息太过庞大玄奥,如同决堤的洪水冲击着他脆弱的精神。陈砚之头痛欲裂,眼前发黑,几乎要昏厥过去。但他咬破舌尖,以剧痛强行保持清醒,贪婪地吸收、记忆着这千载难逢的“灌顶”!
“呃啊——!” 疤面首领发出绝望而不甘的嘶吼,他拼尽全力想要挣脱那无形的束缚,甚至挥刀斩向虚空,却徒劳无功。在石塔显化的天地伟力面前,凡人的挣扎如同蝼蚁撼树。那股力量猛地向内一收、再一放!
轰!
如同无声的惊雷在塔内炸开!疤面首领和他剩余的手下,如同被无形的巨锤狠狠砸中,身体诡异地扭曲、变形,口中鲜血混杂着内脏碎片狂喷而出,眼中充满了极致的恐惧和对这超越理解力量的茫然,随即像破麻袋一样被狠狠抛飞出塔外,摔落在废墟之中,再无声息。
石塔内,狂暴的光芒和那沉重的压力,如同潮水般迅速退去。星图黯淡,坤地、离火两处光源也渐渐熄灭,塔内重新陷入一片死寂的昏暗,只有浓烈的血腥味弥漫开来,证明着刚才惊心动魄的一切。
陈砚之靠着冰冷的塔壁,缓缓滑坐在地,大口喘着粗气,浑身如同刚从水里捞出来。劫后余生的虚脱感与精神被强行灌输大量信息的剧痛交织在一起。他望着塔外那几具迅速冰冷的尸体,心中没有半分胜利的喜悦,只有无尽的苍凉和对那浩瀚天地之力的深深敬畏。伏龙塔的秘密,以最残酷的方式向他展示了守护自身的力量。那失落的河洛两数精义——坤地之厚德载物,离火之文明生发——并非让人攫取力量的工具,而是维系天地平衡、需要被理解与尊重的法则本身。
他挣扎着站起身,最后看了一眼这座沉默而伟大的上古祭坛,深深一躬。然后,他转身,步履蹒跚却无比坚定地走出废墟,走向山下。他怀中,除了那摹本和笔记,更承载着刚刚烙印在灵魂深处的、关于河洛十数本源的无价领悟。这领悟太过珍贵,也太过沉重。它不应被独占,也不该再次失落于私欲与血腥。他望向东方,洛京城的方向在晨曦微露中显出轮廓。他知道,自己该去往何方——那汇聚天下典籍、承载文脉的煌煌学宫。这一次,他将带着这来自远古的、失而复得的“天地根”之秘,以无可辩驳的实证和超越时代的理解,去叩响那扇曾将他拒之门外的大门。
河洛十数之谜,终在陈砚之引动体内神阙、命门两大“天地根”时得以窥见本源。
伏龙古塔的显化,以雷霆之势昭示了坤地离火之力,更无情涤荡了觊觎者的贪婪。
陈砚之携此烙印灵魂的天地至理,重返象征文脉的学宫。
他以残卷为引,古塔为证,将失落的河洛精义娓娓道出。
这一次,质疑化为惊叹,排斥转为敬服。
千古谜题,终在人体与天地的共鸣中得以延续。
它不再仅是玄奥的符号,而是先贤留给后世、关于和谐与平衡的永恒明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