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山西平阳府那顿当街毒打,如同滚烫的烙铁,深深刻在丘尊龙的骨血里。丘家在太皇河两岸的田亩连阡累陌,族兵披甲执锐,便是县太爷也要给几分薄面,何曾受过这等踩在泥里的羞辱?
两年,七百多个日夜,丘尊龙眼底的寒冰越积越厚。终于,在又一个辗转难眠的深夜,他唤来了自己最锋利的刀,亲弟弟丘尊虎。
“虎子,”丘尊龙的声音干涩得像砂纸摩擦,“平阳府那个姓韩的杂种,该还债了!你带上世昌,再挑两个最得力的,去!把他的人头给我提回来!”
丘尊虎,丘家族兵首领,身形壮硕如铁塔,一身虬结的筋肉在油灯下泛着古铜色的光。他沉默地点点头,眼中是兄长同样翻涌的、沉淀了两年的恨火。“哥,放心。不提着那姓韩的狗头回来,我不姓丘!”
三天后,四匹快马裹着淮北平原干燥的尘土,蹄声如闷雷,碾过黄河故道,一路向北,直扑山西平阳府。丘尊虎一马当先,丘世昌紧随其后,另外两名黑虎寨老兵如影随形。
平阳城的喧嚣扑面而来,却未能冲淡丘尊虎眉宇间凝结的煞气。他像一头闯进陌生猎场的孤狼,用最笨拙也最有效的方法搜寻着仇人的踪迹。
丘世昌扮作行商,在韩家宅邸附近支起个卖杂货的摊子,一蹲就是大半个月,眼珠子几乎黏在了那扇黑漆大门上。两个寨兵则混迹于码头脚夫、酒肆茶棚之间,竖着耳朵捕捉任何与“韩爷”相关的只言片语。
消息一点点汇聚,拼凑出韩恶霸如今的图景。当年那个当街行凶的狂徒,似乎也嗅到了复仇的腥风。他散了大把银子,身边常年跟着七八个精壮打手,个个眼神凶悍,腰间鼓鼓囊囊。出门更是前呼后拥,等闲难以近身。
丘尊虎带着丘世昌,曾在韩恶霸常去的“醉仙楼”外远远盯梢过两次。只见那姓韩的腆着肚子从楼里出来,身旁围得铁桶一般,几个打手目光如鹰隼般扫视着街面,连只苍蝇都难飞进去。
日子一天天在焦灼与挫败中滑过。平阳城灰蒙蒙的天空,压得人喘不过气。丘尊虎的眼神越来越阴鸷,像淬了毒的刀子。丘世昌看在眼里,急在心头。
这日午后,丘世昌心中烦闷,独自踱到城外官道旁一个简陋的茶棚。泥炉上黑黢黢的大茶壶噗噗冒着白气,几个赶脚的汉子正唾沫横飞地闲扯。丘世昌要了碗最粗的茶梗泡的浑水,坐在角落的条凳上,有一搭没一搭地听着。
“……要说那韩爷,如今可是越发威风了,连他妹子家都跟着沾光……”一个豁牙的老汉咂摸着嘴里的茶沫子,声音不高。
旁边一个精瘦的中年汉子接口道:“沾光?严家庄那家?快别提了!韩爷那个妹子,嫁过去十来年,也就生了两个半大小子,严家拢共才几口人?韩爷是给妹夫家置办了几亩地不假,可那严庄主啊,是个老实疙瘩,见着韩爷那阵仗,腿肚子都哆嗦,生怕惹上麻烦。前些天,韩爷带人去走亲戚,呼啦啦十几条汉子,差点把他家那小院门楼子挤塌喽!啧啧……”
丘世昌端茶碗的手猛地一顿,滚烫的茶水泼在手背上也浑然不觉。严家庄?韩爷的妹子?两个儿子?他心头猛地一跳,像黑暗中骤然擦亮了一根火柴。
他不动声色地凑近些,又摸出几个铜钱加了碟盐煮豆子,有一搭没一搭地套起话来。那豁牙老汉和精瘦汉子得了吃食,话匣子更是关不住,韩氏嫁的严家、人口几何、住在严家庄哪个方位……零零碎碎的信息,如同散落的珠子,被丘世昌飞快地串了起来。
当丘世昌按捺着狂跳的心赶回城里的落脚点,将打探到的消息一股脑儿倒给丘尊虎时,丘尊虎眼中那潭死水骤然沸腾了。他猛地站起身,魁梧的身躯几乎顶到低矮的房梁,脸上肌肉扭曲,绽出一个混合着残忍与狂喜的狞笑:“好!好一个韩家的亲妹子!好一个严家!天助我也!”
平阳城西二十里外的严家庄,正值午后,庄子里静悄悄的,大部分劳力都下了田。严家那几间土坯瓦房围成的小院,在午后的寂静里显得有些破败。
院门突然被一只穿着牛皮战靴的大脚猛地踹开,刺耳的声音撕裂了宁静。丘尊虎一马当先,像一尊铁铸的煞神撞了进来,丘世昌和两个寨兵紧随其后,腰刀已然半出鞘,寒光凛冽。
韩氏正坐在屋檐下缝补一件旧衣,闻声惊得跳起,针线筐打翻在地。她一眼就认出这几个凶神恶煞的陌生人绝非善类,尖叫着就要扑向屋后。丘尊虎一个箭步上前,蒲扇般的大手铁钳般攥住了她的胳膊,力道之大几乎要捏碎她的骨头“想活命,就闭嘴!”他声音低沉,带着浓重的淮北口音,每个字都像冰渣子砸在地上。
屋里闻声跑出严庄主,后面跟着两个半大男孩,约莫七八岁,正是韩氏的儿子。严庄主刚喊出半句:“你们……” 丘尊虎身后的两个寨兵已如饿虎扑食,一把将两个男孩掼倒在地,冰冷的刀锋瞬间横在了孩子稚嫩的脖颈上。
“啊——!”韩氏发出一声凄厉到不似人声的尖叫,疯了一般挣扎,却被丘尊虎死死按住。
“听着!想让你这两个崽子活命!”他下巴朝韩氏一扬,“现在去城里,把你哥哥韩爷给我请来!就说家里有急事,速速前来!若敢耍半点花样……”他手中的腰刀微微下压,刀刃在男孩颈侧压出一道细微的红痕,孩子吓得连哭都忘了,只剩喉咙里嗬嗬的抽气声。
“去!快去啊!”严庄主猛地推了呆若木鸡的妻子一把,声音带着哭腔,“那是你哥!他造的孽……不能拿我儿偿命啊!快去!照他们说的做!”
韩氏被丈夫这一推,踉跄几步,目光死死粘在两个儿子颈间那刀刃上。巨大的恐惧和绝望像冰冷的潮水淹没了她,她嘴唇哆嗦着,看看丈夫,又看看凶神恶煞的丘尊虎,最后视线落回儿子们惊恐万状的小脸上。
时间仿佛凝固,每一息都像刀子剜心。终于,那作为母亲的本能压垮了一切,她呜咽着,猛地转身,跌跌撞撞地冲出院子,朝着平阳城的方向狂奔而去,背影仓皇得如同被狼群追赶的母鹿。
等待的时间,每一刻都粘稠得如同凝固的血。丘尊虎像一头困在笼中的猛兽,在小院里焦躁地踱步。丘世昌守在紧闭的院门后,耳朵竖得笔直,捕捉着外面任何一丝风吹草动。
两个寨兵死死看住被捆住手脚、堵住嘴的严家父子,刀刃始终不离要害。严庄主瘫坐在地,面如死灰,眼神空洞地望着惨白的日头。那两个孩子蜷缩在墙角,小小的身体不住地颤抖。
不知过了多久,一阵由远及近的马蹄声打破了死寂,停在院门外。接着是韩氏那带着哭腔、极力压抑却依旧颤抖的声音:“哥,快……快进去吧,当家的……快不行了……”声音里浸满了绝望的伪装。
“哭什么丧!天塌了不成?”一个粗嘎不耐烦的声音响起,正是丘尊虎刻骨铭心记了两年的嗓音!沉重的脚步声靠近,伴随着另一个声音的劝阻:“爷,我们几个都进去!”
“滚一边去!你们都进去岂不让我那胆小的妹夫死的更快!”韩恶霸的声音透着跋扈和不耐烦。吱呀一声,虚掩的院门被一只穿着锦缎靴子的大脚粗暴地踹开。
就在那扇门彻底洞开,韩恶霸完全暴露在院内天光下的瞬间,蹲在门后阴影里的丘世昌猛地弹起,用尽全身力气狠狠撞上沉重的门板!
“哐当!”一声巨响,院门死死闭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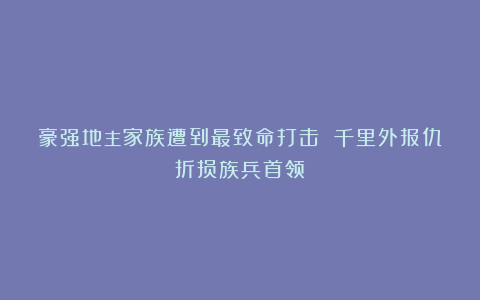
“杀!”几乎在门响的同时,丘尊虎喉咙里爆发出一声炸雷般的狂吼!积压了两年的恨火,在这一刻彻底点燃!他第一个扑向那刚刚踏入陷阱、脸上还残留着惊愕与茫然的韩恶霸!手中腰刀撕裂空气,带着凄厉的尖啸,直劈对方头颅!
韩恶霸猝不及防,本能地抬手格挡,同时发出惊恐的嘶吼:“有埋——!”伏字还未出口,丘尊虎那凝聚了全身力量、带着刻骨仇恨的一刀已然劈至!刀光如匹练!
“噗嗤!……”
战斗爆发得快,结束得更快。不过是几个呼吸之间,韩恶霸和他的两个贴身打手已成了三具倒在血泊中、兀自抽搐的残破尸体。
“叔!成了!”丘世昌抹了一把溅在脸上的血点,声音带着激战后的亢奋和颤抖。
“走!”丘尊虎猛地一挥手,声音嘶哑,带着一种虚脱般的亢奋。
“轰!轰!轰!”
沉重的撞击声如同闷雷,狠狠砸在紧闭的院门上!木屑纷飞,那并不算厚实的门板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
“里面的人听着!县衙办案!速速开门!负隅顽抗者,格杀勿论!”
丘尊虎脸上的狰狞笑意瞬间冻结!他猛地扭头,目光如电射向瘫软在地的严庄主。只见那严庄主不知何时已抬起头,脸上混杂着恐惧和一种近乎疯狂的、孤注一掷的狠厉,眼神死死地盯着院门的方向!
是他!这个懦弱的老实人,竟偷偷派了那个被绑在柴房角落、吓得半死的严家老伙计,从后院的狗洞钻出去报了官!官差来得如此之快,显然是早有准备!
“狗日的!”丘尊虎瞬间明白了,一股冰冷的寒意从脚底直冲天灵盖!杀官等同造反!这是灭族的大祸!
“翻墙!快走!”丘尊虎再无半分迟疑,狂吼一声,像一头被逼到绝境的猛兽,转身朝着后院那堵相对低矮的土墙猛冲过去!丘世昌和两个寨兵也反应极快,紧随其后。
“轰隆——!”前院的院门终于被巨力撞开!七八个身着号衣、手持长矛腰刀的县衙兵丁如狼似虎地涌了进来,当先一人身材魁梧,正是县衙捕头!
“贼人休走!”捕头一眼看到后院翻墙的人影和满院血腥,厉声大喝,“放箭!”
嗖!嗖!几支力道强劲的弩箭带着破空声射向正在翻越墙头的丘尊虎等人!两个落在最后的老寨兵闷哼一声,后心处爆开一团血花,直接从墙头栽了下来!
丘尊虎和丘世昌险之又险地避开了箭矢,两人几乎是同时滚落在院墙外的泥地上,毫不停留,朝着拴在不远处树下的战马狂奔!
“上马!”丘尊虎一个纵跃翻上马背,狠狠一夹马腹!战马吃痛,长嘶一声,撒开四蹄朝着远离平阳城的方向,向着东南方莽莽苍苍的山野亡命狂奔!
丘世昌也紧随其后,两人两骑,如同两道离弦的黑色利箭,冲入官道旁起伏的原野。身后,县衙兵丁的怒吼和急促的马蹄声紧追不舍,如同跗骨之蛆。
天色不知何时已变得阴沉如墨,铅灰色的云层低低压在头顶,闷雷在云层深处隐隐滚动。狂风骤起,卷起漫天尘土和枯草,抽打在脸上生疼。一场酝酿已久的暴雨,即将倾盆而下。
“叔!往东!进山!”丘世昌在狂风中嘶喊,雨水开始大滴大滴地砸落,瞬间打湿了衣甲。
丘尊虎伏在马背上,雨水混合着脸上的血污流淌下来。他回头望了一眼,追兵的马蹄声在风雨中显得有些模糊,但依旧顽强地迫近。他猛地一拨马头,不再沿着官道旁相对平缓的野地奔逃,而是斜刺里冲向东南方那片地势更为低洼、河道纵横的区域。那里水网密布,林木茂密,是摆脱追兵最好的屏障。
暴雨终于撕开了天幕,天河倒泻,密集的雨点砸在地上腾起一片白茫茫的水雾,能见度急剧下降。马蹄踏在迅速变得泥泞湿滑的地面上,发出噗嗤噗嗤的闷响。身后的追兵似乎被这突如其来的暴雨迟滞了脚步,马蹄声渐渐远去。
“叔!甩掉了!”丘世昌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声音带着劫后余生的喘息。
丘尊虎紧绷的神经也略略一松。然而,就在这心神稍懈的刹那,他胯下那匹精壮的淮北战马,在冲下一片长满茂密芦苇、被雨水完全掩盖了本来面目的河滩缓坡时,前蹄猛地向下一陷!
“唏律律——!”战马发出一声凄厉惊恐的长嘶!
那不是普通的泥泞!那是一片被连日雨水泡得酥软、又被上游暴涨的河水暗中掏空了的河滩!表面覆盖着水草和浮萍,下面却是深不见底的淤泥和湍急的暗流!就像一个精心布置的死亡陷阱!
丘尊虎只觉得身下猛地一空!巨大的失重感瞬间攫住了他!他甚至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连人带马,如同被一只无形的巨手狠狠拽入浑浊的河水之中!
“叔——!!!”丘世昌的嘶吼声撕心裂肺,被狂暴的雨声瞬间吞没。他眼睁睁看着那匹雄健的战马和丘尊虎魁梧的身影,在浑浊翻涌的水面上只挣扎了不到一个呼吸,便被一股汹涌的暗流猛地卷向河心,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
“叔!”丘世昌肝胆俱裂,猛地勒住自己的马,不顾一切地跳下来,连滚带爬地冲向那片吞噬了他族叔的恐怖河滩。河水瞬间淹没了他的小腿、大腿……他像疯了一样在浑浊的急流中摸索,嘶喊着丘尊虎的名字。回应他的,只有暴雨抽打水面的噼啪声和远处沉闷的雷音。
不知在汹涌的河水中搜寻了多久,丘世昌几乎被绝望冻僵。突然,他的脚踝似乎绊到了什么沉重的东西。他一个激灵,猛地扎入水中,双手拼命向水下摸索。指尖传来皮革和金属冰冷的触感!他心中狂震,用尽全身力气拖拽!
哗啦!
一具魁梧的身躯被他从浑浊的水底拖上了相对浅水的滩涂。正是丘尊虎!
泥水顺着他毫无生气的脸庞、口鼻不断流淌。那身沾满仇人血污又被河水泡得发白的劲装紧紧贴在身上,勾勒出依旧强健却已毫无动静的轮廓。
丘世昌双膝一软,重重地跪倒在泥黄的河水中。他颤抖的手抚上丘尊虎冰冷僵硬的脸颊,巨大的悲痛如同决堤的洪水,瞬间冲垮了他所有的坚强。他猛地俯下身,紧紧抱住丘尊虎那冰冷僵硬的庞大身躯,发出一声凄厉到变调的、野兽般的嚎哭:
“虎叔——!!!”
悲怮的哭嚎在暴雨倾盆、浊浪翻涌的河畔回荡,却显得如此渺小而无力,转瞬便被天地间浩荡的雨声水声彻底吞没。
丘家最锋利的刀,丘尊龙复仇的意志化身,太皇河畔令人闻风丧胆的族兵首领丘尊虎,终究未能跨过这条奔涌的大河。
他斩断了仇人的脖颈,却最终断送了自己的性命,沉沦在这复仇终章的、冰冷的浊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