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矿殇到桃源:
郝湖村的绿色蝶变
《新沂市报》2025-10-17 阅读数:29
郝湖村新来的年轻村官小赵,第一次来到村里,跟着村支书郝其选在村里了解村情时,被眼前景象惊呆了。六月的风掠过村外那片浩渺桃林,沉甸甸的水蜜桃在枝头微微颤动,空气里弥漫着甜香,连呼吸仿佛都成了享受。郝其选随手摘下一个饱满的桃子,递给他:“尝尝,这才是郝湖的味道。”
小赵咬了一口,丰沛的汁水瞬间在口中炸开,清甜直抵心脾。他忍不住赞叹:“真甜!”
郝其选的目光却越过眼前这片醉人的葱茏绿意,投向远处几座沉默的土丘。那里荒草稀疏,裸露出灰白或暗红的矿土底色,像大地无法愈合的伤疤。他声音低沉下来:“甜?七八年前,这里风一刮,裹着的全是砂石,打在脸上生疼,吸一口气,肺里都是灰渣子,那滋味……才是刻骨的郝湖。”
小赵顺着他的目光望去,那几座光秃秃的矿渣山丘,在盛夏浓得化不开的绿色里,显得格外刺目而苍凉。甜桃的滋味尚在舌尖,支书口中那呛人的风砂却已扑面而来,吹开了郝湖村尘封的、布满裂痕的过往。
第一章 砂海沉金与大地呻吟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时集镇郝湖村的地底下,埋藏着让无数人眼热的财富——石英砂。郝其选那时还是郝湖村一位血气方刚的青年,他卷起袖子,加入了村里轰轰烈烈的“淘砂”大潮。1996年,每吨石英砂能卖十几元,到了2010年,价格更是飙升到每吨300元以上。财富,似乎触手可及。
那是一个属于机器的喧嚣年代。12家石英砂厂如同十二头巨兽,日夜不停地咆哮、吞吐。巨大的挖掘机挥动着钢铁臂膀,狠狠地啃噬着土地。运砂车排成长龙,沉重的车轮碾过村道,扬起漫天蔽日的黄尘。整个郝湖村,终年笼罩在粉尘的灰幕之下。
郝其选清楚地记得,那些年,村民们洗好的衣服晾在外面,不到半天就会蒙上一层洗不净的灰黄色。窗户常年紧闭,也挡不住无孔不入的砂尘。更令人揪心的是健康。村里咳嗽声此起彼伏,尤其是上了年纪的老人,气管炎、肺气肿几乎成了常见病。村里的赤脚医生郝大夫见此情况连连摇头,诊所里最畅销的永远是止咳糖浆和消炎药片。
村西头的老矿工郝三爷,是郝其选的远房堂叔。他曾在矿上干了小半辈子,如今咳起来惊天动地,佝偻着背,像一张随时会折断的弓。一次郝其选给他送药,老人枯瘦的手死死抓住他的胳膊,浑浊的眼睛里全是痛苦和绝望:“其选啊,这肺里……跟塞满了砂石磨子一样,喘不上气啊……这钱,真是拿命换的……”话没说完,又是一阵撕心裂肺的咳,憋得脸膛发紫。没过两年,郝三爷就在一个飘着砂尘的深秋早晨走了。送葬的队伍穿过被粉尘染得灰蒙蒙的田野,唢呐呜咽,像是在为这片伤痕累累的土地哭泣。
财富的代价,是郝湖村的青山绿水变成了千疮百孔的废土。昔日肥沃的农田被矿坑无情吞噬,取而代之的是巨大的采掘坑,像大地被剜去一块块血肉,露出深不见底的狰狞伤口。矿坑边缘陡峭危险,四周散落着碎石和矿渣堆成的土丘,寸草不生。流经村边的小河,曾是清亮的,如今裹挟着矿泥和洗砂的浑浊废水,变成了一条令人望而生厌的“牛奶河”。鱼虾绝迹,连水鸟都不再落脚。孩子们被严厉警告不准靠近那些深坑和污河,失去了嬉戏的水边乐园。
村民们的心,也被这漫天的粉尘和机器的轰鸣撕裂。有人因开矿一夜暴富,盖起了村里最早的水泥小楼,摩托车突突作响,惹人艳羡。更多的人,则守着被矿渣侵蚀、日益贫瘠的薄田,或是靠给矿上打零工挣些辛苦钱,在飞扬的尘土里艰难谋生。贫富差距像无形的裂谷,横亘在邻里之间,淳朴的乡情在利益的沙尘暴中被一点点风化剥蚀。年轻人纷纷外出,试图逃离这个灰头土脸、看不到未来的家乡。村子,在表面的“繁荣”下,正无可挽回地空心化、衰败化。
郝其选站在自家平房顶上,望着远处矿坑蒸腾起的尘烟,听着机器的轰鸣,手里攥着刚领到的又一笔“分红”。这钱沉甸甸的,带着砂石的粗粝感,也带着郝三爷临终前那痛苦的喘息和绝望的眼神。他心里的不安如同村外那些矿坑,一天比一天深不见底。这看似滚烫的砂金,究竟要把郝湖村带向何方?脚下的土地在机器的啃噬下颤抖呻吟,他能清晰地感觉到一种巨大的、不祥的阴影,正随着漫天黄尘,悄然笼罩整个村庄。
第二章 断腕关停与黑暗低谷
2014年的初冬,寒风裹挟着砂砾,抽打在郝湖村每一张愁云密布的脸上。一纸措辞严厉的环保整改令,如同冰冷的铡刀,猝然落下。省市两级环保督查组开出的“诊断书”触目惊心:粉尘排放超标十几倍,洗砂废水直排河道,土地破坏严重……结论只有两个字——关停!
命令传来那天,郝其选正与几位矿主在“兴旺砂厂”的办公室里激烈争执。窗外,机器的轰鸣声依旧震耳欲聋。一位矿主拍着桌子,唾沫横飞:“关?说得轻巧!老子身家性命都押在这矿上,关了喝西北风去?几百号工人等着吃饭呢!”另一个声音尖锐地附和:“对!法不责众!咱们十二家厂子,上千号人,上面都敢关?没王法了!”
郝其选坐在角落,指间的劣质香烟快要燃尽,灼烧到皮肤也浑然不觉。他眼前晃动着郝三爷临终时痛苦的脸,耳边回响着村民对污浊空气和河流的怨声载道。他张了张嘴,喉咙干涩发紧,那句“也许……是该停了”终究没能说出口。巨大的矛盾撕扯着他:一边是赖以生存的产业和上千人的饭碗,一边是乡亲们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和无法回避的法律红线。他感到自己正被无形的力量推向悬崖边缘。
然而,环保风暴没有给他们留下任何侥幸的余地。短短一个月内,强制执行的期限到了。那一天,巨大的挖掘机停止了挥动的臂膀,传送带僵死般静止,震耳欲聋的破碎机声第一次在郝湖村的上空彻底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死一般的沉寂。只有风,卷起矿坑边缘干燥的浮尘,发出呜咽般的低啸。运砂车不见了踪影,空留下被重载压得坑洼破碎、覆满厚厚粉尘的村道。喧嚣戛然而止,巨大的失落与恐慌瞬间吞噬了村庄。
“兴旺砂厂”的看门老吴头,蹲在紧闭的铁门前,浑浊的老泪顺着沟壑纵横的脸颊淌下,混着脸上的灰尘,留下泥泞的印子。他枯瘦的手指一遍遍无意识地抠着锁链上的铁锈,嘴里喃喃自语:“完了……全完了……这往后的日子,可咋过啊……”他的儿子和儿媳都在这个厂里做工,一家人糊口的指望断了。
村里的小卖部,曾是矿工们下班后聚集买烟买酒、喧嚣热闹的地方。如今柜台后面,老板娘王婶愁眉苦脸地守着冷清的店面,货架上的商品蒙着一层薄灰。她对着串门的邻居叹气:“唉,以前一天能卖好几条烟,现在?两三天也卖不了一条。人都没魂了,哪还有心思买东西?这店,怕也是开到头了。”语气里满是萧条。
更深的痛楚在那些失去了唯一收入来源的家庭里蔓延。村民郝大壮,人如其名,曾是个壮劳力,在矿上开大车。关停后,他蹲在自家门口的石墩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脚下扔满了烟蒂。妻子抱着刚满周岁的孩子,在屋里低低啜泣。孩子似乎感受到了压抑的气氛,也跟着哇哇大哭起来。那哭声在空旷寂静的村庄里显得格外刺耳和绝望。郝大壮猛地将烟头摁灭在石墩上,火星四溅,他抱着头,肩膀剧烈地耸动起来。生活的重压,瞬间将这个壮汉压垮了。
没有了机器的轰鸣,郝湖村的夜变得格外漫长而寒冷。月光惨白,照着那些沉默的厂房、巨大的矿坑和光秃秃的矿渣堆,如同战后的废墟。偶尔几声犬吠,更衬出无边的死寂。村民们早早熄了灯,蜷缩在冰冷的被窝里,却难以入眠。对未来的巨大茫然和生存的恐惧,像冰冷的蛇,缠绕在每个人的心头,越收越紧。
郝其选独自走在空旷的村道上。脚下是厚厚的粉尘,踩上去发出令人心头发毛的“沙沙”声。寒风钻进他单薄的衣领,刺骨的冷。他抬头望向夜空,没有星星,只有矿尘散尽后残留的、灰蒙蒙的混沌。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窒息感。作为村支书,他亲手参与并见证了这场因砂而起的“繁荣”,如今又眼睁睁地看着它轰然倒塌,留下一个满目疮痍、人心惶惶的烂摊子。路在何方?希望在哪里?沉重的问号像巨石一样压在他的胸口,让他几乎喘不过气。这死寂的冬夜,仿佛没有尽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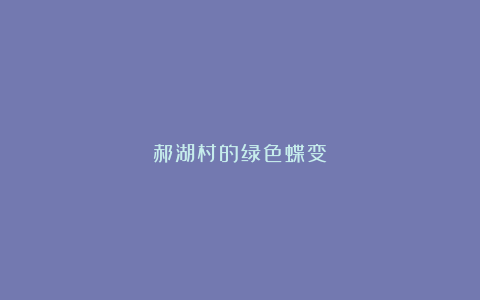
第三章 桃李不言的艰难抉择
2016年,深冬的严寒依旧封锁着郝湖村,而另一份冰冷沉重的“标签”再次压了下来—省级经济薄弱村。这顶帽子像一块巨大的寒冰,既砸在了村“两委”班子每个人的心上,也砸在了每一位郝湖村民的心头。耻辱、焦虑、绝望的情绪在冰冷的空气中弥漫。
村委那间简陋的会议室里,烟雾缭绕,气氛凝重得能拧出水来。墙上挂着“省级经济薄弱村”的牌子,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灼烤着在场的每一个人的眼睛。郝其选掐灭了不知第几根烟,声音嘶哑地打破了令人窒息的沉默:“都说说吧,这穷帽子,咱郝湖人戴不起!到底还能干点啥?坐着等死还是闯条活路?”他的目光扫过一张张愁苦而疲惫的脸。
“还能干啥?除了挖砂,咱郝湖人还会啥?祖祖辈辈就指着土里刨食,可你看看咱们的地儿!”老会计郝长顺敲着桌面,指着窗外远处矿渣堆旁零星的几块撂荒薄田,“那地都毁了!种啥?石头蛋子能长庄稼?”
“就是!出去打工吧,年纪大的谁要?年轻人都跑光了!”有人附和道,声音里满是无奈和怨气。
“打工?”角落里一直沉默的退伍军人、支部委员郝勇猛地抬起头,眼睛里有股不服输的狠劲,“打一辈子工?郝湖村就永远是个空壳子?永远顶着这顶破帽子?我看,还得在土地上想办法!外面搞得好的村子多了去了!”
郝勇的话像投入死水潭的石子,激起了微澜,也引来了更多质疑。
“想啥办法?种粮食?一亩地刨去本钱能挣几个?够填肚子就不错了!”
“搞养殖?没技术,闹场瘟病就血本无归!”
“种果树?谁懂?卖给谁?烂在地里哭都找不着调!”
争论声此起彼伏,充满了怀疑和悲观。郝其选听着,眉头紧锁。他知道,乡亲们怕了。砂矿关停的阵痛还未过去,任何新的尝试都意味着未知的风险和投入,大家输不起。
“都别吵吵了!”郝其选猛地一拍桌子,震得茶杯盖叮当作响,“怕!我也怕!怕再选错路,把乡亲们最后一点指望都折腾没了!可光怕顶啥用?穷帽子就能自己飞了?”他深吸一口气,目光变得锐利起来,“长顺叔说得对,咱除了地,还有啥本钱?勇子说得也在理,外面有干成的!我看,咱不能在家干坐着瞎琢磨!走出去,看看人家咋活的!”
郝其选的话掷地有声。村“两委”最终达成共识:走出去,取真经!一支由村干部、党员代表和有想法的村民组成的考察队,顶着凛冽的寒风出发了。他们的足迹踏遍了山东寿光闻名遐迩的蔬菜大棚,那里四季如春,蔬果累累;走进了苏北丰县集中连片、蔚为壮观的苹果基地,红彤彤的苹果压弯了枝头;也探访了本省一些依靠特色林果业脱贫的先进村。
寿光温室里滴灌系统精密的流水声,丰县果农分拣苹果时爽朗的笑声,深深刺激着郝湖考察队员的神经。更让他们心头一震的是,在参观一个依靠丘陵地种植水蜜桃致富的村子时,那位皮肤黝黑的老支书拍着郝其选的肩膀说:“老弟啊,地是死的,人是活的!咱这坡地,以前种啥啥不行,可桃树就爱这地势,通风透光,果子甜!关键得找准路子,还得豁出去干!”
“找准路子,豁出去干!”这八个字像火种,点燃了郝其选心中压抑已久的希望。他蹲在人家桃园的地头,抓起一把沙壤土仔细捻着,又抬头看看远处起伏的山坡—这土质,这地貌,和饱受创伤的郝湖何其相似!
考察归来,村“两委”的灯几乎成了长明灯。对比、分析、争论,夜复一夜。寿光的蔬菜需要精细化管理和大棚投入,成本太高;苹果种植周期长,技术要求也苛刻。而水蜜桃,管理相对粗放,对土壤适应性较强,尤其耐瘠薄,市场行情稳定,见效周期相对较短。最关键的是,新沂本地已有一定的桃产业基础,邻近的小青山万亩桃园就是活招牌,技术、销路都有辐射的可能。
“种桃!”郝其选指着铺在桌上的土壤检测报告和气候资料,斩钉截铁:“就种水蜜桃!咱们郝湖这沙壤土,透气性好,加上光照足、昼夜温差大,种出的桃子甜度肯定差不了!这是老天爷留给咱郝湖最后的本钱!”
然而,决定公布后,迎来的并非一呼百应,而是更深的疑虑浪潮。
“种桃?说得轻巧!树苗钱哪来?肥料钱哪来?三年挂果,这三年喝风啊?”老成持重的郝长顺第一个摇头。
“技术呢?剪枝、疏果、防虫,哪样是好伺候的?弄不好血本无归!”有过失败种植经历的村民老李头心有余悸。
“销路呢?小青山那边种桃的多了去了,咱这新种的,谁认?到时候桃子烂在树上,哭都没眼泪!”小卖部王婶的话代表了大多数人对市场的担忧。
质疑声如同冰冷的潮水,几乎要将刚刚燃起的微弱火苗扑灭。郝其选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他知道,要让这片被砂矿蹂躏过的土地重新孕育希望,要让这些被贫困和失败磨灭了心气的乡亲们重新站起来,光靠一个决定远远不够。他们需要实实在在的支撑,需要看到破土而出的第一抹新绿。资金,成了横亘在希望之路上的第一座大山。
就在这时,一个意想不到的身影走进了村委会。李金平,一个沉默寡言、眉宇间凝结着化不开愁苦的中年妇女。她的丈夫几年前因病去世,留下孤儿寡母和一笔沉重的债务,生活跌入谷底。她局促地站在郝其选面前,手指绞着洗得发白的衣角,声音低哑却带着一丝孤注一掷的勇气:“郝书记……我……我想试试种桃。家里那几亩薄田荒着也是荒着……可,可我没钱买苗子……”
李金平的出现和她眼中那份被生活重压却仍未熄灭的微光,深深刺痛了郝其选,也更坚定了他破局的决心。不能让一个愿意尝试、渴望改变的乡亲被挡在起步的门槛之外!
“金平,你放心!”郝其选站起身,语气异常坚定,“钱的事,支部想办法!活路是闯出来的,不是等出来的!”
一场为郝湖村寻找“绿色血液”的战役打响了。郝其选带着厚厚的申请材料,一趟趟跑镇政府、市扶贫办,反复陈述郝湖村的困境和转型的决心,嘴唇起了泡,皮鞋磨破了边。郝勇则利用自己的战友关系,四处打听政策信息。精打细算的老会计郝长顺,戴着老花镜,逐条研究扶贫贷款政策和合作社章程,力求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郝湖村绝境求生的决心和详实的规划方案,终于打动了上级部门。一笔200万元的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和60万元的后方单位帮扶资金,如同久旱后的甘霖,注入了郝湖村焦渴的土地。郝其选捧着那份沉甸甸的批复文件,手抑制不住地颤抖。他知道,这不仅仅是钱,更是郝湖村绝处逢生的最后一张船票,承载着整个村庄沉甸甸的未来。
资金到位只是第一步。如何用好这笔“救命钱”,凝聚人心,建立可持续的机制,考验着村“两委”的智慧。经过无数次激烈的讨论和民主商议,一个创新的思路逐渐清晰:成立合作社,抱团取暖,共享收益!
在村民代表大会上,郝其选详细阐述了“新沂市汇康果蔬专业合作社”的构想。村集体利用扶贫资金和帮扶资金,统一流转村民手中闲置或低效的土地,规模化种植水蜜桃和核桃(长线收益保障)。村民们可以用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也可以用扶贫资金入股,成为合作社的股东。对于像李金平这样特别困难又有意愿的农户,合作社提供种苗、技术,并帮助申请小额贷款。
最引人瞩目的是郝其选提出的“4321”分红方案:40%归村集体:用于合作社持续运营、扩大再生产、抵御风险;30%用于村里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再投入:修路、通渠、改善环境,让发展成果惠及全村;20%作为全村老百姓的分红:按股或按户分发,人人受益;10%专门用于低收入农户的分红:精准帮扶最困难的群体。
“这桃子还没种下去,就想着分钱了?能成吗?”会场里依然有窃窃私语。
“咱们这穷家破业的,搞这么大阵仗,万一……”
质疑声依旧存在,但希望的火苗,毕竟在政策的东风和集体行动的规划中,艰难地、顽强地燃烧起来。郝湖村这艘迷失在风沙中的破船,终于调转了锈迹斑斑的船头,朝着一个名为“水蜜桃”的未知彼岸,开始了它充满挑战的航程。
(未完,下期待续……)
新 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