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熊禮匯
劉永濟(一八八七—一九六六),不但是二十世紀著名的《楚辭》專家、《文心雕龍》專家,而且對《文選》深有研究。從劉永濟手批《昭明文選》即可見一斑。先生手批的《文選》版本,是海録軒藏版何義門先生評點之重刻《昭明文選》李善注 。考察先生一生的治學範圍和講學内容,他自幼及老,誦讀、批點的《文選》,當遠不止此一種。其藏書遺物中,就有不少記有研習《文選》作品心得的散頁。只是在何義門評點本上評語較多、且全書保存得十分完整而已。
劉永濟先生生平著述甚多,其中論及《文選》和援引《文選》及前人選學内容者亦不在少數。其學術名著:
一如寫成於一九一七年的《文學概論講義》(一九二二年出版時更名爲《文學論》),論文體分類,即云“我國文學體制分類之源有二:一爲梁 昭明太子之 《文選》,後世總集文章者宗之。一爲漢劉歆之《七略》,後世總集群書者祖之。前者專主文章,其界狹。後者遍及群籍,其界廣。”“ 《文選》不收經、史、子,惟取’綜輯辭采,錯比文華’’事出沉思,義歸翰藻’之文。故阮芸臺曰’昭明所選,必文而後選’,是也。後世之 《唐文粹》《宋文鑑》,即踵之而作。至姚姬傳選《古文辭類篹》,號爲最佳。然類分十三,尚多未當。梅伯言《古文詞略》,於姚之十三門外,增詩歌一門。曾文正公之《經史百家雜抄》,總分三門,各繫子目,皆佳於姚,亦未能盡善。”“由總集文章之門類得下之結果:梁以來經、史、子不屬文學,《文選》重在文采、情思。”又於其書附録之《古今論文名著選》,列入“梁昭明太子《文選序》”。而在一九二二年發表之《學文初步之書目提要 》中,謂“《文選》,南朝梁昭明太子蕭統選,爲總集之始祖,駢體多,可讀”。
二如始作於一九二八年之《中國文學史綱要》(後更名爲《十四朝文學要略 》), 叙論言文之“體類”,即謂“昭明選文,列目四十”,且細加説明:“按梁昭明太子蕭統 《文選》有賦、詩、騷、七、詔、册、令、教、文、策問、表、上書、啓、彈事、牋、奏記、書、移書、檄、難、對問、設論、辭、序、頌、贊、符命、史論、史述贊、論、連珠、箴、銘、誄、哀文、碑文、墓誌、行狀、弔文、祭文,共四十目。”卷一謂“溯文之源,則不但伏羲畫卦,文籍始生”,亦引蕭統《文選序》相關言辭爲證。説諸子文學之影響,則謂“昭明選文,乃謂老、莊、管、孟之流,不以能文爲本,略而弗録。是蓋不知文之涵義,有非純取藻繢者矣”。卷二則有云:“昔昭明選文,騷賦異卷;彦和論藝,别賦於騷;而班志藝文 ,但稱屈賦,不名楚騷。嘗思其故,蓋蕭、劉别其流而班氏窮其源耳。然則論漢賦之流别者,此其大界矣。”又論蘇、李詩爲後人僞作,而“據彦和’擬作’之言,證以當時風會,斷其非處西京”,又謂“蘇詩四首,昭明固未嘗以爲别李之詩”;“按仲洽、仲偉、彦和三君,淵雅多識,文家董狐。皆論都尉而不及屬國,殆彼時獨致疑於李詩耳。昭明愛奇,兼收蘇作,亦未嘗有’贈别’之説也”;“何焯評《文選》李詩曰:’子瞻辯蘇李之詩爲後人擬作,然固非曹劉以下所能辦也。’評蘇詩第四首曰:’江 漢浮雲,一失不復返,一分不復合,以比離别,不得以地非塞外爲疑。少卿詩曰皓首,子卿報以隨時,亦不欲其没異域,示之以不可長也。’按此説亦依違”;“總觀以上諸家之論……惜皆未從一代風會之大處着眼,故有此紛紛也”。又説“古詩十九,致疑枚叔”,取材辨析皆不離《文選》 及前人“ 選學”之説。而言及梁末詩風,有謂“此集(指簡文爲太子時令徐陵所編之《玉臺新詠》)不如《文選》之近雅,故《文選》盛行於唐,而此集稱者獨少”。至於書中評論詩文藝術特色,介紹作者生平、創作風格,引述《文選》李善之注亦在在有之。
三如寫成於一九三三年之《屈賦通箋》,《 離騷》“正字”引《文選》 及選學著述七處,《九辯》“正”字引《文選》及選學著述三處,《九歌》“正字”引《文選》及選學著述四處。並於 《通箋》引用書目列出《文選》《文選集釋》《文選理學權輿》《文選旁證》《文選箋證》《選學膠言》六種書目。
四如完成於一九三三年之《文心雕龍徵引文録》,因豔羨摯虞撰《文章流别志論》 而外,復有集四十一卷,而感慨“後之作者,類多偏主,今所存《昭明文選》,撰録之類也;《文心雕龍》,詮品之流也”,故就《文心雕龍》“所論列之文,撮録爲一編”。“凡所徵引,泛濫四部。篇章繁富,什倍蕭選 ”。其中,補入《 文心雕龍》 “舉人而不選文”“論體而未定篇”之文,和落實“虚述而不指實”之文,則“參以(《 文心雕龍》)下篇所論列。論列未及者,佐以蕭選 。蕭 選所無者,始取之後人撰録之總集”。
上述僅爲先生幾種著述中所含研習《文選》之心得者。又,先生在武漢大學中文系每兩年給三四年級學生講授一年漢魏六朝文的必修課(該課程“詳述漢魏六朝文體之流變,詮品當時作家之異同……俾諸生得欣賞其藝術,而抉擇其高下”,同時還指導研究漢魏六朝文學之畢業論文,這些都離不開對《文選 》及選學的深入研究。反復深入研究而悟入有得,亦屬當然。正因如此,我們才看到先生評論周秦漢魏晋宋齊梁詩文的語句,既見於其著述,又見於其手批《文選》中。論其出現之先後,應該是研習《文選》有得而手批在前。
劉先生手批《文選》,既通過對所選作品及其注釋文字的校勘和訓詁正字、正音,以糾正前人之失或助補前人之缺;又對所選作品作者真僞加以辨析,於作者創作風格加以介紹,於作品字句加以訓釋,於段落、篇章之義加以分析,於全文立意、藝術特色、文學美感加以揭示,並在對其作出總體評價的同時,於前人不同意見提出自己的看法。内容涉及傳統《文選》學的方方面面,而以文字校訂、訓詁和衡鑒評論文章爲主。比較而言,評文分量更重,不但所論作品較多,而且説得細緻深入,顯出先生特有的文學趣味和良好的文藝鑒賞能力。
文字校訂、訓詁、釋義有直陳己見者,亦有援引文獻或選學名家之言作論者。前者如屈原《九歌》雲中君 “靈皇皇兮既降”劉先生批曰:“古者以巫迎神,必象神之服飾,用神之器物。及神降巫身,又代神之語言,此王注所以訓’靈’或神或巫也。”再如班固《兩都賦序》 “抑亦雅 頌之亞”,先生批曰:“’雅 頌之亞’,即漢賦與楚騷不同之處。”又如枚乘《七發》 ”今太子膚色靡曼,四支委隨”,王逸注曰:“隨,不能屈伸也。”先生批曰:“’委隨’即’委佗’。”又如賈誼《 鵩鳥賦》 “傅説胥靡兮乃相武丁”,先生批曰:“胥,相也;靡,隨也。”又如賈誼 《弔屈原文》 “遥曾擊而去之”,注曰:“如淳曰:鳳凰曾擊九千里,絶雲氣。遥,遠也。曾,高高上飛意也。鄭玄曰:擊,音攻擊之擊。李奇曰:遥, 遠也。曾,益也。”先生批曰:“曾擊即層翼。翼以擊搏,此以用爲名也。遥,同摇。”又如東方朔《答客難》 “同胞之徒無所容居”,蘇林曰:“音胞胎之胞也,言親兄弟也。”先生批曰:“注指同胞爲親兄弟,非。蓋指同儔。”“胞,疑袍之借字,同袍,即《詩· 秦風》 ’與子同袍’之’袍’。”又如曹丕《典論· 論文》 “徐幹時有齊氣”,李善注謂“言齊俗文體舒緩,而徐亦有斯累”,先生批曰:“齊氣,乃言偉長《中論》有稷下諸子風氣,蓋許其能持論也。注非。”劉先生自陳己見,看似脱口而出,實則出自其飽學多思的深厚積累,和在學術研究中形成的理性認知系統,故言之中的或識見超卓。比如對“齊氣”的解釋,即源於他的’戰代文學風氣有三大宗主(指齊風、楚風和秦風。而齊風之代表人物稷下諸子’以理智爲主,長於辨析推衍’)”的重要觀念,自有其合理性和創新性。
後者援引文獻和選學名家之言正字釋義者甚多。如司馬相如 《封禪文》 “鬼神接靈圉,賓於閑館”,先生批曰:“郭璞曰:靈圉,仙人名也。按此句當是接鬼神靈圉於舘。”同篇“詩大澤之博”,先生批曰:“詩,承也。沈欽韓説。”同篇“而梁父罔幾也”,先生批曰:“幾有望義。《史記· 晋世家》’毋幾爲君’,《索隱》訓望。幾,又訓期。期望 、希冀,皆庶幾之義,故曰無所庶幾。”同篇“厥之有章”,先生批曰:“之,志也。墨子以’天之’爲’天志’。”又如揚雄《解嘲》 “欲談者卷舌而同”,劉先生批曰:“同,《漢書》作’固’。固,閉也。”同篇“顩頤折頞”,先生批曰:“顩,《漢書》作’顉’。師古曰:’曲頤也,音欽。’”同篇“亢其氣”,先生曰:亢,《漢書》作’炕’。師古曰:’炕,絶也。’”又枚乘《七發》“猶將銷鑠而挺解也”,高誘《吕氏春秋注》曰:“挺,猶動也。”先生批曰:“挺,亦解也。見《後漢書· 臧宫傳》注、《傅燮傳》 注。”又顔延之《陶徵士誄》 “道路同塵”,先生批曰:“道,善本原作’首’,此作’道’,當是’導’字,然不如’首’字。”又謝靈運《道路憶山中》 “楚人心昔絶,越客腸今斷”,注謂“楚人,屈原也”,先生批曰:“楚人,鍾儀爲晋幽囚,秉操南音,喻思歸也。注誤。”又任昉 《王文憲集序》 “有詔毁廢舊塋”,先生批曰:“羅振玉 《敦煌本〈文選〉跋》曰:’發毁舊塋,今本發作廢。’’敦煌本乃隋代寫本,此文無注,或乃李善未注前本也。文内衷字缺筆作哀(《誄》有“皆折衷於公”句)。’”先生徵引文獻訓詁釋義,除援引《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晋書》《南史》《資治通鑑》 等史書及相關訓詁注釋外,還用到《 北堂書鈔》《初學記》《一切經音義》《太平御覽》《藝文類聚》 和眾多别集,以及《 説文》《廣雅》 等字書。至於援引學者之説訓詁釋義、正字正音,涉及學者雖不乏清代以前者,如劉向、崔豹、郭璞、湯惠休、鍾嶸、劉勰、王世貞、陳繼儒、孫月峰等;但更多的是清代學者,如王念孫父子、錢大昕、沈欽韓、李慈銘、孔廣森、孫志祖、何焯、姚鼐、吴汝綸、梅曾亮、梁章鉅、王先謙等。而援引王念孫一人説法最多,《文選》前八卷十三篇大賦之訓詁至少有十篇用到王氏 《讀書雜志 ·餘編下》之説。像批點揚雄 《甘泉賦》《羽獵賦》,均是四引王説;班固《西都賦》,張衡《 西京賦》《東京賦》,均是五引王説;批點司馬相如《上林賦》、左思《吴都賦》,均是六引王説。
評文即衡鑒評論文章,是劉先生《文選》批點的主要内容,這一點既是先生用力的重點,也是本書一大特點。先生有意於此,似與其研究文學十分重視文本的習慣有關,故而特别注重準確把握作品立意和作家情思走向,深入細緻領略其行文之妙及文内文外之美。至於評論精到,則與其良好的文學理論修養、 豐富的創作經驗以及合理取用前人之見有關。
正因先生治學十分重視對作品的衡鑒,故其批點《文選》,特選何焯評點本爲底本。何焯爲清代選學名家,黄侃即謂“清世爲《文選》之學,精該簡要,未有超於義門者也”。又謂其衡文雖有“蔽”未祛,而“論文亦有精語”(《文選平點》)。其論文涉及文章學的方方面面。
有論及古人風格者,如論張衡 《西京賦》,謂“平子彩奇詞秀,全祖相如,固是孟堅以上人”。論王粲《 詠史詩》,謂“仲宣詩極沉鬱頓挫,而鍾記室以爲文秀而質羸,殆所未喻”。有論及文章立意者,如説班固 《東都賦》 “前篇(《 西都賦》)鋪張揚厲,此篇乃專頌功德。立意輕重較然”。説曹植《洛神賦》 ,“托詞宓妃,以寄心文帝,其亦屈子之志也”。説陶潛《歸去來辭》,“雖去騷人已遠,而詞旨超然,自覺塵埃不到”。有論及書寫策略者,如論司馬相如 《子虚賦》 ,謂“《子虚》《上林》 爲宋玉嫡派,從《高唐賦》而鋪張之,加以縱横排宕之氣,其局開張,其詞瑰麗,賦家之極軌也”。論揚雄《 長楊賦》,謂“客卿之談,正論也;主人之言,微詞也。正論多忤,微詞易入,所以爲諷。借客卿口中入正論,正妙於諷也”。有論及藝術特色者,如論揚雄 《解嘲》,謂“詞古義深,子雲文如此篇,固退之所當退避, 進學解 不能及也。本東方之體而恢奇淵深過之”。論謝惠連《秋懷詩》,謂“一往清綺而不乏真味”。有論及行文之妙者,如論揚雄《趙充國頌》,謂“百餘字耳,叙致詳贍,可爲後人法戒,所以爲作者”。論班固《西都賦》,謂“’窮泰極侈’四字,《西都》一篇眼目,以下皆發明此句,所以極其眩耀也”。論楊修《 答臨淄侯牋》,謂“參看來書,方見 答牋 筆筆與之針對,有次第,有變化,安頓有法”,論潘岳《笙賦》,而謂“嵇之《琴》、潘之《笙》,二賦發端便成文章,各各排突前人之法”。論陳琳《爲袁紹檄豫州》,而謂“收得竦切有力,亦以彌縫不奉迎天子之謬也”。論謝莊《月賦》,而謂“起借陳王立格,與《雪賦》同局。’端憂多暇’生出一篇大意”。論王延壽《魯靈光殿賦》,謂前幅“初是瞻望,繼而登造,繼而詳觀,層次歷歷”,後幅“就其中之所見詳寫之,先結構,次雕鏤,次圖畫也”。論張衡《東京賦》 ,有謂“句法參差,最易板重處,言之磊落生動,何等筆力”。論揚雄《甘泉賦》,有謂“起局全用長句”。“此段(“於是乘輿”段)叙乘輿初出,尊嚴肅穆,句法亦多奇崛”。論謝靈運《游南亭》,有謂“一’馳’字,全篇三時移易,都已貫注”。論盧諶《覽古詩》,謂“通篇直叙藺生事,而結以’張弛’二字,是何等筆力”。論左思《詠史》,謂“’世胄’一聯,横貫’地勢’一聯上,極經緯相雜之妙”。論潘岳《秋興賦》,謂“只此四語,而不堪當世之想,已見乎詞矣”。何焯論文,突出點有四。一是看重書寫策略和表現藝術的創新。如論張協《詠史詩》,有謂“詠史不過美其事而歌詠之,櫽括本傳,不加藻飾,此正體也。太冲多自攄胸臆,乃又其變”。論謝靈運 《從游京口北固應詔》,有謂“謝家山水之作,可云開闢手。而一種生拗之氣,力變前人,厥功不細”。二是從詩風文風演變趨勢言其意義及影響。如論謝靈運《别范安成詩》,謂“清便婉轉,自成永明以後風氣”。論孔融 《薦禰衡表》,謂“章表多浮,此建安文弊,特其氣猶壯。建安文章,結兩漢之局,開魏晋之派者,此種是也”。三是比較言之。如論袁宏《三國名臣序贊》,謂“ 贊 勝士衡 高祖功臣頌。序亦激昂,晋代之佳者。 贊 雅質勝陸,然陸甚變化”。謂“清便婉轉。此等詩亦復憲章陳王,但比之康樂爲差弱耳”。論潘勖《册魏公九錫文》,謂“大手筆,惟韓退之《平淮西碑》 與之角耳。此篇視《 漢書》 中張竦爲陳崇稱莽功德奏,精力不逮而體之雅潔過之”。四是道其由來以言特色。如論揚雄《長楊賦》,謂“《羽獵》擬 《上林賦》,《長楊》擬 《難蜀父老文》。子雲本祖述相如,其奇則相如所不能籠罩,麗處似天才不逮也”。無疑,何焯論文之識見、涉及之方面、思維之方式,都對劉先生有啓迪作用。
對劉先生評文的認知,既要細讀深思其批語,又要仔細琢磨其於全書所作句讀,和在一些字句旁所作圈點符號的含義。當以前者爲重點。若合全篇評語讀之,不但能讀懂其文,還能領略其妙及其作法之巧。這裏不妨選録先生評點三文的所有文字。
如論曹植《箜篌引》,先生即謂“此詩見子建憂生之思”。而同意何焯所説“久要不可忘,薄終義所尤”句,“此植所望于文帝者也”。而於“久要”句至“磬折”句,批曰:“四句本意正面。”於“驚風”云云,批曰:“以下樂極生悲。”於“知命複何憂”句批曰:“言’何憂’,正憂深語。”又總批曰:“’君子屈身果何求乎’一問,亦自明白。故下文不言明,但歎日月之邁,有屈子’美人遲暮’之感矣。”“子建較子桓詞氣爲温厚,然非乃父英邁雄俊。(王氏)”此評詩之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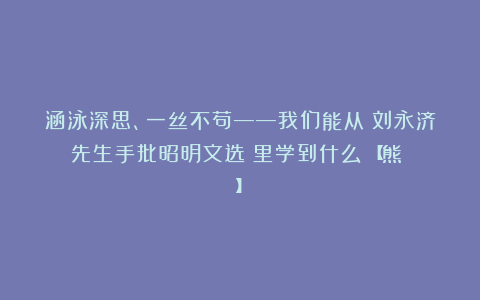
又如論《長門賦》。賦乃後人所擬,非相如作,其詞細麗,先生亦評析入微。先生不但引文獻以言賦之本事,還逐一標出全篇用韻之字。評語始終圍繞“情”作論,説結構層次,謂“初宫怨”,細言則謂“初出人獨處之情”,而於“言我朝往”云云,批曰:“此《離騷》’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之意也。”於“廓獨潛而專精兮”,批曰:“’專精’,望之誠也。”謂“次情望”,細言謂“次寫登臺之無憀”,“分兩小段,登蘭臺一小段,下蘭台一小段”。而於“擠玉户”二句,批曰:“張皋文云:’非寫宫室,乃寫徙倚之情。’然此段皆然,不必此二句。後人宫怨之作,大都此意。李易安所謂’尋尋覓覓’也。”於“日黄昏而望絶兮”,批曰:“’望絶’故悲也。”“次寫宫中夜景,以望幸之意實之。”謂“次琴悲”,細言則謂“’徂清夜於洞房’最悲。清夜自徂,洞房獨處,此所以援琴變調,左右皆悲也。”謂“以下夢遇與夢餘之情”,細言則謂“望不來而夢也”,“夢一小段,夢餘一小段”。而於“夜曼曼其若歲兮”云云,批曰:“雖不來而望無窮時,所謂此恨綿綿也。”又於篇末批曰:“按《日知録》 ’陳後複幸之’云云,正如馬融《長笛賦》 所謂’屈平適樂國、介推還受禄也’。”此評賦之例。
又如論東方朔《答客難》。先生總批曰:“《文心》曰:’托古慰志,疏而有辨。’”而於文中“同胞”,批曰:“觀下文’寡侣少徒,固其宜矣’云云,則此設難之意,蓋指同儔則無有耳。”於“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二句,批曰:“立足甚高。”於“故曰時異事異”句,批曰:“以上對’位卑’,以下對’遺行’。”於“今世之處士”句,批曰:“以下對’無徒’。”(按:“客難東方朔”有“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語)。於“由是觀之”句,批曰:“以下反譏難者。”此評文之例。
從上舉三例可知:先生評文,兼顧内外之美,凡立意、結構、章法、語句皆會言及。不少評語言簡意賅,能於精細處顯大格局,稍事連綴即成一見識卓然、頗能道出文章藝術美感之賞析文字。
大抵先生評文,有幾大習好。一是引《文心雕龍》之言作論。這一點,就認識論而言,與黄侃先生講的“讀《文選》 者,必須於《文心雕龍》所説信受奉行,持觀此書,乃有真解”(《文選平點》)相合,而動輒引用或參用其説,實出於先生長年從事文學著述的習好。如論賈誼《鵩鳥賦》,謂“劉彦和曰:’施及孝惠,迄於文景,經術頗興,而辭人勿用,賈誼抑而鄒 枚沉。’”論枚乘《七發》,謂“枚氏首唱,信獨拔而偉麗矣。”論趙至《與嵇茂齊書》,謂“劉彦和曰:’趙至叙離,乃少年之激切也。仍主紹説。’”論曹植《七啓》,謂“彦和’取美於宏壯’”。論司馬相如《封禪文》,謂“自起至’其詳不可得聞已’,彦和所謂’表權輿也’”。所引《文心》之言,論及作家、作品、文體、文風。而論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竟三引“彦和曰”以道“建安”“晋世”“江左”詩風。
二是概説篇章大義,細言語句涵義。篇章大義,包括文章立意、主旨、寫作意義及各段大意。如論班固《兩都賦》,謂“成王營洛邑,曰’有德昌以興,無德易以亡’。婁敬勸高帝立都關中,曰’被山帶河,四塞之國’,此所以不及成王也。杜篤《論都》,亦以西都表裏山河爲言,其識與敬等。此孟堅之所以知大體、得政要,勝杜萬萬也。文章宏贍,尚其次焉。”又於“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批曰:“二句亦兩篇之旨。”論揚雄《劇秦美新》,謂“子雲蓋習於道家逶蛇順時之義,兼喜與古人争勝,乃以恢詭之意爲斯文以擬相如。豈真諛莽哉!然而遂蒙’莽大夫’之恥於千載之下,此文德之不可不講也。”雖以議論口吻言之,文章立意之高下是非,却清晰可見。又如論所謂蘇李詩,以爲“李詩辭情,尚類二人惜别之作”,蘇詩則“大都泛叙離思”(《 十四朝文學要略》),而於其二“黄鵠一遠别”,批曰:“’一’字與後句’雙’字相關,似客中送客之詞。”論陸機《演連珠》(先生論其意及《連珠》写作範式曾參用黎錦熙之説),五十首皆指明喻意所在,且出語簡明直接。如謂“此喻君當度才授任,臣當度德受官”“此喻賢人不可以牽制招”“此喻忠良之臣不藉威力而敵國服”“此喻世昏則賢愚俱困,時明則短長並用”“此喻虚中方可應物”“情不節則禍足以亡國”云云。至於説段落大意、釋語句之義,其例則不勝枚舉。説段落之意者,如於 《兩都賦序》 “臣竊見海内清平”,批曰:“以上序己所以作賦之意,以下序賦兩都之由。”又於“美哉乎斯詩,義正乎揚雄,事實乎相如”,批曰:“’義正’二語,孟堅自許如此,昭明取冠篇首,亦以其如此也。”説明“義正”二語實就《兩都賦》全文而言。又如論禰衡《鸚鵡賦》,分四段而説其大意,依次謂“以上鸚鵡靈異”,“以上靈異而被羅”,“以上因被羅而傷悼,有思故宇、念骨肉之意”,“以上因傷悼而憔悴,有感恩托命之意”。
説語句大意者,如論《離騷》,於“椒專佞以慢謟兮”二句,批曰:“以’專佞慢謟’斥椒,以’欲充佩幃’斥榝。”論揚雄《劇秦美新》,於“崇嶽渟海”二句,批曰:“’崇嶽渟海,通瀆之神’即泰山梁父設壇場望幸之意,相如但言神望,子雲並言人歸。”論曹植《洛神賦》,於“恨人神之道殊兮”,批曰:“此段明借洛神陳詞以抒己意。’恨人神’以下,語語沉痛,必以陳思獻璫君王指妃,轉嫌板滯。且細察上下文意,亦不爾也。”論《與嵇茂齊書》,於“至若蘭茝傾頓”二句,批曰:“蘭茝、桂林,香草、嘉木以喻君子。”論謝靈運《登池上樓》,於“祁祁傷豳歌”,批曰:“《豳風》:’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此用’祁祁’,亦有不得同歸之意,故傷也。”於“持操豈獨古?無悶征在今”,批曰:“被讒思歸之情,二語盡之。”論揚雄《解嘲》,於“意者玄得無尚白乎”,批曰:“此草玄無用爲嘲。”論蘇武《古詩四首》,於“念子不能歸”,批曰:“’念子’句即《孔雀東南飛》 ’生人作死别’意,亦即杜甫’孰知是死别’句所由來。杜言死别,而以爲生離。”論班固《答賓戲》,於“當此之時搦朽摩鈍,鉛刀皆能一斷”,批曰:“此語頗有感慨。”論顔延之《陶徵士誄》,於“首路同塵,輟途殊軌”,批曰:“字中多少人事!與淵明 擬古 一首參觀可知。”其言篇章語句之意,説法不一。既有直言者,亦有换一説法啓發讀者領會者。此外,先生還喜歡通過道其由來的方式,借前人文意言之。如説一篇意旨,論班固《幽通賦》 ,即謂“ 《幽通》取意於《天問》而構體同《鵩鳥》。《鵩鳥》以黄老之言自慰,此則歸之於儒言”。論曹植《七啓》,謂“子建之作,文體取法《七發》,文意乃從 《招隱》來”。如説段落或語句大意,論張衡《思玄賦》,即謂“’行頗辟而獲志兮’四句,亦《天問》之旨”。謂“’中野’’訪命’”一段,從《幽通》來,亦《天問》之旨也”。謂“此下’天命其明,報應昭晰’,亦 幽通 之旨”。謂“此段(“聘王母於銀台兮”以下)從《 神女》《洛神》 來,亦《楚辭》之旨也”。謂“結歸仁義,亦《幽通》之旨”。
三是評説作家作品風格。關注作家、作品風格或風格特徵,也是先生論文的一大習好。前言引“彦和曰”論文,所謂《答客難》“疏而有辨”,《七啓》 “取美於宏壯”,《與嵇茂齊書》 “激切”;前言引王氏“子建較子桓詞氣爲温厚”,以及引《通鑑》謂嵇康“文辭壯麗”,説《謝靈運石壁精舍還湖中作》“清水出芙蕖”,“所謂風流自賞”,皆屬借他人之言説作家作品風格特徵。自言者,則有論曹操《短歌行》,謂“其雄桀之氣,千古如新矣。詩至武帝能振起其氣,故後人有尚氣之論,但不可以壯健之字句當之耳”。謂揚雄《解嘲》“子雲所處之時遠遜東方,故其言激切而恢詭則不如”。謂顔延之《秋胡詩》 “此首不用憤語而作柔音,深合淑女神情,且愈見其哀,所謂怨而不怒也”。謂張協《七命》 “亦《招隱》之詞也,修詞工細,氣骨不如《七啓》”。謂潘岳《馬汧督誄》“馬以奇功誣死,故此文辭情殊磊砢不平。亦文家因情立體之法也”。 謂《古詩十九首 ·迢迢牽牛星》“此詩言跡近而情疏,愈覺悲涼”。自言作家作品風格,既喜道其由來,又喜比較作論,和引經典語録作論一樣,都能突出所論物件的風格特徵。
四是必説文章作法之妙。文之爲文,作法十分重要。先生嫻於辭章之作,於此深有體會,故論文多説作法。像他説蔡邕 《郭有道碑文》,謂“郭以德業見稱故,但以虚辭敷揚”,謂《楊仲武誄》 “仲武夭折無可説,故叙情特詳,故倍見親切”皆專言其書寫策略。而謂《七啓》“文體取法《七發》”,實兼體裁、寫法而言。謂劉安“《招隱士》蓋從《招魂》出,特幅短耳”,則兼立意、寫法而言。謂《古詩十九首· 今日良宵會》,“此反言若正”。謂《演連珠》第一首“先喻理,後指實”,第二首“先説理,次設喻,後指實”,第三首“(前)四句先理後喻,後(四句)指實”,亦就各首寫法而言。除總言全篇寫法外,先生還愛評説一段、一句之寫法。言段落者,如謂《上林賦》 “於是乎周覽泛觀”一段:“東西略,南北詳,是章法之變。”謂《思玄賦》“彎威狐之拔剌兮”數句:“此段摹寫星象文至奇詭,卻仍是《遠遊》化出。”言句法者,如謂《七命》 “秋蟬之翼,不足擬其薄”句,“從《七啓》 ’蟬翼之割,剖纖析微,累如疊縠,離若散雪’數句來”。謂《思玄賦》“三句一换韻,求變古也”。謂《甘泉賦》 “蚩尤之倫帶干將而秉玉戚兮”,“句法特長,子雲創格,相如亦有此長句法”。謂《思玄賦》“倚招摇、攝提以低徊剹流兮”,“長句又從長卿《大人賦》、子雲《甘泉賦》來”。謂謝靈運《游南亭》 “藥餌情所止,衰疾忽在斯”,“衰疾至此,乃倒句。言衰疾至此,所須惟藥物耳”。又謂王褒《洞簫賦》 “是以蟋蟀蚸蠖,蚑行喘息”云云,“四字句與上文長句分用,一以曼聲,一以促節,文章之變亦類簫聲”。謂“亂辭亦前用曼聲,後以促調”。和説立意、論風格一樣,先生講作法也愛道其由來和比較作論,不同的是説句法、字法,還有直斥其弊者。如説《演連珠》“臣聞沖波安流”一首,謂其“’何則’二句意終晦昧”,又説潘岳《楊荆州誄》,謂其“繼褰,援師不至也。造字太生”言其弊,自能從反面説明用字造句當以何種要求爲準。
讀劉永濟手批《昭明文選》,似有兩點應該注意。一是關於先生對《文選》的認知。當然解决這一問題最直接的研究資料,是先生手批《文選》之句讀、圈點符號和訓詁、評文之文字。還有一點不可忽略,那就是何焯評點《文選》的諸多意見。因爲先生對何説基本上是認可的(有異議者皆已指出),先生有些批語實是對何説的發揮和補充。因而唯有兩者結合,方能較爲全面把握先生的 選 學内涵。二是對先生手批《文選》性質的斷定。其實先生當年評點《文選》 ,並不是爲了弄出一部 選 學專著。從手批《文選》諸多評議文字出現在先生其他著述中(如評李陵《與蘇武詩》,所云“魏晋以來,擬作有四種,一補亡,二效體,三借題,四代作”云云,即寫入《十四朝文學要略》等),可以看出這個手批本原是先生研究八代名篇的讀本,他的手批《文選》,是在爲其文學研究作基礎性的準備工作。鑒於此,我們讀先生之書,似於見識其選學精語的同時,還應認真學習他治學看重文本的精神,和誦讀文章,篇章字句涵泳深思、一絲不苟,以期盡得其妙的方法。
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於武昌南湖山莊梅荷苑
供稿:李艳丽
运营:李艳丽
审核:王重阳
精勤传旧业
豆瓣|@崇文古籍
小红书|@崇文古籍
#artContent h1{font-size:16px;font-weight: 400;}#artContent p img{float:none !important;}#artContent table{width:100% !import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