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尼族杀猪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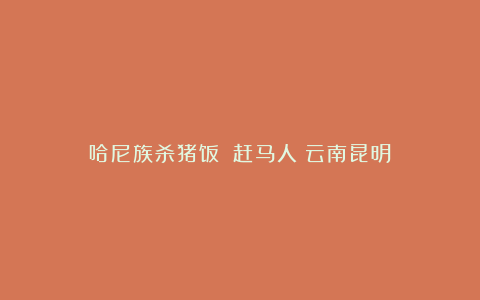
清晨的雾气还未散尽,哈尼山寨的木楞房顶上已飘起袅袅炊烟。我揉着惺忪睡眼跟在阿婆身后,踏着露水往寨子东头走去。今天是波依阿叔家杀年猪的日子,整个寨子都沉浸在节日前般的喜悦里。
刚走近院坝,便听见此起彼伏的喧闹声。三五个壮实汉子正围着石砌的灶台添柴烧水,铁锅里翻腾的水汽与山间晨雾交融成白茫茫一片。院角那棵老核桃树下,几位哈尼阿姐正在清洗芭蕉叶,她们头上的银饰随着动作叮当作响,像山泉敲击青石。阿婆从背篓里取出新酿的玉米酒,郑重地交给系着靛蓝围裙的主家阿妈——这是哈尼人家延续千年的规矩,分享丰收的喜悦要从第一碗酒开始。
“来喽!让开让开!”随着一声吆喝,四个赤膊的哈尼汉子合力将肥壮的年猪抬到松木搭成的杀猪墩上。猪身泛着健康的粉白色,显然是主家精心喂养整年的成果。杀猪师傅是个精瘦的老人,古铜色的臂膀布满细密皱纹。他接过阿婆递来的清水,仔细冲洗猪颈,这是对生命的敬意,也是古老仪式的序章。 当雪亮的尖刀没入脖颈时,早有妇人端来撒了盐的陶盆接住奔涌的热血。鲜红的血珠溅在青石板上,绘出奇异的花纹,波依阿叔见状朗声笑道:“血花开得旺,来年谷满仓!”
最令我惊奇的是褪毛的工序。杀猪师傅在猪蹄处割开小口,用钢筋制成的“挺肠”在皮下细细打通,接着鼓起腮帮往切口吹气。旁边的汉子抡起木槌有节奏地捶打猪身,原本瘫软的猪身渐渐鼓胀如球,在晨光中泛着透明的光泽。后来才知道,这样能让每根猪毛都立起来,褪得干干净净。 如今虽有了气枪代替人工吹气,但寨里的老人仍坚持传统,说只有用人的气息吹胀的猪肉,才带着山野的魂灵。
当白净的猪身被倒挂在木梯上开膛破肚时,院坝里已飘起诱人的香气。新取的猪血与山芋粉拌匀蒸成血肠,嫩滑的里脊肉与野葱爆炒,肥厚的板油炼出清亮的油脂,连最难收拾的大肠也用灶灰搓洗得晶莹透亮。最地道的要数“剁生”——精选的里脊肉与烤猪皮被剁成细茸,拌入野芫荽、小米辣和青柠汁,鲜辣酸香在舌尖炸开,是哈尼人家待客的最高礼遇。
夕阳西下时,长长的篾桌已摆满院落。红烧肘子泛着琥珀光泽,清炖排骨汤飘着菌菇香气,酸菜炒猪血嫩如豆腐,还有用芭蕉叶包裹的粉蒸肉,每道菜都诉说着丰收的喜悦。波依阿叔举起竹筒酒碗:“今年的包谷收成好,猪也肥壮,感谢山水养育之恩!”众人应和着将米酒一饮而尽。火光映照着哈尼人淳朴的笑脸,远处梯田在暮色中泛着粼粼波光,仿佛与这院里的欢声笑语遥相呼应。
离席时,阿婆往我怀里塞了块用红绳系着的五花肉。月光下的哈尼山寨静谧安详,家家屋檐下都挂起了熏制的腊肉。那些在烟火中渐渐金黄的肉条,不仅储藏着一个冬天的滋味,更延续着哈尼人与大山相守的古老契约。这场杀猪饭里,有对生命的敬畏,有对自然的感恩,更有哈尼人家如红河水般奔流不息的温暖情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