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头题字:聆百
未了琴音绕碧堂,
水绘园里寻宛、疆
文/云间方圆
十年前访水绘园时,五十元的门票像道浅浅的门槛,将尘世的喧嚣稍稍挡在园外。如今再至,朱漆园门早已向世人敞开怀抱,免费入园的欣喜还未在心底漾开,便被门侧那尊冒巢民雕像牵住了目光。他长衫微拂,眉眼间带着几分温润的书卷气,倒像位等了三百年(见文后注)的老友,见了来人便要拱手道一句“久违”。
脚下的石板巷是被岁月磨透了的,青灰色的石面上泛着玉般的柔光,像是无数双布鞋、草鞋、锦靴反复摩挲,才揉出这般温润。巷口的晨光斜斜切进来,恰好落在“水绘园”三个字的匾额上。匾额边角的漆皮早已斑驳,露出底下深浅不一的木纹,倒像是时光用指尖写就的诗行,被这缕阳光轻轻拆开,成了封迟到三百年的信,字里行间都是潮湿的期待。
刚迈过门槛,水意便抢先一步漫了过来。不是江南梅雨季那种黏腻的潮,而是清清爽爽的、带着草木气的湿润,比廊下初绽的茉莉更早地钻进鼻腔。一泓曲水绕着园子蜿蜒,把整座园林折成一枚通透的玉佩,回廊是玉佩上盘绕的纹,小桥是缀着的玉扣,石矶则是不经意间磕出的小缺口,反倒添了几分生动。岸边的柳丝垂得低,发梢直蘸着水面,像是董小宛当年临池梳妆时,不慎滑落的一缕青丝,在碧波上写下淡墨般的絮语。偶有白鹭掠过,翅尖扫过水面,惊起一圈圈涟漪,倒像是给这幅水墨画落了个灵动的款。
行囊里揣着的《影梅庵忆语》影印本,纸页边缘已经微微发卷。这是冒辟疆暮年写就的回忆录,字字句句都浸着对董小宛的念想,读起来总觉得纸页间飘着淡淡的梅花香,混着一丝若有若无的药气——毕竟小宛当年为照顾病中的冒辟疆,自己也耗损了元气。书页里夹着片去年从园里拾的荷瓣,早已干成了浅褐色,倒像是从那段岁月里剥下的一小块时光。
顺着回廊往北走,寒碧堂的飞檐先探了出来。堂前的荷塘里,残荷还支棱着枯瘦的茎秆,褐色的莲蓬垂着头,像被时光钉在水面上的铜钉,透着股沉郁的古意。推开门时,木轴发出“吱呀”一声长叹,惊得梁上积着的细尘簌簌落下,在斜射的阳光里跳着细碎的舞。
堂内空阔得很,中央摆着张案几,案上的砚台里还凝着半池宿墨,旁边横卧着一具古琴。导游曾说,这琴的弦是按董小宛当年的法子做的——开春时采的春茧,抽丝时掺了梅蕊上的雪水,晾弦的日子必得选在晴和的春日,让弦丝里渗进些暖阳的味道。我伸出手,指尖还没触到琴弦,穿堂风先一步掠了过去,琴弦轻轻震颤,发出一声极轻的嗡鸣,像是三百年前有人在耳边低唤了一声。
恍惚间,案几旁竟坐了人。青衫的冒辟疆正捧着书卷,侧脸在窗棂漏下的光斑里忽明忽暗,读到会心处,指尖会轻轻在膝头叩着节拍。对面的董小宛刚理完鬓发,正伸手调弦,银簪在烛光里闪着细碎的光。她拨弦的动作极轻,《平沙落雁》的调子便漫了开来,像堂外的流水般悠悠淌着。烛火在墙上投下两人的影子,冒辟疆的影子微微前倾,小宛的影子则侧着头,发丝的影子与他的衣袂交缠在一起,倒比真人更显得亲密。
忽然一声脆响,是檐角的铜铃被风吹得相撞。影子倏地散了,堂内只剩我一人,案几上不知何时多了粒干涸的胭脂,红得像褪尽了血色的桃花。翻开《影梅庵忆语》,恰好翻到“小宛每鼓《潇湘水云》,余辄倚竹而听,至“水云深处”,弦忽咽绝,相顾无言,唯泪千行”。窗外的风正穿过竹林,竹叶簌簌作响,倒像是把当年的琴声藏在了里面,只是再也无人与我共听这弦外之音,更无人在水云深处与我相对垂泪了。
从寒碧堂出来,沿着九曲桥往西北走,壹默斋就藏在一片芭蕉叶后。这斋子小得很,刚够摆下一张榻、一张几,倒像是特意为两个人量身打造的。窗棂外的修竹斜斜探进来,把影子投在素白的粉墙上,风一吹,竹影便轻轻摇曳,像是有人在墙上写着无声的诗。
冒辟疆在《影梅庵忆语》里写过,当年他在此读书,小宛便坐在对面烹茶。“余读书倦,则共论才语,杂以诙谐”,茶烟袅袅里,两人说的或许是《离骚》里的香草,或许是园子里新绽的荷花,又或许只是打趣对方鬓角沾了的墨渍。我在榻边坐下,从行囊里取出便携的茶具,学着书里写的法子:用前日收的雨水养着碧螺春,炭炉里的银炭燃得正旺,水沸时发出“噗噗”的轻响,像极了小宛当年说的“蟹眼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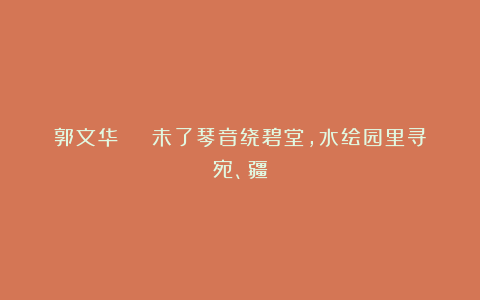
茶香刚漫开,窗棂外“嗒”地落下来点什么。低头看时,是朵早桂,嫩黄的花瓣上还沾着晨露,恰好落在摊开的书页上,正压着“案头瓶花,经小宛手,辄异寻常”那句。指尖轻轻捻起花瓣,一股清冽的香气倏地漫开来——这香气,该是和三百年前冒辟疆闻到的一模一样吧?他当年伏案疾书时,会不会也有这样一朵桂花,不偏不倚落在小宛研墨的腕边?
斋里的案几上摆着个青瓷笔洗,里面盛着半汪清水,水面上漂着片玉兰花瓣。我把那朵桂花放进去,花瓣打着旋儿在水面游移,倒像是两个朝代的花在悄悄对话。墙上有后人题的“当时只道是寻常”,墨迹已经淡了,却恰好应了此刻的心境。冒辟疆写《影梅庵忆语》时,会不会常在这斋里独坐?想起当年小宛为他研墨时“腕底春云散”的模样,想起两人在茶烟里说的那些琐碎闲话,才惊觉最寻常的日子,原是最该珍惜的时光。
暮色漫上来时,我走到了水明楼。这楼是在寒碧楼遗址上重建的,临水的窗棂像被裁开的画框,框着对岸的柳色与天光。楼里的琴台擦得锃亮,台上摆着只紫檀木锦盒,盒盖半掩着,里面空荡荡的,只余一缕若有若无的檀香。导游说,小宛当年弹完琴,总爱把绣着梅花的手帕覆在琴上,一来是防着落尘,二来是让琴身沾些淡淡的香气。如今手帕早已化作尘泥,倒把这檀香的味道浸进了木头里,三百年也没散去。
倚着栏杆往下看,水里的楼影比岸上的更清晰,连飞檐上的走兽都分毫不差。云影掠过水面,楼影便轻轻摇晃,倒像是整座楼在水里慢慢舒展。我忽然想起《影梅庵忆语》里那句“月下泛舟,小宛弹《梅花三弄》,余吹箫和之”,便忍不住伸手抚上琴台。指腹下的木纹凹凸不平,像是把当年的琴音刻进了木头里。
若是此刻弹起《梅花三弄》,那音波会不会顺着水面荡开,穿过三百年的月光,惊起当年那艘画舫的影子?会不会看见冒辟疆披着件月白披风,箫管斜倚在肩头,而小宛正低头调弦,鬓边的珍珠随着船身轻轻摇晃?可终究是没敢弹——这园子里的琴音,原是只属于他们两人的,旁人怎好随意打扰。
从锦盒里取出早上拾的那瓣桂花,轻轻放在琴台上。桂香混着檀香漫开来,倒像是给这段未完的故事添了个温柔的注脚。太阳已经沉到了远处的屋脊后,金红色的余晖把水明楼的影子拉得很长,一直浸到水里,和楼影叠在一处,分不清哪是现在,哪是从前。
园门外的市声渐渐涌了进来,是小贩的吆喝,是自行车的铃铛,是晚归人的谈笑声,把园子里的静谧戳了个小小的洞。回头望时,寒碧堂的窗棂里已经亮起了灯,昏黄的光晕透过雕花木窗,在地上投下细碎的花影,倒像是当年冒董二人未熄的烛火。
合上《影梅庵忆语》时,才发现最后一页的空白处,不知何时落了片柳叶,叶脉清晰得像谁写的小字。风从书页间溜过,带着股湿润的荷香,恍惚间竟像是有人在耳边轻语——原是这水绘园里的每滴水、每片叶、每缕风,都在替那对有情人,续写着未完的《影梅庵忆语》。
走出巷口时,身后的园门正缓缓关上,“吱呀”一声,像极了书页合拢的轻响。这园子其实不大,却装下了冒辟疆与董小宛的一生:寒碧堂的琴音里有他们的相顾无言,壹默斋的茶烟里有他们的寻常日子,水明楼的月影里有他们的泛舟时光。而我们这些后来者,不过是循着琴音、循着茶香、循着月光,来赴一场三百年前的约会。
石板巷的尽头,卖桂花糕的阿婆正收拾摊子,竹篮里剩下的几块糕冒着热气,甜香漫过来,竟和水明楼里的桂香一模一样。原来有些味道,有些记忆,从来都不会真的消失——它们只是藏在某个角落,等一个懂的人,再来轻轻唤醒。
注:“水绘园始建于明朝万历年间(1573 – 1620年),距今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但文中重点并非单纯介绍水绘园的建筑历史,而是围绕冒辟疆和董小宛的爱情故事展开,所以“三百年”更多是服务于爱情故事的时间纵深感,而非精确对应水绘园的存世时长。”
郭文华,男,中共党员,江苏省如皋市九华镇人。江阴市作家协会会员。自幼喜欢文字,在《澄西船舶》《方舟》《江南晚报》《如皋日报》以及各大平台上发表过作品。个人专辑有:《文华录》《文华散文集》《送你一条江南的雨巷》《文华闲笔》《苦难岁月》等。
名誉顾问 | 盛春红
顾 问 | 曹桂明
总 编 | 王 慧
特约作家 | 冒芝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