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那天早上,桦甸的风一阵紧似一阵。
张凤河把褡裢往背上一勒,脚下没停。
他走得很快,像是后面有人追,又像前面有事等着。
其实,他也就是赶路。
但这趟路不一般。
他是打算离开老家,去公主岭的日本租界投奔亲戚。
这事儿年前就定了,只是没想到,刚出村没多久,就先遇上了点麻烦。
事情发生在1923年2月18号,民国十二年。
那时候,吉林省吉长道一带,治安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
只是没人指望政府能管得了山林里的事。
光桦甸周边,打小就有胡子出没,谁都知道。
可真碰上了,还是心里一紧。
那天他穿了件黑土布夹袄,前几天还冻得出门都费劲,这天一暖和,反倒开始出汗,脑门子上水刚冒出来,就被风一吹,痒得直想抠。
可张凤河没空管这个。
他心里惦记的是褡裢里的九百二十块现大洋。
这钱,是他把家里两晌地卖了换来的。
宁可不要奉票,张凤河说,现洋踏实。
可谁知道,刚到大道上,马蹄声就从远处响起来。
五匹马,不紧不慢,像是随便溜达。
但骑马的人,一看就不是好惹的。
有人腰插盒子炮,有人背着长响子,全都盯着他背上的褡裢。
说实话,张凤河也不是没准备。
他怀里别着一把小左轮。
但他没动。
对面那几个人的枪,可比他的玩意儿厉害多了。
他要真掏枪,那就是找死。
可他也没慌。
右手握住左手腕,往左胯一放,嘴里就吐出一句:“西北悬天一枝花,天下绿林是一家。”
胡子听了这句,眼神立刻就不一样了。
这不是普通老百姓说得出来的话。
那是“里码人”的盘道切口。
对上了,就说明不是外人。
为首那人一勒马,跳下来:“辛苦,辛苦!是朋友?”
张凤河接着说:“是朋友!人不亲,枪把子还亲呢;枪把子不亲,山头还亲呢。”
只这几句,气氛就变了。
两边原本剑拔弩张,现在倒像老朋友见面。
可这真的是巧合吗?
其实不然。
张凤河年轻那阵子,确实在“山头”混过。
那会儿他跟着一个叫“东来顺”的小绺子,跑腿、传信,干过一阵子“递信柱”。
后来年纪大了,回了村,种地娶妻,过普通日子。
但那几年学的黑话、行规,他一直没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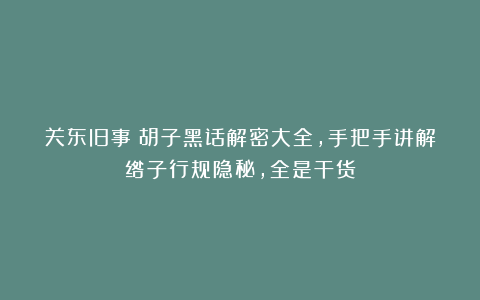
这次出门,他也不是没想过可能会遇胡子。
只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那时候的东北,说句不好听的,胡子比老鼠还多。
不是说他们天生就是坏人,而是那时候人活不下去。
清末民初,战乱不断,土地兼并严重,不少人连口饭都吃不上。
有人上山当胡子,也有人走江湖混口饭。
谁也不想一辈子做土匪,可谁又真能选?
胡子讲规矩。
也讲黑话。
他们自称“局”,有大掌柜、四梁八柱,有花亭子和递信柱。
说话讲究切口,做事有行规。
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乱来。
比方说,赶大车的师傅走道上要是碰上胡子,先得下车,把帽子倒扣在马背上,再从左边车辕上去,右边跳下来,抱拳一举:“达摩老祖威武!”这套动作,是告诉人家:我没藏枪,别紧张,大家都是江湖人。
再比如,胡子要进村,头一件事是“看皮子”,也就是看狗。
然后得弄明白村里谁说了算。
说得对,吃顿饭,休息一晚就走;说不对,轻则挨打,重则“插人”。
这年头,普通百姓也得学点黑话。
不是为了吓唬谁,而是为了保命。
有个老头,腊月时候赶集,背着一扇猪肉回家。
半路遇上胡子,胡子看他胡子上都是冰,说:“这老元良,五柳子全是亮清,也不顺一顺。”老头机灵,说:“冰得住一时,冰不住一世,胡子才是长长久久的!”“冰”与“兵”同音,这一句说得好,胡子高兴了,连猪肉都没抢,还送了他顶狐狸皮帽子。
这些事儿听着可能像段子,但在那时候,是真事。
东北的绺子,不是一个两个。
大的上万人,小的几个人就能成局。
流寇、山林、半正规化的地方武装,全都有。
他们不光抢富户,也抢普通人。
可只要你会说话,懂规矩,往往就能平安脱身。
张凤河就是这样。
他知道该说什么,怎么说。
“串串叶子”不是聊植物,是要你脱衣服换他们的。“干净媳妇”不是找女人,是要笤帚刷马。“锅盖”不是锅盖,是马鞍子。“干枝子”不是柴,是粉条子。
不懂这些,轻则挨一顿“摔手子”,重则命都保不住。
可张凤河懂。
他能对上话,也能接得下去。
连对方问他拜哪个“花亭子”,他都能顺着说出“传号递信,联局扯旗子曾打伊通”。
这可不是随口胡说的,得知道规矩、懂来历、熟门道才行。
那几位胡子听了,心里明白了:这人,咱不能动。
也许曾是兄弟,也可能有靠山,反正不是随便能惹的。
最后,什么也没发生。
张凤河背着褡裢走了。
他的钱没丢,命也没丢。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这样叫过他。
参考资料:
王树增,《1911:辛亥革命纪实》,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
李国文,《东北抗联纪实》,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
侯宜杰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资料选辑》,中华书局,1992年。
孙立川,《黑话词典:中国旧社会秘密语言释义》,商务印书馆,1991年。
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吉林省志·社会治安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