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竹终章:生于卢龙,葬于建昌,
一部跨越时空的归葬史诗
文‖计鹏
辽宁建昌东大杖子战国古墓群,其墓主身份至今成谜。将其与古孤竹国相联系虽仍属推测,但从时间、地理、葬制等多重证据来看,这或许正是一段被尘封的真实历史。
东大杖子古墓群的埋葬历史可追溯至战国中早期,并一直延续到战国晚期,历经两百余年。考古学上可以肯定,墓主人是深受燕文化影响的辽西土著。然而,在大凌河流域上游地区,并未发现与东大杖子墓葬规模相匹配的聚落遗址,因此基本可以判断,墓主人生前应居住于区域之外。有观点认为,东大杖子墓群属于某一支游牧民族,因而没有固定聚落;但在考古学上,很难解释一个居无定所的族群,却会拥有如此集中、延续数百年的固定祖茔。
建昌县东大杖子村航拍图
一、孤竹国灭亡之后的归葬传统
据史书记载,公元前664年,齐燕联军攻破孤竹国,孤竹遂亡。关于孤竹国的都城位置与疆域范围,学界至今众说纷纭,至于其亡国后的去向,更是迷雾重重。
《尚书大传》有云:“古者诸侯始受封,必有采地:百里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诸侯以十五里。其后子孙虽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子孙贤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谓兴灭国,继绝世”。商汤灭夏封大禹后人于杞,武王灭商封商纣后人于邶,包括齐桓公立僖公以存鲁,城夷仪以存邢,城楚丘以存卫等都是“兴灭国,继绝世”的具体表现。
因此,齐桓公在击败孤竹国后,为消除北方边患,很可能继续遵循’兴灭继絶’的古义,存其宗祀、迁其君族至卢龙,并降爵为“子”、“男”或者“附庸”,使其以燕国附属形式继续存续。即便如此,孤竹国以“继绝世”的合法身份,仍可保留一定的礼制传统与政治尊严。
在此背景下,孤竹的国君与贵族去世后,极有可能仍恪守’归葬’传统,即返葬于辽西封地。《史记·管蔡世家》中就有“悼公死于宋,归葬”的记载,说明“归葬”是周代贵族重要的礼俗之一。
从地理上看,东大杖子已属辽西故土,地势平坦,土地肥沃,背倚月牙山,面临凌河水,不仅符合“背山面水”的择葬标准,而且距离孤竹新址相对最近,具备作为归葬之地的理想条件。
从时间上看,东大杖子墓群的建造史,上应孤竹国“灭亡”之后,下附燕国濒亡之前,跨度正与笔者所推测的“孤竹以燕国附庸身份延续至燕王喜时代”基本吻合。
迁徙与归葬的闭环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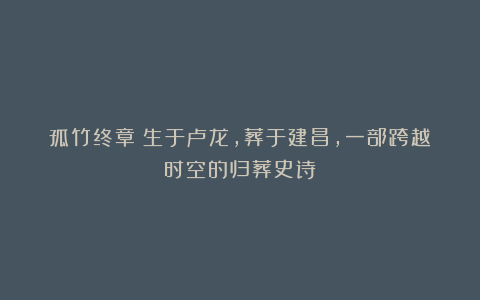
二、“五牲俱全”与“七鼎六簋”的礼制密码
据考古报告,东大杖子古墓群中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是一座“填土墓”。墓中不仅发现“五牲俱全”,即殉葬有牛、羊、猪、狗、鸡五种祭牲,还出土了“七鼎六簋”的礼器组合——这显然是诸侯级别的葬制。
“五牲”也称“五畜”,在古代祭祀与墓葬中象征祭品齐备,是高级贵族葬礼的体现。而“七鼎六簋”是周代礼乐制度中诸侯等级的配置:鼎盛肉食,簋盛黍稷,鼎簋搭配使用,数量直接标识墓主人生前的政治身份。值得注意的是,东大杖子所出并非铜器,而是陶仿铜器。这或许说明,墓主人仍享有象征性的诸侯名分,却已失去与之匹配的国力与财力。
因此,我们可合理推测,这座高等级“填土墓”的主人,很可能就是孤竹国被迁往冀东之后,首位去世并归葬故土的君主。史书并未记载孤竹“亡国”时,其君主是被杀还是投降,但可以确定的是,其爵位必遭贬降。东大杖子这座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墓葬,或许正是这位失国后仍保留名义爵位的孤竹君之最终归宿。
周代殡葬礼制
三、国力式微与墓地的最终停建
进入战国晚期,燕国在秦国的压迫下国力日衰,疆土不断萎缩。作为其附庸,孤竹国很可能被不断征调兵源与物资,实力持续削弱,逐渐沦为一方地主。加之数百年过去,后代对故土的认同感逐渐淡化,“归葬”所需的人力、财力与政治意志也难以为继。
随着战国末年的动荡加剧,列国兼并进入白热化,辽西地区亦成为燕、胡交错争夺之地。交通阻隔、国力枯竭,使得延续两百余年的归葬传统被迫中断。至战国晚期,东大杖子这片墓地再无新墓入葬,一段“归葬”的历史就此定格。正是这段历史变迁的沉默见证——它或许标志着孤竹作为一个政治与文化实体的最终消散。
归葬
四、结语:一段被黄土掩埋的归葬史
东大杖子古墓群,如同一部埋藏于地下的无字史书,以其独特的葬制、延续的时序与空白的聚落反差,默默指向一个失去故国的族群——孤竹。他们或许在政治上被迫远离辽西,却在文化记忆与葬俗中执着地回归。墓中的“七鼎六簋”,虽已降为陶质,却仍是其不灭身份意识的最后宣誓。
历史的真相或许仍待更多考古发现来证实,但东大杖子墓群所提示的,正是一段关于“归葬”的执着传统,一个关于“孤竹遗民”的悲壮故事。最终,这部写于黄土之下的史诗,成为了在时代洪流中挣扎求存的所有小国命运的共同缩影。
建昌县东大杖子村鸟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