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第一作者聂鑫教授
摘要
“董事”一词并非外来,而是中国传统古典词。晚清以降,在公司制度引入的背景下,经历了“官督商办”“绅领商办”以及《公司律》颁行后的三个阶段,“董事”的词义扩大,在指代传统民间主事者的同时,也逐渐具有现代公司治理角色的新含义。结合公司理论,早期公司治理结构映照了相应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近代中国公司董事的产生方式、职权结构和议事机制深受传统地方事务基层治理机制“绅董制”影响,呈现出强烈的本土色彩。与代议制国家中由股东选举、集体决策、履行监督职能的董事会不同,近代中国公司董事在形式上虽然贴近现代公司制度,实则往往由推举或委任方式产生,依赖个体决策,合议性与独立性相对有限,是传统治理逻辑的延续。传统“董事”因与现代公司董事一职的功能相仿,而被借以阐释新意,但时人忽略了二者设置目的和运作逻辑的本质不同,导致公司董事制度在本土化过程中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近代公司“董事”概念的形成过程揭示了在法律移植过程中,需考虑到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政治背景,才能将外来概念真正转化为有效的法律资源。
关键词
“董事”;近代公司;“绅董制”;代议制;法律移植
在现今社会,“董事”一词并不算陌生,“董事”最常指涉的是现代公司董事会的成员,我国现行《公司法》规定董事由股东会选举产生,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当下,在论及我国公司治理时,董事会中心主义与股东会中心主义理论之争、董事义务的标准和范围、董事责任的界定等议题无疑是学界讨论的热点,而董事会职权与责任的失衡问题却仍未得到妥善解决,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中国的董事会制度依然处在法律移植与本土化改造的探索过程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探水须探源,制度总是根植在历史文化的土壤里,梳理相关概念可以使制度更加明晰。陈寅恪曾言:“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此语揭示了一种由字/词观察历史的取径方式,成为后代学人的治史追求。晚清时节,中国面临“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西方的思想、制度传入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由古向今的转化进程。冯天瑜先生认为,对在处于古今—中外坐标系间(近代)的词语进行意义考析,不仅上承训诂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传统,而且通过追索词汇的生成、演变历程,可以进入“历史文化时空”,把握词汇概念的真实样貌,从而对相关的制度有更深刻的理解。
因此,我们不妨回到公司“董事”概念形成之初追溯发问:“董事”这一概念是否完全是一件舶来品?晚清的志士仁人在学习、移植公司制度时,对“董事”有怎样的认知?近代中国的公司董事会制度在建立初期是否受到了当时政治制度的影响?其在进行本土化整合时又遇到了什么阻碍?本文希冀借助古籍、近代报刊、档案等历史文献,结合政治理论和翻译理论,通过梳理近代公司“董事”概念的形成过程,并与西方公司制度相比较,尝试回答上面这些问题。
冯天瑜、聂长顺著《三十个关键词的文化史》
一、“董事”词义探源
与“干部”“书记”之类的外来词不同,“董事”实际上是一个汉语古典词,自宋代成词以来,一直保持相对固定的含义。晚清时节,受到西方制度的影响,“董事”一词又汲纳了新含义,在本土意涵与外来概念相互格义的过程中,其指涉对象愈益复杂。因此,若要探究中国近代公司“董事”概念的形成,有必要先行考释本土“董事”词义,方能准确辨析其在不同语境中的概念所指。
王先谦撰《尚书孔传参正》
(一)源起:词组“董事”的产生
从其结构来看,“董事”是由“董”与“事”组成的词,词义的重点在“董”字上。“董”字最初的用法有两个:一为“监督、监察”,一为“督正、纠正”。“监督、监察”的用法出自《尚书·大禹谟》,《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俾勿坏。”孔安国将“董”字训为“督”。《左传·文公七年》引《夏书》作“董之用威”句,杜预注为:“董,督也,有罪,则督之以威刑。”又如《左传·昭公十三年》:“董之以武师。”《后汉书·陈忠传》:“入则参对而议政事,出则监察而董是非”等,均为此用法;“督正、纠正”用法见于《尚书·周官》:“归于宗周,董正治官。”《尔雅·释诂》中云:“董,督,正也。”又如《后汉书·岑晊传》载:“虽在闾里,慨然有董正天下之志。”
及至两晋,“董”字又引申出“督统、统率”的含义,如《三国志·吴书》载:“祎体质方刚,器干强固,董率之才,鲁肃不过。”西晋陆机所撰《汉高祖功臣颂》有云:“肃肃荆王,董我三军。”
宋代以降,“董”字逐渐衍生出“主管、主持、负责”的意思,并且开始与“事”字结合组成词组。此时最常见的用法是“董其事”,“其”为代词,代指前文所述的工作内容,意为主持、主管某事。兹举史籍数例以为证:《续资治通鉴长编·太宗》有“殿前都指挥使杨信初董其事,上以信病瘖不能言,命天武左厢都指挥使崔翰代之”。《宋史》有“愿诏得一改造新历,委官专董其事”。《金史》有“县官兼董其事”。《元史》有“设官吏掌钥者三十二人,仍以宦者二十二人董其事”。《明史》有“崇祯中,议用西洋新法,命阁臣徐光启、光禄卿李天经先后董其事,成《历书》一百三十余卷”。《清史稿》有“世宗于滦、蓟创营田,设营田水利府,命怡亲王董其事”。“董事”合用的情况最早也出现在宋代,如宋人所著《唐会要》:“夫设官分职,董事置吏,得人则天下自治。”这里的“董事”省略了中间的代词“其”,但仍是一个动宾短语,还未单独成为一个名词。
王溥撰《唐会要》
(二)演进:表述职位的名词“董事”
明清以来,“董事”逐渐演进成一个用于表述职位的名词,意为主管、主事者。“董事者,必择公正绅衿、身家殷实者为之。遇有公事,与地方官分庭抗礼,其名至重,其位极尊”。董事作为民间组织或公共事务的管理人、主事者,其职责主要为统管事务、做出决策以及管理经费账目。以下试举书院董事、善堂董事及商业行会董事三例说明之:
1.书院董事
中国古代书院是官府整理典籍和私人治学教书的机构。清朝时,书院已遍布全国大部分地区,数量达7 000所以上。明清书院行政由山长统摄,下设监院、总办、掌管、董事等职,其中董事亦可被称为院董、董理、首事、绅董等,各个书院按人数多寡可设置二至三十人的董事职位,任期三至五年不等。“书院一切经理,无不责成董事,必须选派得人”。清代书院董事一般由选派推举而来,如广州应元书院董事由监院分派,梯云书院董事由各乡生童公举而来。“正途端方”“公正殷实”“秉公执正”“小心谨慎”是董事的基本要求。董事的职责主要在于选聘山长,管理院务、开支和学规稽查,书院还会根据管理事项的不同分别设置董事职位,如云门书院董事“分监院、营造、催租、收存、支发,各司其事”。总的来看,筹措、管理经费是书院董事的主要职责之一,董事或自行捐款,或向地方士绅大户劝捐,或经营学田、置地、收租等充作书院经费,并且负责将书院经费发商生息。
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学规集成》
2.善堂董事
明清时期,各类善会、善堂、育婴堂等慈善组织在各地都市成立,其主要的管理制度是由宋代社仓制度演变而来的“董事制”。善堂董事人数不等,任期一般为三年,通常由绅士公举端廉殷实之人担任。之所以需要推举家境殷实之人作为善堂董事,是因为董事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管理善堂的资金。董事们不仅需要四处劝捐解决经费问题,还要经营田房产,如有必要还需董事垫付银钱,因此身家殷实的董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不侵吞公款。如扬州同善堂“(经费)用不敷,则董事捐输,以补其乏。”又如嘉庆朝嘉定县育婴堂董事充任条件为“捐银五十两,以裕经费。每岁每人捐银十二两”,是为“捐资襄事”。
3.商业行会董事
明清时涌现的商人组织同样存在董事制度,尤其是在同业行会、公所中,主事者大多为董事(或称为“行董”“商董”等)。商业行会的董事亦由推举而来,一般由行会成员公推人品端方、德高望重的人士充任,任期“三年一换,以防日久生变。”行会董事职责为收取会费(捐款)、管理账目、调解矛盾、制订行业章程以及开展慈善事务等,管理账目一事还要接受众会员监督,如徽商木业公所董事每年六月朔日需集结众商,在朱子神前祭拜,然后查核账目,任期届满时董事也需要“先行邀集众商交明账据,洁身而退”。行会董事制定的章程既包括行业规定(工资、市价、行业标准等),又包括纠纷解决方式(行业内调解或送官),最后还负责将这些章程规定刊刻在石碑上,主动向官备案,以供众商参览。
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
二、本土“董事”的成熟:绅董与绅董治理机制
19世纪管理工作的激增,打乱了官僚制国家地方治理旧制的平衡。董事逐渐走出民间组织的行政架构,开始与官方接轨,协助官府进行地方公共事务的治理,清代乾嘉朝保甲制度设有“董事”一职,即可视为开端:“乡设一局,以绅衿一人总理,士夫数人辅之,谓之董事……董事民间所自举,不为官役,又皆绅士,可以接见官府,胥吏虽欲扰之不可得矣。”咸同年间太平天国叛乱,各地筹办团练活动,团练亦设董事一职,负责协助官府倡办、劝募捐输,动员社会力量并解决经费问题。
这些协助官府办理公共事务的董事往往由地方绅士充任,手握实权,但无官职,没有品级,是谓“绅董”。“书院有绅董也,善堂有绅董也,积谷有绅董也,保甲有绅董也,团练有绅董也。或一董总理数事,或各董共理一事。虽各处公事不同,而皆足代官分理则一也”。咸同以来,绅董活跃在地方各个领域中,积极操持大小事宜,向上承接各级官府的指示,向下对接基层民众的需求,可谓能“通上下之情”。他们能够履行政府无法履行的职能,“地方公事,往往官所不能了者,绅董足以了之;官所不能劝者,绅董足以劝之”。绅董常常参与到地方事务的决策和管理过程中,平衡官民之间的关系,如同治年间绅董开始独立管理水利工程,若民力不支,绅董会主动环请缓办,知县也会召集绅董征求意见。久而久之,绅董既替官府襄理事务、向官府传达民情,又与官府分庭抗礼,因而在当地拥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具有比普通绅士更高的身份地位,享有更多的法律特权。
此前关于绅董的研究常被纳入“士绅研究”和“地方精英研究”范畴内,视为“士绅”的同义词,然而二者实际上并不能完全画等号。伊懋可(Mark Elvin)最先提出绅董是士绅群体中尤为特别的存在,他们是地方绅士中资历较深的人,不一定有功名,但以专业组织者的身份拥有相当大的权力。王先明经过考察后也认为既往的研究大多受限于社会阶层视野,他提到实际上虽然具有功名身份的绅士人数众多,但并非所有绅士都能够参与地方公共事务管理,“只有被推举(或选举)为地方各级或各项事务的总董、董事者,才能真正成为地方社会事务的掌管者”。易言之,绅董应当是士绅范围内更精英的群体,他们切实地参与了清代地方公共事务,能够行使瞿同祖所说的“非正式权力”。
张仲礼著《中国绅士研究》
绅董的“非正式权力”并非由官府直接赋予,而是绅董在协助地方事务治理的过程中逐渐拓展出的一个权力空间。孔飞力(Philip A. Kuhn)认为这一非正式的权力空间是对“官治”的补充,仍然在“官治”的统辖范围内,即便如此,绅董凭借这些权力已经足够在地方事务中大显身手:在善会善堂,绅董借助官方权威解决内部矛盾,扩大募捐规模,获取非正式的行政权推进地方的慈善事业;在团练活动中,因为团练“与其说是作战单位,不如说是行政单位”“一切经费均由绅民量力筹办,不得假手吏役”,所以地方厘金、亩捐等税款的征收工作均由绅董办理,绅董进而逐步获得地方非正式的财政权;在商业会馆,绅董负责制定行业章程,调停商业矛盾,代替衙门进行商事审判,拥有非正式的司法审判权;绅董还在各公共行业领域负责人事选聘,如选拔书院山长、善堂司事、义仓仓长等,实质上获得了非正式的地方人事权。
由于绅董深度参与了地方事务,地方治理架构因而逐渐形成稳定的、贯穿市场结构和区域界限的“官府—绅董—民众”社会网络结构。绅董“非官而近官,非民而近民”,既代替民众直面国家,又代表官府直面社会,民众或许不知有“国家”,不知有“中央”,但一定知道绅董是权威的象征,他们才是民众眼中“做主的人”。“是绅董者,介乎官与民之间,所以沟通地方之群情,巩固地方之团体,不失为地方政治上之以机关者也”。由是,清代的地方治理机制发生转变,从“国初以来,例不用绅”到“权在绅而不在官”,绅董治理机制迅速普及到大多数地区,关涉民众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着民众百姓的观念和行事方式,成为晚清中国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孔飞力著《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
三、近代公司“董事”概念的形成
中国的公司董事是清代咸同朝以后才出现的新职业身份。咸同朝以前,中国尚无本土公司,彼时“公司”是英国东印度公司(EIC)的专用名称。中国本土的传统商行组织形式各异,与西方的公司形式差距较大,直至19世纪70年代,才出现了第一批模仿西式公司的新式企业。晚清公司按照不同阶段可以大致分为三种模式:“官督商办”模式、“绅领商办”模式及《公司律》颁定后的公司模式,中国近代公司董事的概念便是依托公司的发展而逐步形成的。若要探寻近代“公司董事”概念的形成过程,其与传统董事的联系及区别,便需着眼“董事”在不同阶段下以及不同模式公司中的具体产生方式、职责与义务。
(一)“官督商办”公司中的董事:以轮船招商局为例
“鸦片战争的真意义,就是用火与剑的形式,告诉中国人的使命:中国必须近代化,顺合世界的潮流”。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陷入内忧外患境地的清政府开展了洋务运动,在引进西方技术设备的同时也尝试通过借鉴西方的公司组织制度打造中国的现代工商业,一批新式企业应运而生,其中1872年在沪成立的轮船招商局最具代表性。
作为第一家华商股份制公司,轮船招商局采取的经营体制是“官督商办”模式,公司各项事宜均由官府主导,“各商所有轮船资本,必渐归并官局”。不过当时的清政府由于没有充分的启动资金,便派盛宣怀联络朱其昂奔走集股,最终以官本制钱二十万串(合银十三万五千两)、李鸿章出资五万两、郁熙绳入股一万两、各商认股十余万两作为资本正式开局。
上海市档案馆编著《旧中国的股份制:一八六八年—一九四九年》
轮船招商局在开办后制定的三份章程规条中都对“董事”职位有所规定,但招商局的董事与西方公司董事的职责相差甚远:
《轮船招商公局规条》(1872)规定:“有能代本局招商至三百股者,准充局董,每月给薪水规银十五两。如自行赴局搭股者,能满三百股,该得薪水即归本人自领。”
《轮船招商局局规》(1873)规定:“选举董事,每百股举一商董;于众董之中推一总董,分派总局、各局办事,以三年为期。”董事协同商总(总办),具有人事任命权并负责管理财务:“总局、分局、栈房、司事人等,由商总、商董挑选精明强干,朴实老诚之人,查明来历,取具保结,方可任用。设有差池,惟该董原保是问。”“总局银钱由商总会同商董选择殷实钱庄存放,生意务宜格外留心”。此外,股票登记需由商总、商董会同画押,加盖本局关防,方可生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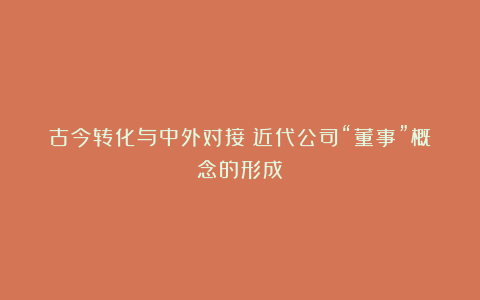
《轮船招商局章程》(1873)规定:“办事商董拟请预先选定,以专责成也。商局设于上海,议交唐丞廷枢专管,作为商总以专责成,再将股份较大之人公举入局,作为商董协同办理。”这份章程任命朱其莼、徐润为上海局商董,宋缙为天津分栈商董,刘绍宗、陈树棠、范世尧三人充当汉口、香港、汕头三处商董。
从这三份章程可以看出,轮船招商局的总办(商总)由官方委派任命,董事则是根据招股数量的多寡推举而成,但实际上并无推举程序,人员皆为官方指定,这和西方公司由股东选举董事的产生方式截然不同。我们追溯历史后能够发现,轮船招商局的董事实际上仍属于中国本土董事。明清以来,各个行业公举董事,其中最重要的一份职责是解决经费问题,或是自行出钱,或是出力劝捐,这与轮船招商局每招商百股便可推为董事的制度可谓一脉相承。招商局开办之初总股本仅一千股,每股股银一千两,一百股即为十万两股银,持股占总资本的10%,因此招商局的合格商董人数并不多,被任命的商董,如朱其莼、徐润、宋缙等人除自己本身是大股东之外,也的确在招股融资中出钱出力,两年时间使招商局实收股金四十七万六千两,仅董事徐润一人就持股二十四万两。再者,轮船招商局因其官督商办的经营模式,各商董虽能够襄理商总参与总局和各局的人事、行政、预算以及分红等日常经营事务,但在其中并无多少实质决策空间,也难举行会议合议重大事项,事事皆受制于官方派来督查的道员。易言之,轮船招商局的董事仍属于本土的传统董事。
徐润
(二)“绅领商办”公司中的董事:以大生纱厂为例
甲午战败,洋务运动遭到了重大挫败,官督商办公司的弊端逐渐显露。此时“商战”思潮正盛,商人们认为官方开办的公司钳制太多,难以施展拳脚,公司任意侵蚀商人入股的资本,股息却数年不返,“良法美意,以官督而悉败矣……以君权而行之民事,安在其不败也?”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批评道:“由官设立办国事者谓之局,由绅商设立为商贾事者谓之公司……今中国禀请大宪开办之公司,虽商民集股,亦谓之局。”官督商办的公司总办以道员居多,只求品级较高,不问胜任与否,既不熟识商务,又不谙其中利病,导致股份虽多,官秩虽大,但“所学非所用,西人无不讪笑。”郑观应认为商贾之事应当交予专业的商人办理,“董事由股东而举,总办由董事而举,非商务出身者不用”。“公司所用之人,无论大小皆须熟悉利弊,方准采用,当道不得滥荐”。如此才能振兴商务。
在此背景下,清政府放宽了开办公司的限制,允许民间私人办厂,原有官办局厂也相应进行改制,“商总其事,官为保护,若商力稍有不足,亦可借官款维持”。1895年至1899年,张謇在南通筹办大生纱厂时筹股受阻,几番陷入资金困局,最终被迫引入官股,以“绅领商办”的经营模式开办纱厂。在“绅领商办”模式下,官方不参与厂务,不派官董督管,不计盈亏,仅每年分取官利红利。厂内首设总理一人,由张謇担任,总管一切事宜,通官商之情,负责酌定章程,举措董事。开厂之初的董事均为厂内大股东,由沈敬夫、高清和蒋锡绅等人充任,负责各项厂务。董事之下,设执事、经理等人具体办理各项事宜。
郑观应著《盛世危言》
大生纱厂的董事权力极重。根据《厂约》规定,大生纱厂中重大事宜,以银钱账目、机器、进出货、杂务四项为大宗,每宗分设一名商董主事,其他附股商人不得参与其中。商董负责人事任命,“严禁局外荐人,挂名干修”。《厂约》还详细规定了商董的具体职责,除专管事项外,以监督产品质量、审核物料价格、稽查偷弊、考核用度为主。各商董每日还需在总办事处集中开会,“考论花纱工料出入利弊得失,酌定因革损益”。至于各部门如何具体行事查察,则由各绅董领衔与执事商讨,制定章程。
大生纱厂《厂约》对董事的相关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公司在制定董事制度时,有意综合本土董事和西方公司董事两种制度。延续中国本土董事制度的是各部门分设董事以专责成制度。如上文所举云门书院一例,书院事务分监院、营造、催租、收存等,分别设董事进行管理,这一角色更像是西方公司里的部门经理或主管,而西方公司的董事不一定分管公司具体的日常事务。借鉴西方公司制度的地方有四处:第一,大生纱厂开始实行初步的董事会合议制度,各董事每日集会总办事处对生产工作进行讨论,决策公司经营方向,进行战略管理,这与西方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集体决策的制度有相似之处;第二,董事职责不同,各有权限,但都有“稽查”之权,具有监督职能。作为总理的张謇也要接受董事的监督,“章程未善,举错不当,进退未公,功过未确,赏罚未平,诸君皆可随时见教。”这意味着董事能够制衡权力,不会致使权力为一人独专;第三,当时的人已经意识到董事会与股东会之间应当两权分离,相互制衡,如钟天伟即建议:“每一公司由各股东公保董事十二人,由众董事再推总办正副各一,而每人亦必有多股于中。总办受成于各董,各董受成于各股东,上下钳制,耳目昭著,自然弊无由生”;第四,董事的任期、选举方式等规定也仿照西方公司,如《通州广生油厂集股章程》中:“比照各国商律,公司董事任期三年为满,届满之先由绅知照股东会议另选。”
以大生纱厂为例,我们不难看出经过公司“官督商办”经营模式的阶段,当时的实业家对公司有了更进一步的思考,不仅认识到公司的“私属性”,而且也对公司董事制度的概念有了更进一步的认知。他们为“绅领商办”模式下的公司制定规则时,有意借鉴西方公司治理经验,融合中西董事制度,进行本土的改造和实践,中国近代公司董事制度由此初现雏形。
张謇
(三)《公司律》颁布后的公司董事
庚子之变后,清政府厉行新政,率先设立了商部并命伍廷芳、沈家本、陈璧等人着手编订商律。1904年初,《钦定大清商律》梓行,内有《商人通则》九条及《公司律》一百三十一条。《公司律》中“第四节”专门规定了公司董事产生方式、人数、任期及职责,“第六节”董事会议则规定了董事局会议的议事规则。
邓峰总结公司董事会制度有三项原则:董事会由股东选举(公司的两权分离)、采取共管与合议模式及董事作为公司责任的最后承担者。他提到清末《公司律》大致恪守了这三项原则:董事由众股东公举,成立董事局(第六十二条),明确了两权分离原则;董事局议会需有三人到场方可议定各事(第六十四条)以及在董事局会议时,每人有一议定之权(一票),施行多数决议事(第八十九条、第九十条),确立了董事会采取共管与合议模式原则;董事局为各公司纲领,董事应办应商各事宜(第六十七条)和董事局负责选派(开除)公司总办或总司理人、司事人等(第七十七条),即明确了董事会作为产生其他机构的中心原则。此外,《公司律》还仿照《日本商律》的规定,限定只有持有公司股份十股以上(资格股)的股东才有资格成为董事(第六十五条),以及董事局每年需督率总办或总司理人等结算公司账目,造具报册。
《公司律》的颁布意味着近代公司董事概念的正式形成,但这并不是商人或实业家从实践中探索而来的。《公司律》在编订时以“兼顾中西商情”为宗旨,通过翻译各国法律书籍及通商条约,最终以《英国颁行公司定例》和《日本商律》作为师法对象进行整合而成,虽调整了个别规定以符合国情,但大多数制度均是移植而来。因此《公司律》的董事制度可视作西方公司董事制度的“翻版”。
邓峰著《普通公司法》
四、概念格义:两种政治制度的抵牾与融合
晚清的能人志士认为只要将西方的制度与法律通过翻译的手段引入中国并加以实施,就可以治愈晚清的沉疴痼疾。但不难发现的是,法律移植与本土化并没有当时的人们想象得那么简单,古语与新词、西方制度与中国传统的水土不服之处比比皆是,单在公司“董事”这一处着眼,就可见一斑。
(一)近代西方公司制度的移植困境
《公司律》颁布后,清政府继而制定了《公司注册试办章程》并下谕施行,已设立和新设立的公司均需按照《公司律》的规定到商部注册执照,经核查后方可开办。但是《公司律》的实施情况如何呢?通过查阅《商务官报》每期《本部要批一览表》,可以发现不少公司设立的章程与《公司律》中的规定有诸多相左之处,被商部要求整改。譬如,江苏茅麓树艺公司董事兼任查账人,与商律规定不符;广东自来水公司章程中董事未设任期,永不更换,没有按照程序选举,与商律规定相悖;常州大均机器油饼公司章程既规定董事需一年一换,又规定经理须对公司事务驾轻就熟,不可随意更换。商部认为这两条规定未免两歧,不符商律精神。
章程的设立是一回事,公司的经营又是另一回事。按照商律要求设立章程的公司在实际运营中是否遵守章程规定呢?根据徐立志的考证,即便各个公司的章程都严格符合商律的规定,各公司店铺在实际活动中也未必按照章程行事。实际上,在董事选举方面,当时有大量的公司董事是按照股东出资金额的多少进行推举的,控股股东对公司有绝对的控制权;在公司议事方面,股东大会、董事局会议往往流于形式,《公司律》未颁之前,便有人总结中国公司议事等同设宴,形同虚设:“凡遇议事,先期发帖,届期众至,相待如客,公事未说,先排宴席。主宾欢然,其乐无极。迨至既醉既饱,然后以所议之事,出以相示,其实则所议早已拟定,笔之于书,特令众人略一过目而已。原拟以为可者,无人焉否之,原拟以为否者,无人焉可之。此一会也,殊属可有可无。”在《公司律》颁布后,许多公司依然照旧,董事局并不合议议事,仅负责举办宾主尽欢的宴席,实际的决策权仍属于大股东,不仅会议无效,而且浮费巨大,影响公司的财政和运营。可见,晚清政府对西方公司制度的移植并不成功,在本土化的过程中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至此我们不禁发问,造成这种移植困境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商务官报》
(二)叶徒相似:法律移植的不可通约性因素
法国法学家皮埃尔·罗格朗(Pierre Legrand)在论及法律移植时曾犀利地指出:“法律移植”是不可能的。法律作为规则的一种,一旦移植到他处,其意义(语词的观念内涵)就会发生改变,而当规则的意义发生改变时,规则自身也会改变。与此同时,其他法域的法律规则被传入本地时,总是遭遇来自本土性的、不可通约的因素抑制。因此,本土的接受是有限的,且本土文化固有的强大整合能力会使这些外来的规则发生本土化趋势。此时彼物非此物,矛盾随之而来。因此皮埃尔·罗格朗总结道:“从一个法域借用的规则不会具有该规则在原来法域的任何意义。原初的规则一旦跨越了边界,就必然会经历某种变化,影响其作为规则的资质。”皮埃尔·罗格朗还借用语言学的理论论证法律移植只能翻译文本信息,无法将意义体系完全从一个文化传输到另一个文化。
皮埃尔·罗格朗像
跨文化的传播与融合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罕见。诞生在异族文化背景下的事物,其名称往往独具含义,在传入之初势必与本国文化互相龃龉。及至了解渐深,则会发现文化之间的共通之处,于是便以本国的义理阐释异族的事物,这便是陈寅恪先生所言的“格义”之法。陈寅恪先生在《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中提出“格义”是西晋时竺法雅传播讲颂佛经所用的方法,即“取内典与外书以相拟配”,以“外书”(儒家经典)中的类似概念去比拟配合“内典”(佛经)中的词汇含义,其用意“固在融会中国思想于外来思想之中”。与“格义”之法暗合的是由尤金·奈达(Eugene A. Nida)提出的“功能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翻译理论,即注重翻译的交际功能和目标读者的反应与体验,从功能的角度出发,不拘泥于语言的形式,力求最大程度贴近受众读者的语言环境。
尤金·奈达
但正如罗格朗所担忧的那样,翻译上的“格义”与“功能对等”可能反而会导致概念理解上的混乱。以清代学者介绍西洋学术时的翻译为例,后人总结其有两处谬误:一是“译名之谬误”,一是“意义之谬误”。一些专有名词本应有特殊意义,但是译者每每“以意为之,毫无标准及命意可言”。以本国固有的传统观念去理解新兴事物本就不容易,倘若新兴事物又借用古典语词的“躯壳”阐释新意,不免会引发诸多矛盾。中西方“董事”概念即是如此,中西方的“董事”一职因功能相仿,而获得了相同的名称,但时人却忽略了二者的设置目的和运作逻辑的迥然不同。
罗格朗的理论实际上强调的是地域文化背景之间的不可通约性,这意味着全盘的法律移植并不可取,在移植法律概念及功能的背后还需要考虑概念之外的政治文化制度。易言之,公司制度一定程度上是政治制度在实践和理论上的反映。这一点其实早在百年之前的中国就已有人提出:“欧美商业公司,其制度之美备,殆无异一民主,此自以生于立宪民主国,取则不远之故。专制君主之民,本无平等观念,故公司之制,中国亘古无之。”严复在其翻译的《法意》中,通过按语辨析了中西公司制度的异同,指明其差别在于政治制度与观念。梁启超亦有相似洞见:“大抵股份公司之为物,与立宪政体之国家最相类,《公司律》则譬犹宪法也,职员则譬犹政府官吏也,股东则譬犹全体国民也……是故新式企业,非立宪国则不能滋长。盖人民必生活于立宪政体之下,然后公共观念与责任心乃日盛,而此两者即股份公司之营魂故也。”梁启超认为新式企业发展之根本在于国家需确定立宪政体,采取施行代议制度,传统的政治土壤无法孕育新式企业。
严复译《法意》
(三)淮南淮北:孕育中西方“董事”制度的政治土壤
西方公司董事会制度受制于政治和宗教文化的影响。“历史表明,公司诞生于政治活动,是政治斗争的产物,而不仅仅是技术创新的自然结果。政治斗争塑造了公司的定义、权力、责任、宗旨及其成员”。富兰克林·格瓦兹(Franklin A. Gevurtz)考证出西方公司集体决策与合议制度源于中世纪国王设置的采用委员会机制的顾问团;代表制度源于国王要求地方长官推动选举组成议会,由骑士和城镇代表组成议院,和贵族分别议事——贵族后来成为上院的组成人员,而骑士及城镇代表则发展成下院;投票选举制度源于英国的城镇理事会,国王授权选举执政官和司法官,由城镇举行集会进行选举。这些政治制度传统也受到宗教(基督教)的影响,如中世纪教会内部红衣主教团的选举。史蒂芬·博顿利(Stephen Bottomley)教授则应用相对现代的宪法理论(Constitutional Theory)考察公司,公司如同国家,公司章程如同宪法,二者都需要考虑个体成员与整体利益的关系。再如美国宪法通过打破集权的方式避免滥用权力,使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分立并相互制衡,立法权与行政权分别由议会和政府行使。对应到公司,董事会、股东会与管理层各司其职,尤其是董事会和股东会权力需要两权分离,相互制衡。公司股东通过代议制选举出少数人组成董事会,通常采用多数决的方式,共同行使决策职能与监督职能,并约束整个公司。董事会不仅需要考虑股东利益,更需要考虑公司整体共同利益。如同1844年英国《合股公司法》通过时,时任英国贸易委员会副主席的罗伯特·罗威(Robert Lowe)将公司比喻为“小共和国”(little republics)。公司“是政治斗争的产物”,是“一种创新”,是“几百年来出现的第一个自治机构”,在公司身上可以看到代议制民主的映照;同时,“这类’小共和国’显然对催生它们的社会产生了政治和社会影响”,进一步推动了现代国家代议制的完善。
罗伯特·罗威
西方公司处处映射着代议制的影子,中国近代公司董事制度则深受绅董制的影响。咸同朝前后出现了拥有“非正式权力”的绅董群体,“州县有州县之绅董,一府有一府之绅董,省会有省会之绅董”。绅董治理逐渐与官僚制分野,成为一种普遍的地方基层治理机制。但绅董制“并不是朝廷典章制度意义上的规范体系,各地的绅董权属体系并不具有统一规制和范式”。易言之,绅董制并没有被朝廷建制成正式的政治制度,却在实际的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治理逻辑、治理方式和组织结构都潜移默化地成为基层习惯,影响着地方社会各个层级和行业。
各地、各行业绅董董理事项不一,权责各异,却也有共通之处:第一,绅董由推举产生;第二,个体决策,复杂事务通常会有多个绅董分管,各个绅董各任一事,互不干涉。向前追溯,这两项特点都是由中国传统制度演变而来:第一,推举制最早可以追溯到禅让制,两汉施行的察举制也是通过举孝廉的方式选拔人才,延续到魏晋南北朝时为九品中正制。尽管最终科举制取代推举制成为正式的选官制度,但是民间的推举制度并没有消失,乡贤、耆老均是通过推举制度进行选拔的,如各地方志中常有“公举乡贤”“推服耆老”等语;第二,受皇权和宗族观念的影响,中国古代主要以家族为单位进行生产生活,家族之间都较为独立,家族内部成员往往分工明确,共事生产,族长(家长)负责整体经营、开支、分配等决策。“谚云宁可一人养一鸡,不可数人牵一牛,”中国古代更推崇个体决策,而非集体决策。
瞿同祖著《清代地方政府》
(四)橘枳之辨:中西董事制度的差异与融合
由于中西方政治制度的不同,受其影响下的公司制度也有较大差异。对比绅董制影响下的中国近代公司董事与代议制的西方公司的董事,我们可以发现二者之间的显著差别:首先,西方公司董事是由股东通过投票程序选举而来,而中国近代公司的董事常常是由控股股东直接推举,或是由总办任命,没有经过选举程序;其次,西方公司董事会集体决策已是惯例,而中国近代公司董事则仅对自己分管的工作内容具有决策权,公司的重大事项如经营方向、支出决算、官府交际等由总董一人决定,没有集体决策的制度来源;最后,西方公司董事会与股东会之间两权分离,而中国近代的公司董事和大股东角色则高度重合,董事常由控股股东推举而来。又因为中国古代没有集资招股的制度,常见的乃是商帮式的合伙,因此极易导致控股股东兼董事“招股既成,视如己物,大权独揽,恣意侵吞”的情况,而小股东又不问公司经营状况,一味炒股,任意退出,影响公司的发展。
绅董制与代议制本是两项独立发展的制度,晚清十年新政则打破了二者之间的壁垒,中国的政治制度随之进入了一段改弦繁密的时期。1907年,清政府公布了预备立宪《逐年筹备事宜清单》,规划了地方自治实施步骤,并下谕民政部拟自治章程。随后编制馆大臣电谕各省督抚,要求府州县设置议事会及董事会,推行地方自治活动,率先在地方效法西方建立代议制度以试行立宪政治。次年颁行的《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便详细规定了董事会的职责、权限及选举方法等内容,绅董开始获取正式权力,绅董制也与代议制产生了交集。
约翰·米克尔思韦特、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著《公司简史:一种革新性理念的非凡历程》
《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中第一条讲明:“地方自治,以专办地方公益事宜、辅佐官治为主,按照定章,由地方公选合格绅民,受地方官监督办理。”自治事宜包括学务、卫生、道路工程、农商工务、善举(救贫、救生、救火等)、公共营业(电车、自来水、电灯等)及这些事务的款项筹集和例由绅董办理的工作。各城镇设议事会和董事会,董事会设总董1名,董事1—3名,名誉董事4—12名。总董由各省督抚遴选任用,董事由城镇议事会选举,经地方官核准任用,均为两年任期,任满改选。董事出自本地城镇选民,选民资格为具有本国国籍,在本地居住三年以上,年纳正税或公益捐款2元以上的年满25岁男子。董事员额为议事会议员的二十分之一,城镇议事会议员以20名为定额,若满五万人口增设议员,其后每加人口五千,可增议员1名,最终以60名为限。
原本在地方官的影子下把持乡政,垄断公共权力的绅董们通过选举的方式跻身官位,建立了集体决策的董事会,走向正式的权力场,但令人意外的是这却使立宪政治止步于此。绅董群体本是代议制中最合适的“代议士”,他们长期担任的职责也是“通上下之情”,但他们虽然通过“民主”的方式拥有了更大的权力,却并非民主政治的斗士或倡导者。在一定程度上,绅董成为了民众新的父母官和冲突对象,宪法制度和思想没有向下伸展到地方基层。这样看来,清政府九年预备立宪计划中提升国民教育水平、开化民智和完善地方自治制度的规划并非是延宕立宪的托词,实为推行立宪必不可少的工作。
也许按照预备立宪的计划,在逐步提升全国国民教育水平之后,绅董制能够与代议制相融合,从而逐步探索建立适合中国的公司制度。未及立宪,清祚已终,近代中国自此陷入长期的动荡状态,公司的发展也近于停滞。
五、结论
19世纪中叶以降,“董事”这一古典语词的词义与指向发生了频繁的变化。此前“董事”仅是指涉管理书院、善堂、商会事务的职位,咸同年间地方团练的开办使“董事”与地方绅士结合,组成协助官府进行地方公共事务治理的绅董群体,并由此发展出实际统理地方事务的基层治理机制——“绅董制”。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办,公司制度落地近代中国,在经历了“官督商办”“绅领商办”以及《公司律》颁行下的三种模式后,近代公司“董事”概念也在中外对接与古今转化的过程中渐次形成。
本文第一作者著《中国法制史讲义》
然而“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中西两地的政治土壤差异过大且相互抵牾,导致近代中国仅能习得公司的制度框架,虽样式俱全,却领会不到个中精魂。透过“董事”一词,我们可以清晰地观察到近代公司法律制度移植的部分剪影,西方公司董事制度受制于中世纪的政治与宗教文化,处处反映着代议制度,近代中国公司董事的“名”与“实”则深受绅董制的影响。因为中西方的政治制度大相径庭,所以两种制度下公司董事的选举方式、议事制度以及权利责任也截然不同,中西方的董事制度可谓“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如果忽略了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政治背景,哪怕将当时“最先进”的法律制度移植到本国,也无法发挥同样的作用、无法真正地成为有效的法律资源。
[原文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4期,作者:聂鑫、朱小丫,清华大学法学院]
编辑:若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