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魏北齐壁画墓中出现了较为突出的神人神兽出行图像,可按分布位置和丰富程度分为三种,并与墓葬规模和等级密切关联。此类图像皆以墓室部分的四神为核心,龙、虎和玄武背上往往有神人乘御,显示出护卫和扈从升仙的意义。前两种尤其是第一种的神人神兽继续向甬道、天井和墓道上部延伸,形成以龙虎为引导、包括风雨雷电和河伯诸神等的庞大队伍,并与其下部的仪仗出行队伍相配合,一方面显示了出行的目的——神仙世界,另一方面则彰显着出行者的身份——天神威仪。而对于北朝墓葬壁画的布局和意义,还应综合顶部和上部与天界有关的内容来考察。
威仪自天:北朝壁画墓神人神兽出行图像试探*
王 煜 雷嫣然
东魏北齐时期,以都城邺城和别都太原为中心,出现了一批规模宏大、绘制精美、布局规整的大型壁画墓。墓主多为帝、王级别,壁画内容和布局较为稳定,被学者称为“邺城规制”,受到学界高度关注。目前学界对其中的主要内容如墓主人像、牛车、鞍马和仪仗出行等皆有较多研究,而对主要集中于墓室和墓道上部的各种神人神兽出行题材尚少讨论。或泛论其升仙意义,或以《山海经》等文献考释其内容,或认为是道教雷部众神的表现。这些研究皆有不少突破,也提供了较好的基础。其实,此类内容不仅在最高等级大型壁画墓,在同一时期的中型壁画墓中也有较为稳定的呈现,只是分布位置和丰富程度有较大差别,但其核心却始终一致。对此类图像的深入考察,不仅能深化壁画题材的研究,对于壁画整体布局与意义的理解也将产生重要帮助。因此,本文拟在以往研究基础上,较为全面、细致地梳理此类图像,进一步结合其等级特点和整体布局,并联系相关文献进行较为深入讨论,提出一些新的认识,以求正于学界。
本文所论北朝壁画墓神人神兽出行图像是指以神人和神兽为主体的成一定队列的行进图像,目前集中出现于东魏北齐时期的大中型壁画墓,尤其是邺城、太原一带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几座壁画墓中。根据分布位置、整体布局和丰富程度等情况,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形式。
第一种内容众多,连续分布于墓室、甬道和墓道上部,尤其在墓道上部展现为规模庞大的出行队伍。
河北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是目前所见整体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东魏北齐墓葬,自南向北由长斜坡墓道、甬道和弧方形墓室组成,全长52米,墓道长37米,墓室边长约7.5米。一般认为属于帝陵,墓主被推定为北齐文宣帝高洋。墓室壁画基本漫漶不存,顶部残留有包括银河和星点的天象图,其下为带方格的36个动物,或为与十二辰同类的三十六禽,下有神禽神兽等残迹,再下的墓室壁面推测为人物、仪仗等。墓道壁画保存较好,地面绘出地毯,两壁下部为人数众多的手持幡幢羽葆和各类器杖的仪仗出行,上部即本文所论神人神兽出行队伍,方向皆朝向墓外。东壁最前部以青龙为主体,其前尚有一凤鸟和一兽首人身神祇。该部分处于墓道最前部的狭长三角区域,从位置上看,应该共同引导其后上部的神人神兽和下部的仪仗出行,本文暂以内容将其归入上部神人神兽出行。其后依次为人面鸟身、鹤、鸟身蹄足、兽首人身、龙首鸟身、兽首人身、虎形翼兽、凤鸟等神人神兽,其后随着幅面的加宽而再分为上下两排,内容主要为兽首人身神祇和凤鸟〔图一,图二〕。西壁与东壁大体对应,只是最前部以白虎为主体。甬道壁面残存有人物,门墙上部壁画保存较好,主体为正面的朱雀,两旁有对称分布的凤鸟、翼兔和兽首人身神祇。就位置和题材来看,这里以朱雀为中心的壁画与墓道上部的神人神兽出行相接,似为一体,由于位置和形制的原因,表现为此种状态。
图一 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壁画线描图
河北磁县出土
1. 墓道东壁 2. 甬道门墙
图二 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墓道上层壁画神人神兽形象
河北磁县出土
河北磁县茹茹公主闾吒地连墓下葬于东魏末,根据出土墓志,墓主为柔然公主、后来北齐武成帝高湛之妻。该墓形制与湾漳大墓相似,规模略小,全长近35米,墓道长近23米,墓室边长5.5米左右。墓室壁画残损较多,顶部应有天象图,北壁、西壁上部残存玄武、白虎,墓壁下部主要为人物,北壁正中似为墓主。墓道壁画保存稍好,地面亦绘地毯,东、西两壁也为以青龙、白虎为前导的上层神人神兽和下层仪仗队伍,东壁可见者有兽首人身神祇、手持麈尾和芝草的仙人、凤鸟等,皆朝向墓外奔走于云气之中。甬道壁面绘人物,门墙上亦为以正面朱雀为主体的神人神兽。
类似的图像还见于山西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该墓形制与上述两例大体相同,全长41米以上,墓道长31.5米,墓室边长近6米。墓室壁画残损严重,顶部应为天象图,东、西壁上部有龙、虎残迹,下部为人物出行,尚存骑马和伞盖羽葆残迹。墓道壁画保存较好,分为上下四层,上一层为神人神兽出行,与前述类似,下三层皆为人物活动,内容稍异。上数第二层主要为山林狩猎场景,第三层为服饰各异的武士挎弓出行,第四层为戴冠武士佩刀行进。下面两层行进人物虽未持器杖,但与上述仪仗出行亦颇相似,只是汉文化因素较少而胡风和武备因素突出,符合代北风气。上层为本文所论神人神兽出行,东壁前端残损,其后可辨者依次有凤鸟、人物持麈尾、牛形翼兽、兽首人身、象首鸟身、狮形兽衔蛇、人物持袋吹气、人物骑蹄足翼兽、人物持扇、衔蛇神禽、鸟身蹄足、兽首人身衔蛇、凤鸟衔仙草等神人神兽。西壁前端亦残损,其后可辨者依次有兽首人身、人面怪兽、站立和蹲踞怪兽、人物持麈尾、翼兽、犬形兽衔蛇、人物骑鱼、兽首人身、持瓶倾倒的人物骑龙、兽首人身持飘带、人物持麈尾和仙草、人物(女)骑鹤、兽首人身、兽首人身扛石、身绕连鼓的兽首人身、凤鸟、凤鸟衔仙草、翼马衔兽、人物持麈尾、兽首人身等神人神兽。整个出行亦朝向墓外奔走于云气之中〔图三,图四〕。门墙上绘门楼和侍女,屋顶两侧为一对凤鸟(朱雀),亦与墓道上层神人神兽相接。甬道顶部尚有兽首人身神祇等。
图三 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墓道壁画线描图
山西忻州出土
1. 东壁 2. 西壁
图四 九原岗北朝壁画墓墓道上层神人神兽出行壁画 (局部)
山西忻州出土
1. 西壁后部 2. 东壁后部
第二种不见于墓道,主要分布于墓室和甬道上部等。由于空间局限,内容较第一种简略。又由于墓室盗扰和密封性差等原因,壁画保存较差,限制进一步讨论。
太原北齐东安王娄睿墓为坐北朝南长斜坡墓道单室墓,甬道前有一天井,全长36米有余,墓道长约22米,墓室边长约5.7米,规模与茹茹公主墓相近。墓室上部壁画残损严重,顶部为天象图,其下为十二辰或三十六禽。东壁上部残存青龙的大部分身躯,龙身上有一人乘骑,残存人物腿部以下。龙前应有一导引仙人,亦仅存腿部〔图五:1,参见图十五:1〕。龙后一兽首人身神祇持槌敲击环绕其身的连鼓〔图五:1,参见图九:1〕,神人神兽皆朝墓外行进。从脱落的西壁残片,推测其原有白虎等,北壁上部残留玄武的一段蛇体,北壁下部为墓主夫妇宴饮。东、西壁下部为鞍马、牛车及簇拥其旁的羽葆、伞盖、仪仗等。甬道上部两侧各有一只凤鸟前行,下部为门吏。天井东壁下部为仪仗人物,上部的最下部分还残存有朝向墓外出行的鹿首鸟身和兽首人身神祇各一〔图五:2〕。墓道分三层绘制,上两层为各种牵马和骑马人物和仪仗,下层为仪仗人物。可见,墓室、甬道和天井上部原有较为丰富的神人神兽出行图像,很可能也是连为一体的,许多形象与上述大墓一致。不同的是,这类图像并未延伸到墓道上部。由于多出天井结构,且天井上部残存的神人神兽出行较其前墓道中的仪仗人物位置低出很多,不排除神人神兽出行原本顺着天井向上延伸的可能。
图五 太原北齐娄睿墓神人神兽壁画线描图
山西太原出土
1. 墓室东壁上部 2. 天井东壁下部
第三种仅见于墓室,虽然仅以四神为主题,但龙、虎背上多有人物乘骑,前后尚有少数神人神兽引导、扈从。一方面出行意义仍然突出,另一方面也与上述大墓墓室部分的神人神兽出行图像一致,故应归为一类。
太原南郊北齐壁画墓墓室边长约3.7米,规模较上述大墓逊色许多。顶部原有星象图,已损毁。东壁上部最前端为一仙人引导,其后为一黄衣人物骑青龙,人物之上尚有一些神人神兽,画面中间夹杂着各式仙草和云气〔参见图十五:2〕。西壁上部残存白虎与虎上人物的足部,北壁上部神人神兽中见有人首鸟身形象。东、西壁下部应为人物仪仗与牛车、鞍马,北壁下部为人物端坐于帷帐之中。
山东临朐崔芬墓墓道残长9.4米,墓室边长3.58米。墓室顶部残缺。四壁壁画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为神人神兽出行以及星象图,下部为树下人物屏风和墓主人出行。其中东壁上部主体为人物骑龙,前方有二仙人引导,后方有一奔走的兽首人身神祇。西壁为人物(女)骑虎,前面似有仙人引导,后方亦有一兽首人身神祇,此下有墓主人出行。北壁为持剑人物御玄武,两侧各有三名兽首人身神祇。南壁西侧为口衔仙草的朱雀〔图六〕。
图六 临朐北齐崔芬墓墓室壁画神人神兽出行示意图
山东临朐出土
1. 东壁 2. 北壁 3. 西壁 4. 南壁
作者制,底图采自临朐县博物馆《北齐崔芬壁画墓》,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16-17页,图四-七
山西朔州水泉梁北齐壁画墓墓道长13.5米,墓室边长4.5米。壁画集中于墓室和甬道,不见于墓道。顶部为以银河为中心的天象图,其下圈带内按方位绘制四神,其间尚有一些兽首人身神祇和其他神兽,四神及神人神兽皆行进于云气之中。再下一圈为按方位配置并进行于云气之中的十二辰。北壁主体为墓主夫妇端坐于帏帐之中,东、西壁为牛车、鞍马出行,甬道及东、西壁前部尚有骑马持旗的仪仗队列。不论从墓葬规模和壁画内容、配置来看,该墓皆处于前述典型的大型和中型壁画墓之间。例如,相比大型壁画墓,缺少墓道壁画部分,神人神兽和仪仗出行队伍也较为简略;但相比中型壁画墓,神人神兽和仪仗出行队伍又要突出一些。只是由于表现神人神兽出行的圈带较窄,形象较小,四神与其他神人神兽之间未体现差别,其上也无人物乘骑。十二辰在四神和神人神兽出行之下,也与前述大型壁画墓有所不同。
另外,山西太原北齐武安王徐显秀墓墓门和甬道上方各绘有两名向下俯冲的兽首人身神祇〔参见图十四:4〕,应当亦有神兽伴随出行的意图,但并未形成较为完整的队列,故不列入。
上述神人神兽出行图像,一方面题材丰富、形象多样,加之涉及神怪,观念驳杂,而当时人也未必对具体每一形象都赋予明确内涵;但另一方面毕竟集中出现于最高等级墓葬中,应该还是有所设计的。因此,本文仅对其中在中古时期图像传统中较为稳定、可以参证的题材进行探讨,以利于进一步讨论其整体意义。
(一)龙、虎与四神
湾漳大墓和茹茹公主墓墓道最前端上、下两层神人神兽、仪仗出行队伍起始皆为体型颇大的龙、虎,龙在东壁,虎在西壁〔图七:1、2〕。此种做法目前只见于邺城地区的东魏北齐皇室墓葬中,可能具有等级意义或属于一定的阶层文化。稍早的南朝陵墓两壁拼砌砖画中也以体型巨大的龙、虎引导上、下两层神人、仪仗出行〔图八〕,只是砖画集中于墓室中,龙、虎既承担了引导意义,同时又与墓顶前后的朱雀、玄武构成四神,而北朝陵墓墓道前端的龙、虎是另立于墓室四神之外的。虽然墓室上部壁画大多保存很差,但仍有部分残迹,且可相互参考。青龙、白虎、玄武分别位于东、西、北壁上部,朱雀的位置和形式则比较多样〔图七:3〕。龙、虎上应有人物乘骑〔参见图十五:1、2〕,崔芬墓玄武上亦有乘御人物〔图七:4〕,前后尚有一些神人神兽扈从,呈现出行形态,总体上与甬道、墓道上部的神人神兽出行构成连续画面。墓室中的四神和墓道前端的龙、虎形体较其他神人神兽大得多,结合位置来看,墓葬上部的这一神人神兽出行队伍应以四神为中心,龙、虎为前导(目前仅见于邺城皇室墓葬)。
图七 北朝墓葬壁画中的四神
1. 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墓道青龙 河北磁县出土
2. 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墓道白虎摹本 河北磁县出土
3. 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门墙朱雀摹本 河北磁县出土
4. 临朐北齐崔芬墓墓室北壁玄武 山东临朐出土
图八 丹阳金家村南朝陵墓墓室右壁神人神兽与仪仗出行砖画布局示意图
江苏丹阳出土
作者制,底图采自南京博物院《琅琊王:从东晋到北魏》,译林出版社,2018年,第81页;姚迁、古兵《六朝艺术》,
文物出版社,1981年,图版二一三、二一四、二〇六、二〇九、二一〇、二一二
(二)风雨雷电与河伯诸神
九原岗墓墓道西壁神人神兽出行后部有一左手持棰的兽首人身神祇,周围环以连鼓〔见图四:1〕,毫无疑问为汉代以来常见的雷公形象〔图九〕。中部一骑龙神人手持一瓶往下倾倒,应为雨师〔图十:1〕。汉墓图像中已有手持水瓶的雨师形象,但并不骑龙。《抱朴子·登涉篇》云:“辰日称雨师者,龙也。”梁元帝《金楼子·志怪篇》亦同,可见六朝时期确实存在龙与雨师相关的观念。东壁与雨师相对的位置,有一神人长发后扬,口吹气,手持袋,当为风伯〔图十一:1〕。汉墓中也常见口吹气的风伯,但此种一手持袋的形象更接近北魏以来佛教石窟中所见的风神王,后者尤其流行于东魏北齐的邺城地区〔图十一:2〕。阿富汗巴米扬、新疆克孜尔石窟及敦煌莫高窟中均可见双手持巾或袋的风神〔图十一:3〕,此种形象应该综合了汉地传统和西域佛教因素。西壁乘龙雨师之前,尚有一骑鱼神人〔图十:2〕。虽然乘坐鱼车或乘鱼形象也多见于汉墓,性质可能比较多元,但与风雨雷电诸神组合者往往指向河伯。因为河伯也有“浮云洒雨”的能力,且地位、神性与风雨雷电诸神相近,在游仙文献中也常组合出现。娄睿墓墓室东壁上部人物乘骑青龙之后,也有一兽首人身持棰而环绕连鼓的雷公〔参见图九:1,图五:1〕。由于大部脱落,是否还有风伯、雨师等内容已不得而知,至少说明此类题材并非九原岗墓独有。
图九 环绕连鼓的兽形雷公形象
1. 太原北齐娄睿墓壁画摹本 山西太原出土
2. 敦煌莫高窟第249窟
3. 临沂吴白庄汉墓画像石拓片 山东临沂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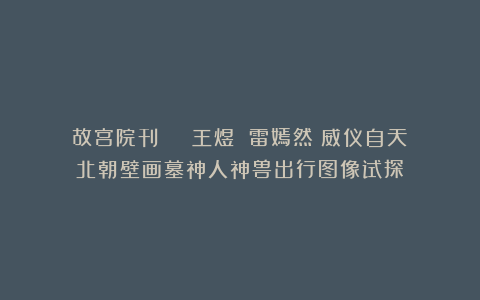
图十 九原岗北朝壁画墓所见乘龙持瓶和乘鱼神祇
山西忻州出土
图十一 北朝风伯与风神王形象
1. 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 山西忻州出土
2. 安阳大留圣窟
3. 敦煌莫高窟第249窟
(三)其他
相对于具有固定形象和组合,且在中古墓葬中存在稳定传统的四神和风雨雷电诸神,其他神人神兽形象则难以认定、争议颇大。笔者认为,不应仅据文献如《山海经》中某些形象描述的相似性,便推定其名称和属性,因为这些文献中的形象描述往往多元而杂乱,上述神人神兽图像也未必全部具有明确属性,必须结合墓葬图像传统才能找到较为准确的定位。
例如,河南邓县和湖北襄阳南朝墓葬中多见将人首、兽首鸟身形象配对于一砖之上,有的就题记为“千秋”“万岁”〔图十二:1〕。太原晋阳古城出土北齐天保元年(550)画像砖上也见有兽首鸟身形象一对,题记为“吉利”“富贵” 〔图十二:2〕。另外,今朝鲜德兴里高句丽永乐十八年(408)壁画墓中一对人首鸟身形象题记为“千秋之象”“万岁之象”,另一对兽首鸟身形象则题记为“吉利之象”“富贵之象”〔图十三:3-6〕。《抱朴子·对俗》云:“千岁之鸟,万岁之禽,皆人面而鸟身,寿亦如其名。”《太平御览》卷九二八所引及敦煌本《抱朴子》中“千岁”,均作“千秋”。萧梁孙柔之《瑞应图》云:“吉利,鸟形兽头也。”“富贵者,鸟形兽头也。”湾漳大墓墓道东、西壁前数第四名神人神兽分别为男、女性人首鸟身形象,显然具有配对关系,大概也是“千秋”“万岁”之类〔图十三:1、2〕。另有一些兽首鸟身的形象〔参见图二:2,图五:2〕,或未与同类形象成对组合,或组合关系不详,是否也与“千秋”“万岁”或“吉利”“富贵”有关,尚待确认。不论是人首、兽首鸟身或其他组合型神人神兽形象,属性和意义都可能比较多元,如果缺少配伍和组合关系,不宜贸然断定。又有意见认为,上述兽首鸟身的蹄足兽为文献中“鸟身鹿头”的飞廉。飞廉为风伯,与屏翳(雨师或云、雷、风神)等相配,从图像组合上看也是有可能的。但文献中同时有飞廉“身似鹿,头如雀”的相反说法,仍有疑问。
图十二 南北朝画像砖中人首、兽首鸟身形象
1. 邓县学庄南朝墓 河南邓县出土
2. 晋阳古城北齐天保元年画像砖 山西太原出土
图十三 魏晋南北朝墓葬壁画中人首、兽首鸟身形象
1、2. 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 河北磁县出土
3、4. 德兴里墓“千秋之象”“万岁之象” 朝鲜平安南道出土
5、6. 德兴里墓“吉利之象”“富贵之象” 朝鲜平安南道出土
出现最多的是一种兽首人身(身体大部为人形,但手、足仍为兽爪)的形象,以往多称为“畏兽”〔图十四:1、2、4〕。该形象在汉墓中已经出现,过去笼统认定为方相氏,有学者将持有多种武器者认定为“持五兵”的蚩尤,颇为合理,但并不能涵盖所有。敦煌佛爷庙湾西晋墓M1照墙上的此类形象题记为“河精”〔图十四:6〕。1926年洛阳城西东陡沟村发现的北魏冯邕妻元氏墓志盖,四周有18个此类形象,姿态、持物各不相同,题记为“挟石”“掣电”“攫天”“发走”“长舌”等〔图十四:3〕。另外,辽宁省博物馆藏传为东晋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宋摹本)上也有一此类形象奔走于云气之中,其旁题记为“于是屏翳收风”〔图十四:5〕。《洛神赋》中屏翳为风伯,可见还可以表现风雨雷电诸神,而上述雷公正是连鼓环绕的此种形象。九原岗墓另有与雷公组合者双手举起巨石〔参见图四:1〕,类似元氏墓志盖上的“挟石”,或许也与雷电之神有关或相近。综合目前材料来看,此种兽首人身可能自汉代起就已是普遍化和多元化的神祇形象,具体属性必须结合持物等特征和组合才能确定,而大多数并无进一步特征,形态或大或小,地位或主或从,数量或一或多,自然不能一概而论(另,深圳博物馆近藏据称为北朝的一件石棺床上,此类形象题记为“辟非守”,由于未详来源,仅备注于此)。
图十四 魏晋南北朝兽首人身神祇形象
1. 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 河北磁县出土
2. 临朐北齐崔芬墓 山东临朐出土
3. 北魏冯邕妻墓志拓片 河南洛阳出土
4. 太原北齐徐显秀墓 山西太原出土
5.《洛神赋图》宋摹本 辽宁省博物馆藏
6. 敦煌佛爷庙湾M1 甘肃敦煌出土
可见,北朝壁画墓中的神人神兽出行图像可根据分布范围和丰富程度分为三种,共有的部分即是墓室中以四神为主体的内容,龙、虎甚至玄武背上有神人乘御,呈出行状态。而墓道前端的龙、虎和墓室中的四神形体也最大,为出行队伍的前导和核心。出行队伍中能够确认且比较重要的还有风雨雷电和河伯诸神。一方面,在题材最丰富的三座大墓中,尚不见于邺城的两座皇室墓葬,可见其并非核心和必备内容。另一方面,在九原岗墓中,它们成组合且较为对称地分布于神人神兽出行队伍的中后部;在娄睿墓中,雷公紧接人物乘龙之后,且形体较大,可见又相对重要。这些认识是进一步理解神人神兽出行图像意义的基础。
三 神人神兽出行图像的意义
由于一方面具有共同的核心内容,一方面在墓葬规模、等级和图像分布、题材数量上又有较大差别,我们拟分为基础意义和上层意义两个层次来讨论。
(一)基础意义
理解此类图像的基础意义,当然要从其核心——也即墓室部分的四神入手。从目前所见材料看,同类组合已见于北魏洛阳时期的石棺上。如永安元年(528)曹连墓石棺,两侧板主体图像为男、女人物各乘骑龙、虎〔图十五:3〕,前后尚有一些神人神兽引导和扈从;后挡为神人乘御玄武;前挡刻画大门,门上有兽面和一对凤鸟(朱雀)。具体题材和整体组合皆与上述墓室部分的神人神兽出行图像高度一致,应是同一传统在不同载体上的表现〔图十五〕。学界多将其称为升仙石棺,认为是乘御升仙的表现。只是有意见认为龙、虎背上的男、女人物为东王公、西王母等神祇,也有意见认为代表墓主夫妇。前者目前并无确切依据,而有些材料中玄武背上也有人物,因此是否一定是墓主夫妇的象征,也有疑问。结合文献材料,目前还是理解为墓主升仙的引导和扈从为宜(后详)。在墓室上部四神的基础上,第一、二种神人神兽出行图像又在前方的墓道和甬道上部增加了龙、虎前导,风雨雷电和河伯诸神等内容,构成更加庞大的出行队伍。
图十五 北朝人物骑龙虎形象
1. 太原北齐娄睿墓壁画摹本 山西太原出土
2. 太原南郊壁画墓摹本 山西太原出土
3. 曹连墓石棺线描图 河南洛阳出土
此种以四神为核心的升仙队伍最早见于西汉中晚期洛阳地区的墓葬壁画中,如卜千秋墓脊顶壁画也是一幅连贯的神人神兽出行图像,前端以持节羽人为引导,中间主体部分为青龙、白虎、朱雀和神兽(玄武形象此时尚未定型或完整四神具有等级限制),后部也有乘骑神兽的一对男女,其中还出现西王母及其附属。其后的此类图像中出现了风雨雷电和河伯诸神等内容,并在东汉中晚期进一步发展成为内容丰富的庞大出行队伍。学界也多注意到北朝墓葬中此类神人神兽出行图像与汉代以来墓葬传统的紧密关系,有意见根据天帝和雷公等形象,进一步认为其为道教太一出行和雷部众神的表现。不过,目前所见只有极个别汉画像石中出现了天帝形象,在上述北朝壁画墓即便是作为帝陵的湾漳大墓中皆未见到。而且,如前所述,风雨雷电诸神在其中虽有一定重要性,但并非必要和核心内容,不论在汉代还是北朝皆是如此。更为重要的是,包括四神、风雨雷电和河伯诸神甚至天帝的升仙想象,自战国秦汉以来直至魏晋南北朝,在文献中有着连续的反映。如楚辞《九辩》云:“骖白霓之习习兮,历群灵之丰丰。左朱雀之茇茇兮,右苍龙之躣躣。属雷师之阗阗兮,通飞廉之衙衙。”“飞廉”即风伯。王逸注:“风伯次且而扫尘也。”《惜誓》云:“飞朱鸟使先驱兮,驾太一之象舆。苍龙蚴虬于左骖兮,白虎骋而为右騑。”《远游》云:“风伯为余先驱兮,氛埃辟而清凉。⋯⋯左雨师使径侍兮,右雷公以为卫。”此种驾驭四神、役使风雨雷电的升仙想象此后一直是汉代辞赋中不断重复和夸张的内容。除文学作品外,如《淮南子·原道训》云:“昔者冯夷、大丙之御也,乘云车,入云霓,游微雾。⋯⋯令雨师洒道,使风伯扫尘,电以为鞭策,雷以为车轮;上游于霄雿之野,下出于无垠之门。”这里的冯夷即是河伯。西晋傅玄《歌》云:“雷师鸣钟鼓,风伯吹笙簧。西母出穴听,王父吟安厢。”《云中白子高行》亦云:“超登元气攀日月,遂造天门将上谒。⋯⋯紫宫崔嵬,高殿嵯峨,双阙万丈玉树罗。童女制电策,童男挽雷车。云汉随天流,浩浩如江河。”仍然继续着这一传统。不过,南北朝正是道教迅速发展并扩展至上层统治者的重要时期,其神仙信仰自然也吸纳了上述传统内容。如北魏《化胡歌》云:“天龙翼从后,白虎口驰刚。玄武负钟鼓,朱雀持幢幡。”因此我们并不完全反对这些内容与此时兴盛的道教有关,只是更强调其与传统神仙信仰的一致性,不必从道教中新兴的某些特殊观念去理解。
(二)上层意义
如前所述,北朝墓葬中神人神兽出行图像的前两种尤其是第一种,在作为核心的四神之前尚有庞大的队伍和丰富的内容,与墓葬规模和等级呈现相应的级差之势。第一种中湾漳大墓规模最大,被普遍认为是帝陵,茹茹公主也为最高统治者的家庭成员,九原岗墓规模仅次于湾漳大墓,墓主虽有争议,但无疑为东魏北齐统治集团的核心人物。第二种娄睿墓的规模也颇大,墓主为北齐外戚重臣、东安郡王。第三种皆属于中等规模壁画墓,崔芬墓墓主为东魏威烈将军、行台府长史,属于中级官员,身份相对要低出很多。前两种墓道部分皆有规模庞大的仪仗出行队伍,与上部的神人神兽出行队伍正相配合。尤其是湾漳大墓和茹茹公主墓中,墓道下层的仪仗出行与上层的神人神兽出行队伍同由前端的龙、虎引导,一体性十分明显。众所周知,这些规模宏大的仪仗出行队伍皆出现在最高等级墓葬中,具有强烈的彰显身份的意义,那么,与之紧密配合的神人神兽出行队伍,是否也具有这一意义呢?
《韩非子·十过》中就说黄帝出行时有神人神兽护卫和扈从:“昔者黄帝合鬼神于泰山之上,驾象车而六蛟龙,毕方并辖,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后,腾蛇伏地,凤皇覆上。”黄帝同时具有天神和帝王两种属性,但汉代以来,这种想象被用于人间帝王的出行中,除了地上有庞大的仪仗队伍外,天上也有神人神兽队伍护卫和扈从。如班固《东都赋》在描写天子出行的宏大排场时说:“礼官整仪,乘舆乃出。⋯⋯山灵护野,属御方神,雨师泛洒,风伯清尘。千乘雷起,万骑纷纭。”张衡《羽猎赋》在描写校猎队伍时也说:“蚩尤先驱,雨师清路,山灵护阵,方神跸御。”“方神”即以四神为代表的方位神。如前所述,汉画像中的蚩尤正好可以由兽首人身的形象来表现。张衡《西京赋》云:“天子乃驾雕轸,六骏驳。⋯⋯于是蚩尤秉钺,奋鬣被般。”可见,此时的蚩尤确实为人兽结合的形象。再加上风雨雷电诸神,其内容和组合与本文所论神人神兽出行图像颇为一致。内容最为丰富的应数扬雄的《甘泉赋》《羽猎赋》《河东赋》,不仅包括上述青龙、白虎、风伯、雨师、蚩尤,还有飞廉、云师、雷公、电神、河灵、夔魖、蒙公、秦神及句芒、蓐收、玄冥、祝融等。其中,河灵或为河伯,或为河精。河伯在汉唐时期多作乘鱼出行的形象,并见于上述北朝神人神兽出行图像中。河精在敦煌佛爷庙湾西晋墓M1中被表现为兽首人身形象,已见前述。夔魖、蒙公,《文选》李善注引孟康曰:“木石之怪曰夔,如龙有角,人面。魖,耗鬼也。”又引如淳曰:“蒙公,髦头也。”秦神,《汉书》颜师古注引苏林曰:“秦文公时庭中有怪化为牛⋯⋯今之茸头是也,故曰秦神。”这些神祇的形象虽不能确知,但大体上也具人兽结合的特点。句芒、蓐收、玄冥、祝融,作为四方神的一种,为人首鸟身或兽身形象,在汉墓壁画中也有出现。赋中描写帝王“方驰千驷,校骑万师”的出行队伍,在这些“风发飙拂,神腾鬼趋”的神人神兽的护卫和扈从下,浩浩荡荡,“萧条数千万里外”。
汉代形成的这种对帝王出行排场的神奇想象也为魏晋南北朝所继承。如曹植《大飨碑》中描述帝王威仪时即云:“设天宫之列卫,乘金华之鸾路。达升龙于太常,张天狼之威孤。千乘凤举,万骑龙骧。威灵之饰,震曜康衢。”北魏李谐《述身赋》亦云:“王略恢而庙胜,车徒发而雷响。扇风师之猛气,张天毕之层网。”《周礼·春官·大宗伯》郑玄注:“雨师,毕也。”这里的“天毕”与“风师”(风伯)对举,自然指雨师。实际上,此种想象也有对天神出行的模拟。如北齐《高明乐》云:“辟紫宫,动华阙。龙虎奋,风云发。飞朱雀,从玄武。携日月,带雷雨。”统治者的出行队伍中,除有人间仪仗外,还想象有一套天上威仪,这恐怕也是此种规模庞大的神人神兽出行图像目前只见于帝、王级别的陵墓中,且与仪仗出行图像上下相承的原因。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北魏孝文帝和北齐后主都颇好辞赋,北魏迁洛以后也出现了阳固、李骞、李谐等一批辞赋家,且萧梁末年的动乱中,一批南方文士如颜之推、庾信等进入北朝,更是推动了辞赋的发展,但北朝总体上仍不能称为文学和辞赋发达。我们并不认为辞赋中的内容直接影响了墓葬壁画,而是认为上述辞赋中表达的此种对帝王出行的想象,也被表现在帝王墓葬的出行壁画中。作为一种虚拟的想象,其在辞赋文学中更能集中地表达,并非仅是辞赋中特有的内容。其实,中古时期帝、王出行仪仗中并非没有天界神人神兽的内容,只是主要表现于车马,尤其是旌旗羽葆的装饰上。正如前引曹植所云:“威灵之饰,震曜康衢。”又如北魏“制乾象辇,羽葆圆盖,画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天街云罕、山林奇瑞、游麟飞凤、朱雀玄武、驺虞青龙”,“又制象辇,左右金凤,白鹿仙人,羽葆旒苏”;北齐承北魏制度;北周“太常画三辰(日、月、五星),旂画青龙(天子升龙,诸侯交龙),旟画朱雀,旌画黄麟,旗画白虎,旐画玄武,皆加云气”;唐代卤簿旌旗上则有白泽(神兽)、摄提(神兽)、金鸾、狮子、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和风雨雷电等。后世大驾卤簿中也有同类内容,在一些传世画作中尚能见到〔图十六〕。现实出行中,这些内容绘画于旌旗羽葆之上,飘扬于空中,而在上述辞赋、绘画等文学艺术中,却可以独立表现并夸张铺陈,现实与想象通过不同的形式,表达着同一个天界威仪。
图十六 元佚名 《大驾卤簿图》(局部)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另外,前引扬雄《甘泉赋》《河东赋》和班固《东都赋》中描述的是天子祭祀、巡狩时的出行队伍,扬雄《羽猎赋》和张衡《羽猎赋》《西京赋》中则是描述校猎时的出行队伍,而忻州九原岗大墓和太原娄睿墓墓道下部出行队伍中,除有仪卫外,还有突出的狩猎内容,是否也具有关联,尚待将来进一步讨论。
综上所述,东魏北齐时期大中型壁画墓中出现了较为突出的神人神兽出行图像,作为墓葬壁画的主要内容之一,过去的关注尚不够全面和深入。可按分布位置和丰富程度分为三种,并与墓葬等级密切关联。第一种连续分布于墓室、甬道和墓道上部,规模宏大、内容丰富,出现于帝陵和相近等级的墓葬中;第二种连续分布于墓室、甬道上部,可能由天井向上延伸,内容较为丰富,墓主为外戚重臣、郡王等级;第三种仅分布墓室上部,内容较少,只在龙、虎前后有少数神人神兽,墓主为中级官员。虽然规模有很大差距,但其核心——即墓室部分以四神为主的内容则高度一致。龙、虎和玄武背上往往有神人乘御,显示出共同的护卫和扈从升仙的意义。前两种尤其是第一种的神人神兽继续向甬道、天井和墓道上部延伸,形成包括风雨雷电和河伯诸神等的庞大队伍,但仍以墓室部分的四神形体为最大,皇室陵墓的墓道前端还见有一对形体颇大的龙、虎为先导。以四神和风雨雷电及河伯诸神引导和扈从升仙的图像,自汉代以来即流行于墓葬之中,也与文献中战国秦汉以来的升天游仙想象高度一致。除了升仙这一基础意义外,庞大的神人神兽出行队伍分布于帝、王陵墓的墓道上部,与其下部的仪仗出行队伍相配合,共同表现着墓主超凡的身份。汉代以来,人们想象帝王出行时,天上也有包括蚩尤、四神、风雨雷电和河伯诸神等的众多神人神兽护卫和扈从。这在现实中自然不会出现,往往只能在旌旗羽葆上描绘,但在文学和壁画中正好可以表现出来。因此,这些神人神兽出行队伍,一方面既显示了出行的目的——神仙世界,另一方面也彰显着出行者的身份——天神威仪。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神人神兽引导和扈从升仙与统治者出行的想象,皆承自汉代,但二者在当时似乎并未结合起来,墓葬图像也未形成一定制度。一方面,汉代规模较大的神人神兽出行图像并非高等级墓葬特有,甚至未见于等级很高的墓葬,反而在卜千秋墓这类中小型墓葬中有较多出现。另一方面,蔡邕《祖饯祝》亦云:“鸾鸣雍雍,四牡彭彭。君既升舆,道路开张。风伯雨师,洒道中央。阳遂求福,蚩尤辟兵。苍龙夹毂,白虎扶行。朱雀道(导)引,玄武作侣。勾陈居中,厌伏四方。往临邦国,长乐无疆。”看来,此种出行想象也未必专用于统治者。但上述北朝壁画墓中神人神兽出行图像的等级性却是一目了然的,类似内容在南朝画像砖墓中也具有明显的等级性,只是南朝陵墓相对简素,不如北朝铺陈〔见图八〕。这些内容在西安地区唐代前期高等级墓葬中还有孑遗〔图十七〕。这也可以作为南北朝墓葬文化中继承甚至复兴了许多汉墓内容,并将其发展和部分制度化的又一例证。
图十七 唐代高等级墓葬中的神兽出行壁画
1、2. 懿德太子墓墓道青龙、白虎陕西乾县出土
3. 长乐公主墓墓道西壁云中车马(摹本) 陕西礼泉出土
4、5. 节愍太子墓甬道券顶神禽 陕西富平出土
值得注意的是,过去对东魏北齐墓葬壁画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墓葬下部,如墓室正壁的墓主人像,两壁的牛车、鞍马及高等级墓葬中延伸至墓道的仪仗队伍,认为已经形成较为统一的图像逻辑——即墓主出行。根据本文的讨论,至少墓葬上部的神人神兽出行与下部的墓主出行密切相关,甚至属于一个更大的图像逻辑。墓室两壁的牛车、鞍马象征着墓主出行的核心,而其上部的神人乘骑龙、虎也是神人神兽出行的核心;高等级墓葬的仪仗队伍在墓道下部延伸,而神人神兽出行队伍又在其上方延伸,似乎可以拓展墓主出行的图像逻辑。这里的出行应该同时承载彰显身份和升仙两种愿望,这两种愿望并非上下截然分开,而是统一甚至交织在一起。只是一方面所有墓葬的顶部天象壁画保存过差,几座重要墓葬的墓室壁画也基本脱落或保存不一,目前只能相互对照,进行推测;另一方面北朝政权变动频繁,制度和文化的连续性也不及南朝,陵墓壁画布局的稳定性和延续性也需要谨慎〔图十八〕。不过已可提示我们对于北朝墓葬壁画布局和意义的考察,还应该将顶部和上部与天界相关的内容综合起来加以考虑。
图十八 北齐陵墓壁画布局推测示意图
作者制,底图采自前揭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著《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第6页
[作者单位:王煜,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雷嫣然,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硕士生)]
(责任编辑:谭浩源)
*本文系202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考古所见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天文材料的整理与研究(” 项目编号:21AKG009)的阶段性成果之一,受到四川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双高计划”资助。
论文完整注释信息请检阅纸本期刊正文。
#artContent h1{font-size:16px;font-weight: 400;}#artContent p img{float:none !important;}#artContent table{width:100% !import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