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者身份之形塑*
吴门绘画中有不少作品专为医者而绘,突出特点是在山水中融入芝、鹤、丹灶、杏树等典型元素以凸显受画人的职业身份。该现象在吴门绘画之前与之后皆属罕见,以往关注亦不多。考察相关作品及其缘起,有利于探索吴门画家如何运用画史资源来制作一件与受画人身份乃至审美趣味相契合的作品;深入对出现了类似元素但受画者及使用情境尚不明作品的探查;亦有助于理解医者群体对自我身份的认知及其地位在明代的变化。
《芝鹤图》轴〔图一〕、《为祝淇作山水图》轴〔图二〕与《南山祝语图》卷〔图三〕这三件沈周(1429-1509)画作有许多共同之处。一是从功能来说,皆为祝寿图;二是画面皆为山水与人物小像的组合,尤其人物面部都得到了相对充分的描绘,具有较为鲜明的肖像特征;三是受画人也即像主皆为医者。三作中,芝、鹤、丹灶、杏树等元素位置醒目、刻画充分且与像主存在互动关系,唯有将受画人的职业身份考虑进来,才能更好地体察画家经营的匠心。
图一 明沈周 《芝鹤图》 轴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二 明沈周 《为祝淇作山水图》 轴
浙江省博物馆藏
图三 明沈周 《南山祝语图》 卷
故宫博物院藏
约作于15世纪80年代的《芝鹤图》,画面兼具山林之清幽与庭园之雅致,像主被安置在竹丛与溪水之间,背靠大石,姿态放松地斜倚在低矮的石榻上,虽正面面向观者,眼睛却看向榻旁生长出的红色芝草。与芝草隔岸相对的,是一只立鹤,芝鹤二者占据的画面空间虽不大,却位于画面下部正中位置,即像主与观者目光交汇处。画面右上画家题诗并落款:“已知仁术寿生涯,医国高垣㮣太霞。小住人间一千岁,青精为饭酒松花。乡生沈周奉寿璞庵先生金石之筭。”可知画与诗是为一位医官璞庵贺寿所作。诗中盛赞这位医官医术高明,将其比拟为以药草为食的仙人。
文人素有养鹤的传统,但园林中不会随意长出芝草。仙气十足的芝、鹤与医者的渊源颇深,早在宋代以前,医疗即与仙道紧密相关,医者与神仙、异人比列。在元人的叙述中,依旧可见将医者与学仙者并举的例子,而采芝、养鹤等意象,也常见于时人投赠医者的诗作中。明初陈循曾在一幅《采药图》上题诗赠予一位医者,此图的样式,或可从发现于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的辽代《采药图》轴〔图四〕推想一二。图中人物从发型、服饰来看应非凡人,其右手所持及背篓中所盛皆为芝草。
图四 辽佚名 《采药图》 轴
1974年发现于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
芝、鹤二者的组合出现,以往多见于仙山图。元末陈汝言的《仙山图》卷描绘了在芝草遍地的松林间观赏双鹤起舞的仙人〔图五〕。仙人斜倚的姿态与沈周笔下的医者璞庵可谓如出一辙。作于正德二年(1507)的《为祝淇作山水图》中,沈周基本延续了《芝鹤图》的图式,描绘像主祝淇(1418-1508)与款步前行的衔芝鹤于山水间的互动。
图五 元陈汝言 《仙山图》 卷 (局部)
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
两作中,沈周的创新之处不在于借鉴仙山图像来为医者祝寿,而在于以文人趣味对既有图式进行改造,塑造出兼具文人气质与职业特色的医者形象。《芝鹤图》中,璞庵先生一袭白袍,衣襟半敞,既带有几分仙风道骨,又酷似古代高士,而背后的竹石、身畔的茶炉、头上的幞头、身下的草席,则为其增添了更多的文士气质。而《为祝淇作山水图》中,祝淇则被描绘为身着红色官服、头戴官帽、正襟危坐的形象,身后放置着一摞书籍。精于医术的祝淇自少时即业儒,但他本人未有功名,只因其子祝萃的功绩而被封为刑部主事,即沈周贺诗中所言“九十封君天下稀”。画家巧妙地将祝淇的官员、儒者、医者身份呈现于一幅画面之中。
未署年款、从画风来看应为沈周晚年之作的《南山祝语图》,据卷后王鏊题跋可知是为医者韩世光所作。有别于前两作中的芝鹤组合,此作以杏树、鹤、丹灶的组合来凸显受画人的医者身份。画面起首处的树丛中便藏着两株杏树,但描绘得不若画幅中段像主侧前方、山岩间斜伸出的那株精细,后者与沈周作于弘治十五年(1502)的《杏花图》轴(故宫博物院藏)中的杏枝形态颇为相似。此处杏树的作用既非点明季节,亦非寓意儒生高中,而是指涉与医者关系更为紧密的种杏、杏林等典故,与位于像主斜后方的鹤遥相呼应。在杏树、鹤所围合的空间中,头戴方冠、作道士装扮的韩世光跽坐于石台之上,面前是一座丹灶。丹灶、丹炉本是修道学仙者炼制丹药的核心仪器,但与采芝、采药一样,后来逐渐成为与医者紧密相关的意象:在元末明初医者韩奕的《次韵医家十六咏》中,便有分题采芝、丹炉等诗;胡奎的《赠医士长律十首》中,亦有分题丹灶、芝田者。
沈周并非要将韩世光塑造成出世的修道者。观者展卷时首先看到的是掩映在山石松林间的书斋,斋中桌案上放置着琴、书,另一侧桌案上有铺开的纸。这是一间典型的文人书斋,即卷后王鏊提及的云堂:“韩君世光作堂,扁之曰云。”题跋中,沈周与王鏊皆落脚于仁:“无心结伴似有义,济物事医还得仁。”“惟君之先世为良相,今为良医,其有似于云乎。相之泽及于四海,医之惠及于一方。广狭不同,同归于仁。仁而不自以为仁,故有似于云。”画、诗、文同共塑造了韩世光的医者仁心与儒者仁术。
从明代医者为自己选择的别号、斋号中,亦可窥见他们对职业身份的认同与自我形塑。有以存仁、春雨为号者,亦有号芝岩、芝田者。沈周约作于弘治六年(1493)的《芝田图》卷〔图六〕应是送给医者的别号图。该图采用了流行的斋室图样式,书斋中一文士持卷独坐,与之一水相隔的是一片田地,田中生长着朵朵灵芝。卷后沈周题云:“董家报德人栽杏,天报君家芝满田。”以董奉医术高明、病人栽杏为报的典故,点明受画人的医者身份。姚绶题云:“忽见华芝秀,何妨种术田。医家能积累,和气在生全。”朱绶题云:“种德心田那有期,西溪俄见产琼芝。能医人世皆难老,不比商山只疗饥。”原本长于仙山的灵芝,由于医者的德行而出现在田间,延续了芝草作为祥瑞现世的传统。
图六 明沈周 《芝田图》 卷
故宫博物院藏
吴门医者王观(1448-1521)早年以杏圃为号,后改号款鹤。唐寅(1470-1524)为其作《款鹤图》卷〔图七〕。画面突出了一种荒寒不毛的景象,唯像主所在之处生机昂然,以树木之荣枯凸显生命力之有无。像主于茂密的树阴下伏石案而坐,正看向一只鹤,鹤曲颈俯首,前爪略伸,后爪离地,似在回应主人,又似在起舞。与鹤为友,观鹤起舞,常见于仙山图像,然像主的文人衣冠、石案上摆放的纸张文房与一旁煮茶的童子,又共同营造出一副消闲士人的模样。卷后沈周题诗亦兼顾了蓄鹤、茹芝的医者意象与种竹、读书的儒生形象。
图七 明唐寅 《款鹤图》 卷
上海博物馆藏
总体来说,前述诸作塑造的是儒医形象,而唐寅约作于16世纪初年的《烧药图》卷〔图八〕描绘的医者,则更接近修仙学道者。画面绘像主端坐于崖顶松下兽皮上,头戴方冠、身着道袍,左手持卷,右手拈一丸,目视正散发着热气的丹炉,炉旁的童子一边扇火,一边回首望向像主。丹炉位于平坦开阔处,后方是一山洞,洞中有泉水涌出。画面所绘幽僻环境与传为仇英的《玉洞烧丹图》卷(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卷末场景相似。但卷末唐寅题诗中所用种杏、春雨等典故及“老我近来多肺疾,好分紫雪扫烦襟”句,应是指向医士。卷后另纸有祝允明题《医师陆君约之仁轩铭》。明人斋名、别号往往合二为一,故陆广当以仁轩为号。“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据载陆广行医的特点为“辅以儒术”,这与唐寅笔下的人物形象存在较大差异。张丑曾著录过一件唐寅《炼药图》,其中唐寅题诗与存世《烧药图》一致,却无祝允明题,而有刘浣的诗跋。据张丑所言,此作为其父张应文所藏,因“中岁慕道,故蓄《炼药图》以自况”,可知张应文即将像主理解为一位修道者。祝允明之题或从别处移来,亦未可知。
图八 明唐寅 《烧药图》 卷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张应文对唐寅画作的理解与使用,提示出这类为医者绘制的作品,在脱离初始语境和受赠关系后,可能面临的新解读与原有意涵的被遗忘。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文伯仁《丹台春晓图》卷〔图九〕或与之类似。画面起首绘山水清幽之景,末段崖顶处绘一座丹炉,炉旁侧立一人,衣袂飘举,当为受画人写照。像主身后的书斋在树木掩映下仅现屋顶,童子沿山路而行。因画面出现丹炉与修道者的形象,以往多将之归入道教绘画。值得注意的是,童子右手持有盛放着芝草的篮子,并一鹤嘴锄,这延续的正是采药图像的传统,而采芝与丹炉皆与医者职业身份关联紧密。推测文伯仁此作极有可能是赠予一位医者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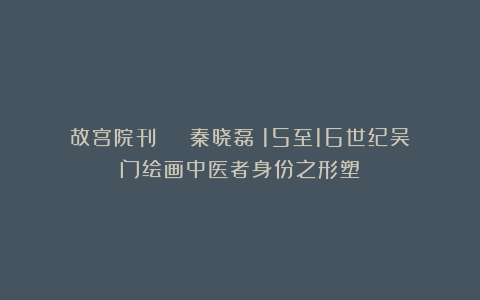
图九 明文伯仁 《丹台春晓图》 卷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成化十五年(1479),史鉴致书沈周,请其作一诗一图,以报陈颀治愈儿子史永龄之恩。业儒并曾任县学教官的陈颀出身于世医之家,休官后以医术自给,正与前述医且儒的人物形象相合。沈周应史鉴之请作《种杏图》并诗,史鉴复题诗一首,赠予陈颀。画虽不存,但从画名可知为病人种杏以报董奉的典故。据《神仙传》记载,董奉“为人治病,不取钱物,使人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轻者一株。如此数年,计得十万余株,郁然成林”。二人之诗与沈周之画皆意在赞颂陈颀的仁心与仁术。清人缪曰藻曾寓目一件唐寅《瞻杏图》,据题跋可知为画家应李毓秀之请答谢钱孔元愈子疾而作。
至晚在元代,《种杏图》《杏林图》等便已成为适宜赠送医者的绘画类型,刘崧曾题跋钱叔昂所作的《杏林图》以寄赠医者林元英,并为一位姓丘的医者题跋其所藏的《种杏图》。元代及之前的《杏林图》《种杏图》面貌不详,或可从南宋马麟描绘了水边杏林的《芳春雨霁图》页(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推想一二。明初,王直曾请金幼孜、杨士奇等人赋诗题咏《五杏图》,以赠予太医院院判蒋主善。金、杨二人皆在诗中将蒋主善比拟为董奉,据杨士奇所言,此图乃是一位中书舍人所作。蒋主善自洪熙元年(1425)始任院判一职,此时王绂业已离世,这件《五杏图》或为受其影响的陈宗渊或其他善画者应王直要求所作。沈周、唐寅应人之请作答谢医者的《种杏图》《瞻杏图》,皆可视为对这一传统的延续,惜二图今已不存,或可从唐寅作于正德十六年(1521)的《观杏图》轴(苏州博物馆藏)推想一二。画面描绘一位高士侧立于两株古杏及湖石围合的空地上,作拈须仰观状,身旁边二童子备茶、奉茶。
韩奕曾为一位精于儿科的医者作种杏轩诗,种杏轩当为这位医者的斋室名。以种杏、杏林等为斋名的医者为数不少,沈周曾为医者戚宗式作杏林书舍诗,亦很可能作有画,诗即题于画上。杏林书舍乃戚宗式为教子行医而设,沈周诗云:“设教开医沸一堂,君家父子为仁忙。松梢露碧临窗研,杏树花红隔水庄。”这与沈周约作于成化十七年(1481)的《杏林书馆图》轴〔图十〕画面颇为契合。该图采用了元代以来流行的立轴式书斋图样式,绘山峰下一处为树木、溪水环抱的幽静馆舍,一文士端居斋中读书,舍外一人持杖过桥而来。馆舍四周的树木中,以杏树居多,画家对其进行了重点刻画,以点明主题及凸显画作受赠人的职业身份。据画心上方诗塘处徐源题跋,可知此作为葛行简答谢医者陈公尚(1433-1500)之作,因其“二子在襁褓时,多疾,几不免,赖其剂而全矣”,故求得沈周之画与徐源之赋报答。陈公尚出身于世医之家,善长小儿医,后被征入京,擢为院判,吴宽曾为作《慈幼堂记》。在为另一位同善小儿医的钱甫所作墓表中,吴宽记述其居住环境“前临长溪,后带广圃,圃中竹树甚茂,而杏为多”,故以杏园为号,可见当时医者对自我形象的主动营造,而相关诗画作品亦并非引用典故的纯然虚构。
图十 明沈周 《杏林书馆图》 轴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在归于仇英名下的多胞作品《东林图》卷、《画园居图》卷(皆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等中,有对杏林的描绘〔图十一〕。画面起首绘幽雅的园居,主人于斋中会友,童仆在外备茶。从竹树枝繁叶茂的程度来看,当为春夏之季,卷末却出现了与时令不符的盛放杏树形象,应对受画人具有特殊意义,画家因而作了艺术化处理。《东林图》中靠近书斋的一株被刻画得格外精细,而卷末溪边的杏林遥接马麟《芳春雨霁图》的传统,在远山映带下,与沈贞写给医者仁斋的诗中之景十分契合:“杏花千树门前路,仿佛桃源小洞天。”文徵明为医者王闻所作《存菊图》的仿本颇多,仇英名下的这些作品,也可能出于类似情形。
图十一 明仇英 《东林图》 卷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除芝鹤、丹灶、杏树等典型元素外,在15-16世纪吴门画家为医者绘制的画作中,也有以其他元素来形塑医者身份或未体现其职业特点的。成化五年(1469),贺甫欲答谢医者杜祥(1429-1510)治愈其子之病,应杜祥之请求沈周父子画作,贺甫找来杜琼等人一同去沈宅求画,途经刘珏宅,刘珏先为作一图,沈周复作,杜琼再作,沈贞补笔于杜琼之作,贺甫合三图为一卷持赠杜祥,即《报德英华图》卷。杜琼、沈周二作皆采用了自元末起流行的书斋图样式与一水两岸的构图,所绘物象亦相似,但沈周重点刻画了端坐于书斋中的像主,并于斋中设一药柜〔图十二〕,以凸显其职业身份。这是吴门绘画中着意形塑医者身份的较早例子。
图十二 明杜琼、 沈周等 《报德英华图》 卷 (局部)
1469年 故宫博物院藏
天顺八年(1464)沈周为孙叔善所作《幽居图》轴(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描绘山居清幽之景,由周本题诗中的“思邈移家住远村⋯⋯杏花踏碎春风里”、沈召“闻说丹丘在人世,杏花深处即仙家”等句,可推知受画人应为居于乡间的医者。永乐十五年(1417)谢缙为医官盛寅作《云阳早行图》轴(上海博物馆藏),画心上方题跋者中,蒋用文、刘溥二人亦为医官。画面绘山水间携童仆赶路的旅人,并未出现点明医者身份的物象。这些画作显示出此时医士与儒士交往的深入程度。以沈周为例,与他往来密切的医者或善医术之人,有韩襄、王观、刘毓、周庚、陈颀、周本等。沈周曾作诗画答谢刘毓治愈弟弟沈召,并在其出任医官后寄赠《蕙花芙蓉图》并诗。韩襄出身于吴门有名的世医之家,沈周家族与之数代相交,韩襄曾为沈周伯父沈贞、妻陈慧庄诊病,在沈周生病时遣子问候。沈周尊韩襄为兄,为其绘制了许多精心之作,如《荔柿图》轴(故宫博物院藏)、《西山有虎图》《雪馆情话图》等。前述《南山祝语图》的受画人韩世光应为韩襄之子或侄,沈周曾与其同游虎丘,还曾在成化二十三年(1487)赠画册予他,并亲切地称呼其为“世光贤侄”。沈周还曾应韩襄之请为其孙韩宗福制作诗画册页。杜琼则与韩襄的从兄医者韩克美往来密切,曾诗咏其别号梅窗,或许也曾作画。在赠给医官刘溥的画作上,杜琼以一首长诗叙述自身画艺源流,足见对刘溥的重视程度。除作《存菊图》外,文徵明还曾为王闻书《金刚经》,为医者葛汝敬作《闲舟图》,为医者沈廛撰墓碑碑阴记文,为陈公尚之子、医官陈宠所编的族谱作序等。
此时部分医者在生活方式和审美趣味上已高度文人化。周庚在凭借医术被征召之前喜读书,任医官后仍业文不废,沈周曾为作《仿王蒙山居图》。陈颀因出身于世医之家的生母韩氏早亡,继母王氏出身儒门,并受业于舅王应良,故成年后业儒。沈周曾题跋陈颀所藏的燕肃《楚江秋晓》卷,陈颀曾题跋沈周家藏的《林逋手札二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等。与沈周、文徵明交好的医者沈律,家富收藏,沈周曾为他作《溪亭秋晚图》。王观所藏“翰墨卷轴,充箱盈目”,其中有米芾《苕溪春晓图》、扬补之《墨竹图》等。
在吴宽等人为医者所作的记文、行状、墓铭等中,除记述其医术高明外,亦着重强调他们拥有的儒士品格,如陈颀“不若世俗之医之计利也”、陈公尚“为人谦谨,人皆重之,非特以医而已”,并明言韩氏、盛氏等吴门世医之家历来多出儒医:“自永乐以来,若韩氏曰公达、公茂,盛氏曰叔大、启东,刘氏曰原博、宗序,至沈以潜、张致和、钱伯常、刘德美、周原己,相继而出,多以儒医称,非寻常俗工可比。”儒医概念形成于宋代,至明代愈发受到重视。儒医因重义轻利而与仅有技术的俗医区别开来,受到时人追捧,这同时透露出医者虽为人所需,但所处社会阶层并不高。医者与文人、画家的交往,一方面有助于提高自身地位、树立儒医的形象,另一方面在病患寻求救治时极重医者声望的背景下,也有利于其职业生涯的展开。从修撰于隆庆年间的《长洲县志》中对韩襄的评价可窥见一二:“韩襄⋯⋯神医张志和子婿也。襄医差亚于志和,有高行,与沈周为莫逆交。凡周贻襄染翰,皆出奇品,人以此益重之。”
医者与文人、画家的交往,自有其时代渊源。一方面宋代医者逐渐从宗教身份中脱离出来,渐受士人之重视;另一方面元代科举之路不畅,许多文人被迫以技艺谋生,寄身于医术、画艺者颇多,许多人甚至身兼数职。明初画家王履在当时更广为人知的身份是医者,与他齐名的吴门医者王宾亦善作画。另外,明代医者、画家的社会地位相近,在这一时期修撰的方志中,二者往往同被归入人物志中的艺术类。吴门画家与医者的交往及相关作品的绘制,正是在上述脉络中展开。
明代吴门多名画家,亦多名医。从沈周著有《续千金方》来看,他本人似亦通医道。文徵明长子文彭娶世医家族钱氏之女为妻;女婿王曰都为王观的侄孙,曾从其受业,后应诏被授太医院医士。因身份地位相近,吴门画家在与医者交往的过程中,敏锐地捕捉到该群体对提升职业地位与自我形塑的需要,约自15世纪中叶起,有意识地在画面中融入能够体现其医者身份的元素,创作出一批极具特色的作品。其中既有《杏林书舍图》《种杏图》这类较多沿续前代酬谢医者题材的作品,也有《芝鹤图》《南山祝语图》等从前代仙山绘画中寻求灵感之作;既有《芝田图》《款鹤图》等塑造理想儒医形象之作,也不乏《烧药图》这类展现医者修仙学道这一传统形象的作品。
与文人画家这一概念相类,儒医虽是具体的社会存在,却无明确标准界定其成员身份。然而儒医区别于普通医者的形象在吴门画家笔下得到了确立。画家在为其作画时,充分考虑了该群体的内心期许与审美趣味。画面中与文人、逸士别无二致的像主身边,常伴有芝、鹤、杏树、丹灶等元素及其组合,发挥着点明像主职业身份的作用;对于今天的观者来说,受画人的医者身份则是理解这些符号的关键。进而推测,出现了类似元素及其组合的文伯仁《台丹春晓图》、归于仇英名下的《东林图》等作,原本也是为医者而作的。受画人及其身份、趣味可以成为理解吴门绘画的一个角度。
图十三 明仇英 《茹芝图》 扇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相关作品及图式在15至16世纪的吴门地区格外流行,仇英的《茹芝图》扇〔图十三〕、《采药图》扇(皆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以青绿设色描绘山水间像主与芝草、杏树图像的组合,将书斋图与采药元素进行融合的做法,也隶属于这一脉络,可知其受欢迎的程度。文徵明的《存菊图》后世仿作颇多,透露出这些原本为医者绘制的作品,或许也曾受到更广阔人群的喜爱。直到17世纪,仍可见对相关图式及元素的运用。张复作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的《雨过芝田图》轴〔图十四〕,画面下部绘一老者隔岸观望生长出芝草的田地,上部绘童子入深山采药,题云“雨过芝田长,云深药迳重⋯⋯寿道澈先生”,结合画面内容与诗句来看,像主应是一位医者。陈祼于天启七年(1627)为陈继儒绘《苕帚庵种芝图》轴〔图十五〕,该图在山水形态与笔墨上摹仿赵孟頫《鹊华秋色图》卷(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图式上融书斋图式与采芝形象于一作,生动地说明了此时通医道、懂养生,已成为文人用于自我标榜的雅趣之一。
图十四 明张复 《雨过芝田图》 轴
1616年 江苏省美术馆藏
图十五 明陈祼 《苕帚庵种芝图》 轴
1627年 美国芝加哥艺术博物馆藏
[作者单位: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编辑部]
(责任编辑:盛洁)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一般项目“吴门绘画及其受众研究”(项目编号:23BF082)阶段性成果。
论文完整注释信息请检阅纸本期刊正文。
欢迎读者阅读、选购纸本期刊。
敬请阅读:
秦晓磊《15至16世纪吴门绘画中医者身份之形塑》,原文刊载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2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