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子皇女
按照清朝祖制,皇子出生,无论嫡出还是庶出,一落地,就会有老妈子抱出产房,交到奶妈手上。
一位皇子按例需要使用四十人伺候,其中老妈子八人,奶妈八人,此外还有所谓的针线上人、浆洗上人、灯火上人、锅灶上人等等。
等到皇子断奶后,就不用奶妈了,增添一些内宫太监作为“谙达”,教皇子吃喝、说话、行走,也教他一些礼节。
等皇子六岁,就准备小帽子小袍褂小靴子,教他跟随大家站班当差,教他上学,也就是去上书房。黎明就起床,穿衣戴帽从容进入乾清门,夹杂在一群王爷中间,站立在大殿上的皇帝面前。
路过的门槛都不准跨过去,都是内侍把他举起来放进门里。其中如何左顾右盼,表现出大方的仪态,走出优雅的步伐,这些都是要“谙达”们教他的。
皇子自从出世,就不与生母相见。每年见面也有固定的时间,见了也不能多说话,不像民间子女可以随时随地与父母亲近。
到了十二岁,又有说满文的“谙达”教他国语。到了十四岁,就必须教他弓马骑射。到了十六或十八岁,就要成婚了。
如果此时父皇在位,那么皇子们就要群居在青宫,这地方就是俗称的阿哥所了;如果皇帝驾崩,皇子就带自己的生母还有妻子分府而居。母亲是嫡皇后就不用搬出去,因为儿子已经登基正位,会供奉她为皇太后。
按:皇子自襁褓到成婚,母子相见总共不超过一百多次,又怎么会有感情呢!如果是皇女,那就比皇子更加疏远,从落地到出阁,仅跟母亲见面几十次而已。
更奇怪的是,每当公主出嫁,就会赐给府第,不跟公婆住在一起。公婆还要以见皇帝的礼数拜谒儿媳。驸马住在公主府的外间屋子,公主不宣他进来,夫妇俩就不能同床共枕。每宣召一次,公主及驸马一定要花很多钱财,这才能够相聚。权力都在老妈子那里,就是人们所说的那种管家婆。
公主如果不贿赂老妈子,就算有所宣召,老妈子必定想办法从中作梗,甚至斥责公主无耻不要脸。女子多是怯懦而软弱的,怎么能不被她们所牵制。
就算入宫见到母亲,公主也不敢告状,本来就有所隔绝,没办法说心里话,就算说了母亲也不会听。所以清代公主基本没有生儿子的,就算有,也是驸马的侧室生的。
如果公主死在驸马之前,驸马就会被逐出公主府。府第的房屋、器具、衣饰全都被收回宫中。除了房屋之外,其它的东西被老妈子私吞的,难以计数。
所以,清代公主大约十个人有九个是因为得相思病死去的。清代公主子女众多,而又夫妇和睦像民间夫妻的,两百年来只有清宣宗的大公主和他的丈夫符珍。
大公主刚刚出嫁时,召见驸马,也被老妈子所阻拦,一年多见不到驸马的面。大公主非常愤怒,隐忍着不吭声。
有一天进宫,大公主跪在清宣宗面前,问道:“父皇究竟将我嫁给了什么人?”
皇帝说:“这话问得奇怪,符珍不是你的夫婿吗?”公主问:“符珍长得什么样?我已经嫁出去一年多了,还没有见过他呢。”
皇帝惊讶地问:“为什么没见过?”大公主说:“老妈子不让我见他。”皇帝更加奇怪,说:“你们夫妇的事,老妈子们怎么管得到?你自己做主就行了。”
公主得到皇帝这句话,回府后立即斥责老妈子。她召来符珍,两人伉俪情深,十分和睦,生了八个子女。这可算是有清以来的首屈一指。由此可见,公主夫妇相隔难以见面,皇帝并不知情。
二百年来的公主,都没有这样的厚脸皮,所以总是一忍再忍,最后独自伤心而死。管家婆虐待公主,比老鸨虐待女妓还过分。然而宫中如果不授权给她们,让她们“照应”公主,她们也不会如此作恶。所以“照应”这两个字,也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不是太可怕了吗,不是太可笑了吗!我非常钦佩大公主,不愧是女中豪杰。也有人说,清代对待皇子和公主这两件事,也是沿袭了明代的制度。
(出自《清代野记》)
吸毒石
《左传》上说:“深山老林,大片的湿地水域,应当是龙蛇生长的地方。”小奴玉保是乌鲁木齐流放犯人的儿子。起初隶属于特纳格尔军屯。
有一次追寻丢失的羊,玉保追到了山谷里,看见一条蛇,有房柱子那么粗,盘在高岗顶上,向着太阳晒身上的皮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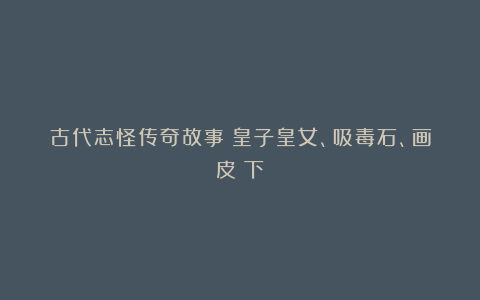
那蛇全身五颜六色,好像堆着的锦绣;蛇的头顶上长了一只角,有一尺左右长。有一群野鸡飞过,大蛇张嘴一吸,虽然相距四五丈远,野鸡却轻飘飘落了下来,像是往壶里投箭一样准确无误地进了蛇口。
玉保心里明白,羊一定就是被这条蛇吞了。他趁着蛇没看见自己,沿着山涧逃了回来,吓得差点儿丢了魂。
军吏邬图麟说这种蛇最毒,但它头上的角能解毒,那东西叫吸毒石。
见了这种蛇,可以用几斤雄黄在蛇的上风头烧,蛇一闻到气味就浑身酥软不能动弹了。这时,可趁机取下它的角,锯成一块块的,在痈疮刚发作的时候,贴一块在疮顶上,它就像磁铁吸铁一样粘住不掉。
等把毒气吸出来时,它就自己掉下来了。把它放在人奶里,浸出里面的毒,还可以再用。毒轻一点儿的,奶会变成绿色,重一点儿的变成青暗色,最重的就变成黑紫色。
奶变成黑紫色的,要吸四五次才能把毒吸干净,其他的吸一两次就行。
我记得堂兄懋园家里有吸毒石,治疗痈疽很有效。它的质地既非木头,也非石头。听邬图麟这么一说,我恍然大悟,原来吸毒石就是蛇角。
(出自《阅微草堂笔记》)
画皮(下)
(接上期)道士问他说:“你家可曾有一个不认识的人来?”二郎回答说:“我一早就到青帝庙去了,实在不知道。等我回家问问。”去了不多时又返回来,说:“果然有这事。早晨有一个老妇人来过,她想给我们家当仆人,操持家务,我妻子留下了她,现在还在家中。”道士说:“就是这个东西。”于是同二郎一块去了南院。
进了院子,道士手握一把木剑,站在院当中,大喝道:“孽障!赔我的拂尘来!”那老妇人在屋里,吓得惊慌失措,面无血色,窜出门想逃。
道士追赶上一剑砍去,老妇人倒在地上,身上的人皮哗的一声脱落下来,变成了一个恶鬼,躺在那里像猪一样嗥叫着。道士用木剑砍下恶鬼的头,鬼的身子化成一股浓烟,在地上旋成一堆。
道士取出一个葫芦,拔下塞子,放在烟中,只听嗖嗖地像吸气一样,眨眼间浓烟便都被吸进葫芦里去了。道士把葫芦口塞严,装进口袋里。大家看那张人皮,眉眼手脚,一样不缺。
道士卷起人皮,发出像卷画轴一样的声音,也装在口袋里,便告辞要走。陈氏迎门跪拜着,哭求道士救活王生。道士推辞无能为力,陈氏更悲伤了,趴在地上不起来。
道士沉思了一会,说:“我法术浅薄,确实不能起死回生。我指给你一人,他或许能救活你丈夫,你去求他,肯定会有办法。”
陈氏问:“是什么人?”道士说:“集市上有个疯子,时常躺在粪堆里。你去求他试试,他若侮辱你,你也不要生气。”二郎也听说过这个疯子,于是告别了道士,同陈氏一块去了。
到了集市上,见一个疯乞丐在路上颠颠倒倒地唱着歌,拖着三尺长的鼻涕,脏得让人不敢靠近。
陈氏跪着爬到他跟前,疯子笑着说:“美人喜欢我吗?”陈氏讲了缘故,疯子又大笑着说:“人人都可以作丈夫,何必非得救活他?”
陈氏苦苦哀求,疯子叫道:“怪哉!人死了,求我救活他,我是阎王爷吗?”生气地用木棒打陈氏。陈氏忍痛挨打,集市上的人渐渐围拢过来,像堵墙一样围着他们。
疯子咳了口痰,吐了满满一把,举到陈氏嘴前说:“吃了它!”陈氏脸涨得通红,面有难色。继而又想到道士的嘱咐,只得硬着头皮吃了。
咽到喉中,觉得像团棉絮,叽哩咕噜咽下去,最后堵在了胸口间。疯子大声笑着说:“美人喜欢我哟!”接着站起身,头也不回地走了。陈氏在后面跟着,见他走进庙里。陈氏进去一看,不知到哪里去了;前前后后仔细搜寻,竟没一点踪影。陈氏又惭恨又羞愧地回去了。
回家后,陈氏既痛心丈夫死得惨,又悔恨吞痰的羞辱,哭得前仰后台,只求一死。她想给丈夫擦洗血污,收尸入棺,家里人都远远地站着看,没有敢靠近的。
陈氏抱着丈夫的尸体收拾肠子,一边收拾一边哭,哭得声嘶力竭。忽然想呕吐,觉得胸中那块堵着的东西,猛劲冲出来,来不及回头,已经掉进丈夫的腹腔中。
陈氏吃惊地一看,原来是颗人心,在腹腔中突突地跳动,热气蒸腾像冒烟一样。陈氏大为惊异,急忙用两手合起丈夫的腹腔,用尽力气挤抱着;稍一松劲,就有热气从缝中冒出来。
于是她便撕了幅绸子捆扎起来,用手抚摸着尸体,觉得渐渐温暖起来。又盖上被子,半夜里打开被子一看,鼻中有了气息。
天亮后,王生竟然活了,自己说:“恍恍惚惚地像做了场梦,只觉得肚子隐隐约约有点痛。”看看原来的伤口,结了个铜钱大的痂,不久就全好了。
(出自《聊斋志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