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打丘杏儿从娘家带回少夫人那句“添丁才是正经事”的金玉良言,王家庄园里的风,便悄然转了向。那本摊开的田亩册子,空白处再无人提笔添上新的墨迹,倒是“嗣息”那一栏,被丘杏儿用朱笔重重圈了又圈,成了小两口心头最紧要的账簿。
这念头一起,便如野草疯长。起初还是夜里枕畔的低语,带着点羞涩和热望。丘杏儿掐着指头算日子,眼巴巴盼着月信迟来。可一月、两月过去,肚子依旧平坦如初,那点隐秘的期盼便渐渐熬成了明晃晃的焦灼。
她坐在妆台前,瞧着镜中自己依旧姣好的面容,眉头却无端蹙了起来:“文柏,你说……莫不是我们年纪大了些?还是我平日里舞枪弄棒的伤了身?”话一出口,自己先觉着晦气,又赶紧“呸呸”两声。
王文柏宽厚归宽厚,这份焦灼却也一分不少地落在他肩上。他白日里巡看田亩,心思却总飘回内宅,看佃户家的小娃儿在田埂上追逐嬉闹,那咯咯的笑声钻进耳朵里,竟比算盘珠子的脆响更让他心头滚烫,又隐隐发酸。夜晚对着账本,那墨字也常常化作一个个胖娃娃的虚影在眼前晃荡。他搁下笔,长长叹一口气,这声叹息里,七分是盼,三分是怕。
少夫人祝小芝的消息最是灵通,听闻妹妹妹夫为子嗣心焦,没过几日,便打发了一个人过来。来的正是她的贴身丫鬟小蝶,丘杏儿幼时一同在丘家大院长大的玩伴,如今出落得越发水灵干练。
小蝶拎着个小包袱,进门就笑:“杏儿姐,少夫人说了,让我来给您搭把手。家里杂事琐碎活计,都交给我,您呀,只管放宽心,养好身子骨是正经!”她手脚麻利,放下包袱就开始支派丫鬟仆人各人活计,那股子熟悉的利落劲儿,瞬间让丘杏儿眼眶微热。有小蝶在,她肩上的担子确实轻省了不少,至少不必再为监督巡视、灶头琐事分神耗力。
然而,心头的焦灼岂是省些力气就能化解的?丘杏儿依旧是那个丘杏儿,既认准了“添丁”是头等大事,便拿出了当年盘算田亩、经营家业的精明劲儿。她开始四处“求经”。
头一个拜访的,是隐居在太皇河上游别院的陈周氏。陈周氏体态丰腴,气色红润,膝下儿女绕膝,正是丘杏儿眼中顶有福气的人。她带着新式的胭脂登门求教,陈周氏见她来意,了然一笑,拉着她的手进了暖阁,细细传授!
“妹妹,这怀身子啊,讲究个’暖宫’。每日晨起,必得用那隔年窖藏的老姜,切得细细,滚水冲了浓浓一碗姜糖水,趁热喝下去,暖意从喉头直透到小腹才好!”
她顿了顿,声音压低了些,带着过来人的神秘,“还有那……晚间,夫妻敦伦之后,切莫贪凉,务要用暖水袋温着腰腹,护住那一点’阳气’……” 丘杏儿听得连连点头,只觉字字珠玑,恨不得拿个本子当场记下。
过了几日,她又备了束脩,去拜访村塾先生李修文的妻子柳氏。柳氏出身书香门第,气质娴雅,说话也带着三分文气。她引着丘杏儿看自家小院中几盆长势极好的兰草,慢声细语道:“妹妹莫急。万物生长,自有其时。依我看,除了温养,还需’静心’。常焚些安神的柏子香,抄抄清心经卷,心神安宁了,那’胎神’才乐意来投奔呢。”
柳氏又取出一张泛黄的纸,“这方子,是我们湖北老家的郎中祖传的,取菟丝子、桑寄生、女贞子几味温和药材,配以乌骨鸡炖汤,最是补益气血,助孕安胎。”丘杏儿如获至宝,小心地收好。
于是乎,王家灶房的烟火气,便添了浓郁的药膳味。丘杏儿将陈周氏的姜糖水、柳氏的安胎汤奉若圭臬,每日雷打不动。晨起,一碗辛辣滚烫的姜糖水逼得她额头冒汗;晚间,那飘着药香的乌鸡汤又成了必备。她不仅自己喝,目光灼灼地看向王文柏时,那份“同甘共苦”的意味便不言而喻了。
王文柏看着妻子殷切的眼神,再看看那碗颜色深浓、气味独特的汤药,头皮隐隐发麻。他是个顶顶怕苦的人,平日里连汤药都避之不及。可此刻,面对丘杏儿那双盛满了期盼的眸子,他如何能推拒?只得硬着头皮咕咚咕咚灌下去。那滋味,直冲脑门,苦得他眉头拧成了疙瘩,五官都挪了位。丘杏儿在一旁紧张地盯着:“如何?可还受得住?柳嫂子说,这汤最是滋补男子精气……”
“受得住,受得住!”王文柏强忍着胃里的翻腾,挤出笑容,额角却已渗出细密的汗珠。这哪里是滋补,分明是酷刑!可为了那不知何时才能到来的胖娃娃,再苦也得咽下去。
有时实在难以消受,王文柏也会生出些“阳奉阴违”的小心思。趁丘杏儿去前院处理佃户事务,他悄悄将那碗黑乎乎的汤药端到后院窗根下,手腕一倾药汁便无声地渗入泥土,滋养了墙根那几株本就茂盛的狗尾草。做完这一切,他心虚地朝门口张望,再若无其事地将空碗放回原处,仿佛自己是个刚刚完成壮举的英雄。只是那狗尾草,似乎长得愈发油绿粗壮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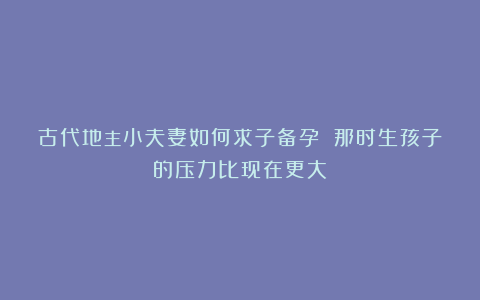
丘杏儿却是全身心地投入这场“生育大业”。她抄柳嫂子给的安胎经卷,抄得簪子歪了都顾不上扶正;按陈周氏的法子,每晚用暖水袋焐着腰腹,焐得自己像只被蒸熟的虾子,辗转难眠。
更将那“敦伦”之事,也列入了需要精心考量和安排的日程。她甚至拿出当年规划田亩轮作的精神,在炕头小柜的暗格里藏了本自制的“花信簿”,掐算着日子,某日必要缠着王文柏早早吹灯歇息,某日又体贴地让他独自安眠“养精蓄锐”。
王文柏被她这阵仗弄得是哭笑不得,有时被她那本“花信簿”安排得明明白白,反而束手束脚,倒不如从前随性时自然。看着妻子亮得惊人的、充满“战略意图”的眼神,他常常是未战先怯了三分,只剩下满心的怜惜和无奈。
一日午后,小蝶在整理丘杏儿的妆匣,无意间抖落出那本秘藏的“花信簿”。她好奇地翻开一看,只见上面密密麻麻画着只有丘杏儿自己能懂的符号,圈圈点点,旁边还用小楷标注着“宜静养”“宜敦伦”“大吉”等字样。
小蝶先是一愣,随即忍俊不禁,噗嗤笑出声来。她拿着簿子跑到正在核对佃户秋粮账目的丘杏儿跟前,指着那些标记,笑得前仰后合:“哎哟我的小姐!您这是……您这是把咱家姑爷当那田里的庄稼来侍弄了?还分节气、看黄历呢?”
丘杏儿正凝神算账,被小蝶这么一闹,先是茫然,待看清她手里的簿子,腾地一下,从脸颊红到了耳根,连脖子都染上了一层薄薄的胭脂色。她劈手夺过簿子,又羞又恼,作势要打小蝶:“死丫头!胡吣什么!看我不撕了你的嘴!”
小蝶笑着躲闪,主仆二人闹作一团。丘杏儿追了两步,自己也绷不住笑了起来,笑着笑着,那笑意里却渐渐浮上一层水光。连日积压的紧张、期盼和屡屡落空的委屈,被小蝶这一闹,像是戳破了的气囊,骤然泄了出来。她靠着妆台,手里还捏着那本可笑的“花信簿”,眼泪竟不争气地滚落下来。
刚巧王文柏从地里回来,一进门便撞见这一幕:妻子眼圈红红,脸上泪痕未干,手里紧紧攥着那本“机密”;小蝶在一旁,又是递帕子,又是挤眉弄眼。他心头一紧,几步上前:“杏儿,这是怎么了?”他下意识地以为是佃户那边出了什么棘手事让她受了委屈。
丘杏儿抬起泪眼,看着丈夫风尘仆仆、带着泥土气息却满是关切的脸,再看看手里这本承载了她无数焦虑和精心谋划的簿子,忽然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是那么傻气又可怜。她吸了吸鼻子,带着浓重的鼻音,将那簿子往王文柏面前一递,带着点破罐子破摔的委屈!
“喏!都怪它!也怪……也怪这肚子不争气!嫂夫人说得对,添丁是大事,可……可这大事,怎么比买地还难上百倍!” 她想起那些难以下咽的汤汤水水,那些掐着指头算的日子,那些深夜里独自焐着暖水袋的辗转,还有丈夫喝药时强忍痛苦的皱眉……种种辛酸委屈一齐涌上心头。
王文柏接过那本画满符号的簿子,只翻了一页,便已了然。看着妻子梨花带雨的模样,再想想自己偷偷倒掉的那些苦药汤,一股混杂着心疼、愧疚和巨大温柔的暖流瞬间冲垮了他的心防。他哪里还顾得上什么“花信”“黄历”,也顾不上小蝶还在旁边抿嘴偷笑,张开双臂,将那哭得微微颤抖的妻子紧紧搂进怀里。她的发丝带着熟悉的、混合着阳光和草药的味道,柔软地蹭着他的下颌。
“傻杏儿,” 他的声音低沉而温暖,带着安抚人心的力量,在她耳边响起,呼出的热气拂过她微凉的耳廓,“买地要看天时、地利、人和。这生娃娃的事,更是天大的缘分,急不得的。”
他宽厚的手掌轻轻拍着她的背,像哄一个受了大委屈的孩子,“咱们只管把身子养得壮壮实实,把日子过得和和美美,该来的,总会来。强求……反倒不美了。你瞧瞧你,这些日子,把自己都折腾瘦了。” 他的手指拂过她眼下淡淡的青影。
丘杏儿伏在他坚实的肩头,感受着他怀抱的安稳和话语里的疼惜,抽泣声渐渐低了下去。丈夫身上熟悉的汗味和泥土气息,此刻竟比任何安神香都更令人心安。是啊,自己是不是太心急了?像对待田亩一样去算计、去强求这生命的缘分?嫂子说要添丁,是长远之计,自己却恨不能立竿见影!
紧绷了多日的弦,在这一刻终于缓缓松弛下来。她抬起泪痕斑驳的脸,望向丈夫温柔的眼睛,那里盛满了理解与包容,没有丝毫的责备或不耐。她有些不好意思地小声嘟囔:“那……那柳嫂子给的乌鸡汤,还炖不炖了?陈姐姐说的姜糖水,还喝不喝了?”
王文柏看着她这副又委屈又带点娇憨的模样,心软得一塌糊涂。他笑着,用指腹轻轻揩去她脸颊上的泪痕:“炖!喝!不过嘛……”他故意拖长了调子,眼中闪过一丝促狭的笑意,“得听我的。想喝才喝,不想喝,咱就不喝。那药汤子,更是不许再灌我了!再灌,我就真成那药渣子了!” 他夸张地皱起鼻子,做了个被苦倒的表情。
丘杏儿被他逗得破涕为笑,轻轻捶了他一下:“去你的!谁灌你药渣子了!” 郁结多日的阴云,在丈夫的怀抱和玩笑中,似乎真的散开了一些。
小蝶在一旁瞧着,抿着嘴悄悄退了出去,轻轻带上了房门。屋内,只剩下相拥的两人。窗外,秋阳正好,暖融融地洒进来,将两人的身影在地面上拉长,温柔地交叠在一起。
灶房里,小蝶揭开砂锅盖子的声音隐约传来,一股混合着药材与鸡肉的浓郁香气,随着袅袅白汽,在午后宁静的空气里缓缓弥漫开来。这一次的汤味,似乎不再那么令人望而生畏,反而透出几分生活的、踏实的暖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