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再次提起元大都遗址发掘,半个世纪过去了。大家翘首以盼的《元大都——1964~1974年考古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终于在2024年3月出版了。从考古发掘到报告出版,半个世纪以来,发生的事情太多太多了。
北京元大都的考古工作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考古队经历了几代考古学者的更替。最初的几位老先生,如魏善臣、屈如忠、贾金华等,是50年代初参加过河南辉县琉璃阁发掘的成员;还有蔡玉章、高济英、李进、段鹏琦、张连喜、安德厚、郭义孚、蒋忠义、徐殿魁、孟凡人、刘震伟和丁六龙等,他们都在60年代中期参加了元大都城垣、街道等的钻探发掘工作。70年代初,先后又有科学院考古所(即今社科院考古所)的钟少林、关甲堃、郭义孚、赵信、蒋忠义,以及北京市文物管理处考古队的马希桂、喻震、潘长华和我——黄秀纯加入进来。前前后后共有二十多人在元大都考古队工作过。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大家多是断断续续地参加某一阶段的工作,只有队长徐苹芳先生自1964年至1974年,始终坚持在元大都考古队发掘前线。现在这些人大多数都作古了。
1969年5月,新都暖气机械厂的工人郭源,在拆除西直门箭楼下的明代城墙时发现了元代的城门洞,即和义门瓮城。
和义门瓮城考古现场
元大都建设之初并无瓮城。元朝末年,元顺帝于至正十九年(1359年)“诏京师十一门皆筑瓮城”,主要目的是阻止农民起义军进攻。明正统元年(1436年)明英宗命宦官阮安等监修京师九门城楼,修建时利用和义门原有的门洞,将元代瓮城压在新建的瓮城之下。城门由内外两个券洞组成,城楼已毁,尚存木门两侧的门砧石和半圆形的铁“鹅台”,与宋代《营造法式》所记形制完全一样,为考古发现中仅见的实例。门楼上还发现了低于铺砖地面的地漏,就是防御火攻的水箄子。这种防御火攻城门的灭火设施,是我国建筑史上首次发现的新资料。
和义门门楼,低于铺砖地面的地漏,就是防御火攻的水箄子
和义门门楼上的地漏
1969年冬天,北京市文物管理处考古队派我去和义门遗址,协助中科院考古所郭义孚先生测绘城址的平、剖面图,做扶塔尺、报数据等工作。空旷的城台显得格外冷冽,郭义孚先生戴着老式的棉帽子,脚上穿的也是老式的骆驼鞍儿棉鞋,冻得不行,一边搓着手,跺着脚,即使这样,也要按比例一块砖一块砖地画。他希望为这座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瓮城,留下尽可能完整的最后的记录。郭老说:“我画的图,将来可以按比例复原元大都瓮城。”
1972年,我正式参加元大都考古队。回想起当年曾经并肩战斗参加发掘的工作人员,徐苹芳、郭义孚、钟少林、潘长华、关甲堃等先生已经仙逝;喻震先生活的岁数最大,于2021年5月寿终正寝,享年94岁;我当时年龄最小,如今也80岁了。尚健在的马希桂先生过了92岁,蒋忠义先生也在86岁左右。参加《报告》专论部分的撰稿人,李德金96岁,张广立也是耄耋老人了。《报告》的出版。对已故的前辈及活着的人都是极大的安慰。
徐苹芳先生是城市考古专家。《报告》的出版,让我们终于看到徐先生的研究成果《元大都城平面规划复原图》的真面貌。在这之前,如何划定元大都的中轴线,众说纷纭。
早在1957年5月,清华大学中国建筑史专家赵正之教授作为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负责人,率队踏查元大都遗迹,其中就有20多岁的考古队员徐苹芳。赵正之先生提出元大都中轴线即明清北京城的中轴线,相延未变,北京内城东西长安街以北的街道基本上是元大都的旧街。在北京城市研究史上,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也是颇受争议的观点。北京城的子午线与明清北京城中轴线并不重合,略向西偏。很长一段时间,主流观点认为元大都中轴线在明清北京城中轴线之西,即今旧鼓楼大街南北一线。
1962年,赵正之教授得了肺癌,无力写出他的研究成果。北京大学考古学家宿白先生建议他的学生徐苹芳每周到医院一次,记录下赵正之的口述,历时两个月。徐苹芳回忆:“他说话声音都哑了,最后实在没力气了,秋天就故去了。”
1966年,徐苹芳先生记录整理的赵正之遗著《元大都平面规划复原图研究》,本应在《考古学报》发表。杂志都印岀来了,还没有来得及装订,就赶上“文化大革命”,便当废纸处理了。直到“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才在《科技史文集》第二辑中得以发表。这些问题都企盼徐先生最后的《元大都城平面规划复原图》如何划定北京城中轴线。
02.
1974年,元大都考古尚未结束,徐苹芳先生就提出了“元大都资料整理及专题研讨计划”,要求整理遗物按用途和质料不同,分类统计和挑选不同标本。元大都出土了大量不同时期不同窑口的瓷片,为了确定瓷片的时代、类型和窑口,我们多次前往全国各地著名古瓷窑遗址考察。临出发前,徐先生约法三章:一,逢州过县不要讨扰地方官员。二,有关北京“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不要对外人讲。三,尽可能地找地方制瓷小作坊,考察原始陶瓷生产工艺流程。同时与山东省淄博市陶瓷研究所合作,并邀请研究员刘凯民和我们一起赴各大窑址调查。后将采集的大量标本交给刘凯民,进行胎质、釉面、烧成温度等化验,并要求写出化验报告。但是刘先生爽约了,他把瓷片标本带回山东,一去不返,如同石沉大海,杳无音讯。
徐苹芳先生撰写的元大都考古报告整理编写工作计划
1976年初,徐先生又提出《元大都考古报告》编写大纲。规定1976年底完成初稿。徐先生分担了《报告》大部分章节,付出了极大的辛苦。我们按徐先生的要求,于1979年前将自己负责撰写的章节都完稿交给主编徐先生,由他最后修改定稿。
由于种种原因,元大都考古报告当时未能出版。80年代中期,徐苹芳先生任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当时国家文物局也给了出版经费。无奈,因徐先生工作很忙,不是出国讲学,就是在各地奔波劳碌,手头稿件堆积如山,特别是元大都报告书稿,当时交的都是手写稿,工作量非常大。
按照徐先生生前要求,由当年参加元大都报告编写且仍健在人员把报告未完成部分补写齐,并将报告的整理工作交给蒋忠义、马希桂完成。他俩几经波折,首先,由蒋忠义先生负责,将《元大都城平面规划复原图》基本按照徐先生手稿补缺完成,各章节统一体例,器物线图统一比例,并完成器物图版编排、画版式等工作,以及绘制和义门遗址建筑复原图等。其次,元大都所有出土器物,早在上世纪70年代大多交与首都博物馆入藏。由于当时照的大多是黑白照片,彩版极少而且多已褪色,质量很差,需要补拍器物彩色照片。由马希桂先生与首都博物馆斡旋交涉,提取文物照相。其间,库房保管人员、首博及文物局来回来去推排球,费老劲了,最后也没有完全如愿,只能“有多少水,和多少面”,将就材料了。为了整理这批材料,蒋忠义先生两年来几乎吃住在办公室,挑灯夜战,所有资料都用稿纸手写,摞起来有1米多高。在最后冲刺阶段,文物出版社担任此书责任编辑的谷艳雪女士,几乎天天在他的办公室,等着拿到出版权。
元大都遗址出土琉璃釉龙头鸱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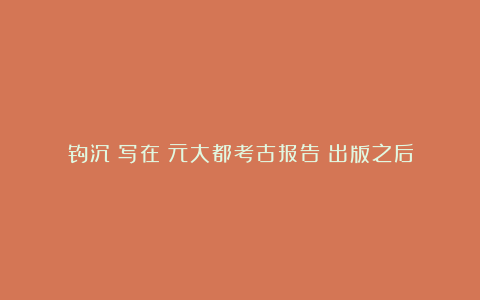
元大都遗址出土双凤瑞兽纹丹陛石(国家博物馆藏)
元大都万宁桥东侧北岸石雕水兽
2013年,元大都考古报告的文稿终于完成,连同国家文物局拨给的出版经费,一并交与文物出版社,并签订了出版合同,约定2016年正式出版。合同签订后,蒋忠义先生把所有原稿、元大都城平面规划复原图、遗址图、器物图、拓片、照片及底版等材料均交给了编辑谷艳雪。据蒋先生说:“这些资料用小汽车拉走的,装一后背箱。”谁知道此《报告》编辑工程太大,梳理原稿,电脑录入,文图编校,超过六年还没有完成。
2022年初,蒋忠义先生对我说:“小黄,元大都遗址发掘,活着的人你最小,你要多活两年见到报告,我和马希桂不一定能见着这报告了。”我那时候都70多岁了,他说得悲悲切切,我听了也很伤感。于是,2022年2月22日,我给文物出版社社长写信,催促《报告》出版事宜。后来通过总编辑我见到责编谷艳雪,她把文字部分的原稿已输入电脑录制完毕。一个人完成将近百万字的文字录入、文稿编辑、后期图版编排等,确实很辛苦。社里虽派了新来的助理,但是插不上手。下厂印制在朝阳区,又赶上三年疫情,朝阳区是重灾区,不能随时下厂去校对。以后校样印出后,蒋先生岁数大了,校对的事只好由我顶上去,责编谷艳雪就把书稿快递给我。校对两次书稿要送回出版社,我怕丢,不敢寄快递,都是坐地铁抱过去的。又经过一年的努力,《元大都——1964~1974年考古报告》总算正式出版了。
《元大都——1964~1974年考古报告》书影(黄秀纯摄)
03.
关于北京城中轴线的界定,以往各种观点争论不休。《报告》出版后,可以说尘埃落定了。
北京城中轴线是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典范,集中体现了传统礼制思想、政治权力象征和文化哲学理念。这条中轴线南起永定门,一路向北,依次穿越正阳门、天安门、紫禁城、景山、万宁桥、鼓楼、钟楼,全长7.8公里。故宫博物院单士元先生在《故宫史话》中提到,考古队1964年对故宫进行钻探:“在文华殿和武英殿取出的土方证明,在两殿的东西平行线上应是元代皇宫金水河,从景山和地安门桥等地所得资料证明,‘元大内’的中轴线就是明紫禁城的中轴线。”
这条轴线自元代形成雏形,明清发展成熟,至今仍是北京城市空间格局的核心骨架。2024年7月2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北京市的第八个世界文化遗产。
元大都考古队的成立,最初缘由是1963年为配合地图委员会编绘任务,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市文物工作队,联合成立北京城历史地图小组,其目的是为研究和复原北京城历史及城市规划,也为北京城历史地图小组提供科学资料。1964年改为元大都考古队,由徐苹芳先生任队长。由于北京内城基本延续了明清北京城的格局,然而元朝的大都城属于古今重叠的城市,钻探发掘工作复杂而繁重。
1964年~1965年,徐苹芳先生领导元大都考古队,对于这座“古今重叠型城市”的元大都进行全面钻探,而且非常注意中轴线的勘察。60年代初,在明清北城墙以北至元土城遗址以南仍是较空旷的地段,尚未盖起高楼大厦。于是队长徐苹芳先生决定,在明清北京北城垣外,元大都土城内,也就是在安贞门南北大街以东、光熙门东西大街以北的范围内进行钻探。结果钻探出二十一条横排胡同。按其间隔距离的排列规律,原应有二十二条横排胡同,但光熙门大街以北的第一条胡同没有发现。 这与今北京内城从朝阳门(元齐化门)至东直门(元崇仁门)之间排列二十二条东西向胡同是相同的。
当时几片地点经常同时作业,一组城东,一组城西,为了及时发现蛛丝马迹,徐先生骑着自行车两头跑,到了中午就在路边找个茶馆,从包里掏出火烧就茶吃,有时干脆不吃。徐先生正是吃饭没规律,得了胃溃疡,住院做了手术。
元大都遗址测绘图
元大都城是按《周礼·考工记》“左祖右社,前朝后市”设计的,“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大城中心设中心阁,“阁之西为齐政楼,更鼓谯楼,楼之北乃钟楼也”(见《析津志》)。经钻探,在今鼓楼大街、景山公园后墙外正中对寿皇殿一带,发现一段南北向路土遗迹,宽达28米,即是当时元大都城中轴线上的街道。
《报告》里关于元大都中轴线是这样叙述的:“元大都的中轴线充分体现了以皇权为中心的政治色彩。大都的中轴线南起外城中心的丽正门,向北穿千步廊至皇城的灵星门,过周桥,至宫城正南中心的崇天门,经前朝的大明殿、后宫的延春阁,北出宫城的厚载门和皇城的厚载红门,向北过万宁桥(海子桥),直抵大天寿万宁寺的中心阁(今鼓楼)。这条中轴线也是明清北京城的中轴线,不同的是中轴线北端的终点为钟鼓楼。这是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修筑北京城时的事情。”
《报告》里还厘清了有关中轴线的历史争议:“关于元大都中轴线的位置,原来认为是以北京内城的旧鼓楼大街为准。1957年,清华大学建筑系赵正之教授提出元大都中轴线即明清北京城的中轴线,相沿未变。1964年,元大都考古队勘探了大都的中轴线,勘探结果否定了以旧鼓楼大街为元大都中轴线的传统推测,并证明了赵正之教授提出的明清北京城中轴线与元大都中轴线一致的说法。特别是近年在清理地安门桥,即元大都的万宁桥(海子桥)时,在其东侧北岸发现了元代的岸边石刻水兽,其底座上刻有“至正四年(1344年)九月”纪年,这是元大都城中轴线历明清而不变的确证。”
上世纪70年代初,环绕北京城墙修建地铁二号线开工。为了配合地铁环线建设工程,1972年,中科院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合作,联合成立元大都考古队,仍由徐苹芳先生任领队,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参加人员有钟少林、蒋忠义、郭义孚、关甲堃、赵信;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参加人员有马希桂、喻震、潘长华和我,潘长华为行政管理人员,负责招工、采买及后勤保障工作。自1972年至1974年止,先后在明清北城墙一线发掘了后英房、桦皮厂、后桃园、西绦胡同、安定门煤厂以及雍和宫等十余处元代居住遗址。
发掘元大都后英房元代居住遗址工作照,左起郭义孚,钟少林、马希桂、黄秀纯,舒世俊摄(作者供图)
元大都后英房东院遗址
1965年发掘元大都后英房东院遗址利用云梯车拍摄现场
田野工作结束后即转入室内器物整理阶段。应该说工作跟进及时,器物修复、绘图、照相等均按计划完成,丝毫没有耽误。队长徐苹芳先生要求参与发掘人员在1979年完成自己承担的《报告》部分。我在1978年即写完了后英房元代居住遗址、德胜门元代倒座门四合院遗址等章节。其他人员也在1979年前陆续完稿,交与徐苹芳先生。当时我和孩子说:“等《元大都发掘报告》出版后,用稿费给你们买一台电视机。”那时社会上正流行牡丹牌9英寸黑白电视机。以后,孩子等啊、盼啊,几乎家家都有了小电视了,我们的《报告》还没有出版。为了了却孩子的心愿,我家添置了一台青松牌12英寸黑白电视机,时价400元。再后来牡丹牌“彩色21遥”都出来了,元大都报告由于种种原因仍迟迟未能出版。
这一等就是四十多年!2024年3月,一套四大本的煌煌巨著《元大都——1964~1974年考古报告》终于出版了。前言里的一段话,说出了考古队所有人的心声:“元大都考古工作队从1964年开始,到报告正式出版,历经半个多世纪,感受颇多。虽然元大都考古队员近一半都已作古,健在的成员也都年过古稀,但编写报告的最后阶段,我们仍按考古学要求,力求科学严谨,若能对宋元考古有所贡献,我们也就安心了。”
(2025年6月于古燕斋)
插图为作者提供,除单独标注,均翻拍自《元大都——1964~1974年考古报告》,文物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