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6-09 22:04
暮色如墨,浸透了青石村头那棵老槐树的枝桠。
王老汉蹲在门槛上吧嗒旱烟,火星子明灭间,他瞥见马厩方向飘来几缕暗红的光。
那光不似寻常灯笼,倒像是野地里磷火,忽忽悠悠地钻进驴棚的苇席缝里。
他喉咙发紧,烟袋锅子在青石板上磕出清脆的响。
三个月前买回的那头黑驴,如今瘦得能数清肋条骨,每日只肯嚼两把干草,连槽头的水都懒得沾唇。
请了三个兽医来瞧,都说牲口没病没灾,可那对琥珀色的眼珠子,总在夜深人静时泛着诡异的青光。
‘当家的,灶上煨着粟米粥。
媳妇春娥端着油灯从灶房出来,粗布襦裙扫过青砖地,带起一阵若有若无的腥气。
王老汉抽了抽鼻子,这味道像是雨后翻开的烂泥塘,又混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甜腻。
他装作没闻见,闷头往屋里走,后脖颈却突然窜起一阵寒意——春娥的影子被灯光拉得老长,竟在驴棚的土墙上晃出个三头六臂的怪形。
三更梆子响时,王老汉轻轻推开后窗。
月光像把银梳子,细细梳理着院里的物件。
驴棚的苇席门帘被夜风掀起一角,他看见春娥跪坐在干草堆里,褪了外衫,露出雪白的脊背。
那头黑驴不知何时支棱起耳朵,鼻孔翕张着喷出白气,竟伸出舌头去舔春娥后颈。
王老汉的指甲深深掐进窗棂,指节泛出青白。
他想起半月前在村口老井打水,听见几个婆娘嚼舌根:’春娥嫁过来前,在镇上当过暗门子呢。
当时他抄起扁担就要跟人拼命,此刻却觉着那些闲话像毒蛇,顺着脊梁骨往上爬。
鸡叫头遍时,春娥才拖着步子回屋。
王老汉闭眼装睡,却感觉她冰凉的手指抚过自己脸庞,带着股子驴棚特有的膻味。
他听见窸窸窣窣的脱衣声,突然想起什么,猛地睁开眼——春娥腰间系着的红绸带,分明是白日里给黑驴系在脖子上的!
次日晌午,王老汉揣着半吊钱进了镇东头的药铺。
掌柜的捻着山羊胡,盯着他递来的驴毛看了半晌:’这畜生……莫不是吃了迷魂草?
说着从樟木匣里取出个油纸包,’掺在草料里,三日可见分晓。
当夜月黑风高,王老汉摸黑往驴槽里撒药粉。
黑驴突然扬起脖子嘶鸣,声音不似驴叫,倒像女人在哭。
他手一抖,药粉撒了大半,正要补救,忽听得身后瓦片轻响。
转身时只见个黑影掠过墙头,春娥的蓝布头巾在风里飘了飘,转眼没入夜色。
王老汉抄起门后的顶门杠追出去。
村道两旁的苞谷地沙沙作响,他总觉得有双眼睛在暗处盯着。
转过老柳树时,前方忽然亮起两点绿光,黑驴昂首站在路中央,脖颈上的红绸带无风自动。
月光下,那畜生竟咧开嘴笑了,露出两排森白的牙。
‘孽畜!
王老汉大吼一声,顶门杠抡得虎虎生风。
黑驴却不躲不闪,待木棍将至面门时,突然人立而起。
王老汉只觉眼前白光一闪,那畜生竟化作个赤身男子,胸前还系着半截红绸带。
他踉跄后退,后脑勺撞上柳树,天旋地转间听见春娥的尖叫。
再睁眼时,王老汉躺在自家炕上。
春娥熬着药,眼圈红得像熟透的樱桃。
当家的,你昏了三天。
她指尖抚过他额角的淤青,’那黑驴……原是河神座下的青驴将军。
原来二十年前,春娥还是女娃时,在河边救过只被渔网缠住的青驴。
那畜生口吐人言,说将来必报大恩。
去年河神娶亲,要选童男童女沉河,青驴将军便化作黑驴混进人世,想寻个至阴至纯的女子替春娥应劫。
‘它每晚吸我精气,是为炼化河神给的避水丹。
春娥解开衣襟,雪肤上布满蛛网般的青痕,’明日就是月圆夜,它要带我跳河……’话音未落,窗外忽起狂风,驴棚方向传来地动山摇的嘶鸣。
王老汉抄起柴刀就往外冲。
春娥死死拽住他衣角:’没用的!
它得了避水丹,水火不侵!
话音未落,黑驴已撞开篱笆冲进院子,四蹄踏过处,青砖裂开蛛网纹。
月光下,它周身泛起幽蓝水光,额间竟生出一支螺旋独角。
‘恩公!
黑驴口吐人言,声如洪钟,’春娥本该三日前溺毙,是俺用千年道行替她续命。
如今河神震怒,降下天雷……’话音未落,头顶炸开霹雳,豆大雨点噼里啪啦砸下来。
王老汉看见春娥脖颈后的青痕正在蠕动,像是有无数蚯蚓在皮下游走。
‘拿枣木钉来!
春娥突然尖叫。
王老汉这才想起,老宅梁上确实悬着三根百年枣木钉,是祖上传下来镇宅的。
他转身冲进雨幕,听见身后传来金铁交鸣之声。
待取了木钉回来,只见春娥手持菜刀与黑驴缠斗,她每砍一刀,黑驴身上就溅起水花,而她自己则像被抽去筋骨般瘫软一分。
‘钉它天灵!
春娥嘶吼着扑向黑驴,菜刀深深嵌进畜生后腿。
王老汉闭眼掷出木钉,正中黑驴眉心。
霎时狂风大作,河面传来龙吟般的怒吼,黑驴化作一滩黑水,水中浮起颗龙眼大的珠子,蓝光流转如活物。
春娥栽倒在地,脖颈后的青痕已蔓延至下颌。
王老汉抱起她要往镇上跑,却被冰凉的手抓住:’没用的……避水丹……’她突然咬破舌尖,将血珠喷在避水丹上。
珠子倏地飞起,撞进她心口,绽开朵血色莲花。
雨不知何时停了。
王老汉呆呆望着怀里的妻子,她皮肤下的青痕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退,而那颗避水丹已化作细沙,顺着她指缝簌簌落下。
河面升起七彩霞光,隐约可见个青衣童子作揖行礼,转眼消失在水雾里。
天将明时,春娥悠悠转醒。
她望着守在炕边的丈夫,忽然轻笑:’当家的,你后脖颈沾了驴毛。
王老汉一摸,果然有根黑亮的硬毛粘在衣领上。
他正要拍掉,春娥却突然握住他的手:’留着吧,就当……记着这场荒唐梦。
此后青石村多了桩奇谈。
有人说夜半经过王家老宅,总听见驴叫声混着女子啜泣;有人说看见春娥在河边洗衣,倒影却是驴头人身。
只有王老汉知道,每逢月圆夜,那根驴毛就会发烫,烫得他整夜整夜睡不着觉。
去年开春,村里来了个游方道士。
王老汉本想讨张符咒,道士却盯着他后颈直摇头:’施主身上缠着水族因果,那驴精并未灰飞烟灭,只是借丹转世去了。
说着掏出面铜镜,镜中赫然映出个襁褓中的婴孩,眉心一点朱砂痣,活脱脱是黑驴转世。
如今那孩子已会满地跑,最爱骑在王老汉肩头学驴叫。
春娥倒也不恼,总笑着往孩子嘴里塞糖瓜:’随他去吧,前世欠的债,今生当牛做马还也是应当。
只是每逢雷雨夜,她总会把避水丹化成的细沙撒在窗台,看着那些银粉在风里聚成小小的漩涡,恍若当年黑驴额间的独角。
青石村外三十里,有座荒废的龙王庙。
这日王老汉背着药篓采药,忽见天际阴云如墨,云层中探出半截青鳞巨尾,鳞片缝隙里渗出暗红血水,滴落在庙顶残破的琉璃瓦上,竟发出铁锅煎油般的滋滋声。
他心头突突直跳,想起游方道士临走前塞给他的黄符。
那符纸此刻在怀中发烫,烫得他胸膛像揣了块火炭。
正要转身,庙门忽然洞开,腐朽的木轴发出垂死般的呻吟,腥风裹着细沙扑面而来,沙粒里混着指甲盖大小的碎鳞,在阳光下泛着诡异的青芒。
王老汉被风沙迷了眼,再睁眼时已站在庙中。
十八根盘龙柱倒塌过半,断口处渗出粘稠的黑色黏液,闻着像腐烂的河蚌肉。
供桌上的龙王像拦腰折断,上半截滚落在地,石雕的龙睛不知被谁剜去,留下两个黑洞洞的窟窿,正汩汩往外冒黄水。
‘恩公别来无恙?
阴恻恻的声音从头顶传来。
王老汉猛抬头,见横梁上倒挂着个青衣童子,双足缠着水草,脚踝处各钉着枚生锈的铜钱。
那童子脖颈以不可思议的角度扭曲着,咧开的嘴角几乎裂到耳根,露出满口倒刺般的细牙。
王老汉倒退三步,后腰撞上供桌。
断裂的龙王像突然抽搐起来,碎石簌簌掉落,竟拼凑出个半人半蛇的怪物。
那物上半身是春娥模样,下半身却覆满青鳞,蛇尾扫过之处,青砖地面裂开蛛网纹,缝隙里钻出无数白骨手指。
‘河神要的新娘……’蛇女吐着猩红信子,瞳孔缩成两条细线,’青驴将军既替你挡了劫,这替身便由你女儿来当罢!
话音未落,庙外传来孩童嬉笑。
王老汉浑身血液凝固——那分明是他家小宝的声音!
他发疯般往外冲,却见庙门变成滔滔河水。
河水凝成万千人手,拽着他往深处拖。
王老汉死死扒住门槛,指甲缝里渗出血珠。
恍惚间听见春娥在喊:’用枣木钉刺它七寸!
他这才想起怀中还藏着祖传的镇物,摸出木钉时,指尖已触到河底森森白骨。
木钉刚触及水面,河水突然沸腾。
青衣童子惨叫着现出原形,竟是只磨盘大的老鳖,背甲上嵌着七枚铜钱,组成北斗七星阵。
老鳖口吐人言:’好个狠心的凡人!
二十年前你爹在龙王庙前溺死童男童女,今日该还债了!
王老汉如遭雷击。
记忆翻涌而上,那年他才十岁,亲眼见父亲将哭闹的妹妹推进河里。
老鳖的龟甲突然迸发青光,幻化出当年场景:暴雨倾盆的河岸,父亲手持桃木剑,将七个孩童串在红绳上,口中念念有词:’以童男童女之血,祭河神换三年风调雨顺……’
‘原来如此!
王老汉踉跄后退,怀中黄符无风自燃,’你们要找的不是我,是王家血脉!
他突然扯开衣襟,露出心口朱砂痣——正是那日避水丹所化。
老鳖见状大喜,蛇女也甩着尾巴逼近,腥风中传来锁链拖地的声响。
千钧一发之际,庙外传来清越的铜铃声。
游方道士踏月而来,道袍下摆沾满夜露,手中铜钱剑串着七盏七星灯。
他咬破舌尖喷在剑上,铜钱叮当作响:’孽畜!
二十年前你借河神之名行妖邪事,今日贫道便替天行道!
老鳖与蛇女同时暴起。
老鳖背甲上的铜钱飞旋而出,化作七道血光;蛇女蛇尾横扫,带起腥臭的阴风。
道士不躲不闪,任由血光没入胸膛,却在间不容发之际将铜钱剑刺入自己心口。
鲜血顺着剑身流淌,七盏七星灯同时爆出刺目青光。
‘以吾之血,引北斗之精!
道士长啸一声,剑尖挑起灯焰掷向老鳖。
青光过处,铜钱阵轰然炸裂,老鳖发出非人的惨叫,背甲裂开蛛网纹,涌出墨汁般的黑血。
蛇女趁机偷袭,却被道士甩出的黄符钉在盘龙柱上,符纸燃起幽蓝鬼火,烧得她鳞片卷曲冒烟。
王老汉趁乱冲向河边。
河水已漫过腰际,小宝的襁褓在漩涡中沉浮。
他正要跃入水中,忽觉脚踝剧痛——无数白骨手掌破水而出,将他往河底拖拽。
恍惚间看见父亲的身影在河底招手,手中还握着那柄染血的桃木剑。
‘爹!
王老汉嘶吼着,突然明白为何每年清明,父亲的坟头总会爬满水蛇。
那些蛇眼全是竖瞳,盯着他时像在看猎物。
此刻河底传来万千童声合唱:’还我命来……还我命来……’他低头看去,每只拽他的白骨手上,都系着根褪色的红绳。
千钧一发之际,怀中避水丹的细沙突然自动飞出,在河面结成太极图。
王老汉只觉天旋地转,再睁眼已站在岸边。
道士正将老鳖的魂魄封进铜铃,蛇女则被符咒锁成条三寸小蛇,在道士的酒葫芦里翻腾。
‘河神早被邪祟夺了神位。
道士将铜铃系在腰间,’二十年前这老鳖化作河神模样,诱你爹献祭童男女,实则是在炼化生魂。
那黑驴本是龙宫巡海夜叉,因打翻炼魂炉被贬下凡,碰巧遇上你媳妇,这才引出这段因果。
王老汉望着河面漂浮的襁褓,突然发疯般要往水里冲。
道士拽住他后领:’那是幻象!
说着抛出铜钱剑,剑尖挑起片荷叶,荷叶上赫然映出小宝在自家炕头酣睡的模样。
王老汉这才瘫坐在地,发现裤脚已被冷汗浸透。
归途上月黑风高,道士突然顿住脚步:’跟了一路,还不现身?
话音未落,道旁古槐剧烈摇晃,落下无数槐花。
花雨中走出个青衫书生,手持折扇轻笑:’道长好手段,竟破了本座二十年的布局。
王老汉瞳孔骤缩——这书生眉眼与黑驴将军有七分相似,只是额间多了枚水滴状印记。
道士如临大敌,铜钱剑横在胸前:’龙宫叛徒!
你盗走炼魂炉,在人间炼制活尸,就不怕遭天谴?
‘天谴?
书生摇着折扇走近,脚下槐花自动分开,’当年龙王为渡情劫,强娶民女时怎不见天谴?
我不过取回本该属于我的东西。
他突然抬手,王老汉心口的朱砂痣开始发烫,避水丹的细沙竟穿透衣襟,在他面前聚成个迷你漩涡。
道士脸色大变:’你竟将炼魂炉藏在避水丹里!
书生轻笑,漩涡中浮出座青铜小炉,炉身刻满狰狞鬼面:’多亏这凡人精血温养,如今炉中已有九百九十九个生魂,只差最后一个……’他目光落在王老汉身上,舌尖舔过嘴角,’便是你王家血脉!
狂风骤起,槐树枝桠化作利爪抓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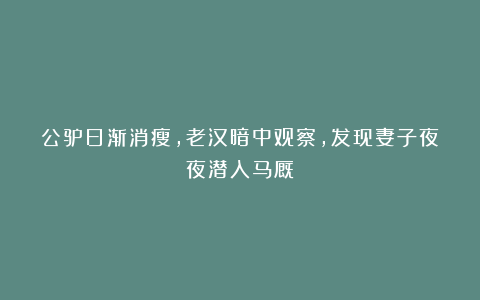
道士甩出七张雷符,符纸在空中结成北斗阵。
书生却化作黑水渗入地下,所过之处青砖爆裂,钻出无数白骨手臂。
王老汉被阴风掀翻在地,怀中掉出个油纸包——正是当年药铺掌柜给的迷魂草。
‘刺他命门!
道士大喝。
王老汉闭眼挥剑,却觉剑锋刺入软泥。
睁眼时书生已现出原形,竟是条百丈青蛟,鳞片上嵌着无数童男童女的面孔。
蛟尾扫过之处,山石崩塌,古槐化作齑粉。
道士咬破中指在虚空画符:’天地玄宗,万炁本根!
符成之际,青蛟突然发出凄厉惨叫,它腹中亮起红光——正是那座青铜炼魂炉。
王老汉福至心灵,将铜钱剑刺入红光处,剑身蝌蚪文骤然亮起,化作锁链缠住炉身。
‘不!
青蛟疯狂扭动,鳞片纷飞如雨。
炼魂炉轰然炸裂,九百九十九道生魂化作金线冲天而起。
王老汉看见妹妹的身影在金线中一闪而过,她手腕上的红绳突然断裂,化作漫天桃花。
青蛟在金光中灰飞烟灭,只留枚水滴状玉佩落在王老汉掌心。
道士拾起玉佩,面色凝重:’这是龙宫信物,那叛徒竟偷了龙王贴身之物。
他忽然盯着王老汉心口:’避水丹与你血脉相融,看来你与龙宫的因果远未了结。
说着将玉佩按在他朱砂痣上,玉佩竟融入皮肤,化作条小龙纹身。
归家时天将破晓,春娥正在院中晾晒草药。
她颈后的青痕已完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枚水滴状印记。
见丈夫归来,她忽然轻笑:’当家的,昨夜梦见条小龙绕着咱家梁柱转了三圈。
话音未落,屋檐下传来细微的龙吟,梁上尘土簌簌而落。
小宝从屋里爬出来,手里攥着半截红绸带——正是当年黑驴脖子上的。
那绸带无风自动,竟在晨光中化作条寸许长的小青蛇,钻进小宝衣襟不见了。
春娥与王老汉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深深的忧虑。
三年后清明,王老汉带着小宝给父母上坟。
路过龙王庙旧址时,忽见荒草丛中立着块无字碑。
碑前摆着七碗清水,水中各浮着枚铜钱。
小宝伸手去捞,铜钱突然化作青鸟冲天而起,在坟地上空结成北斗七星阵。
当夜王老汉梦见黑驴将军。
它额间独角已化作金黄,身后跟着无数童男童女的魂魄。
恩公,河神之位空悬二十年,该有人坐了。
它说着化作金光没入小宝眉心。
王老汉惊醒时,发现小宝枕边放着那枚水滴玉佩,玉佩里游动着条小龙,龙睛正是妹妹当年的模样。
从此青石村多了桩奇闻。
每逢月圆夜,有人看见小宝在河边踏浪而行,身后跟着群光屁股娃娃。
王老汉家的驴棚里,总在深夜传出龙吟般的嘶鸣。
而春娥晾晒的草药,总带着股若有若无的龙涎香……
“爹!”小宝的呼喊穿透浓雾。
王老汉猛回头,只见白茫茫一片中浮着个红肚兜,正是小宝今晨穿的。
他正要伸手去抓,肚兜突然化作团血雾,雾中伸出七只青灰色的婴儿手臂,指甲盖足有三寸长,齐刷刷抓向他面门。
千钧一发之际,腰间玉佩骤然发烫。
王老汉踉跄后退,后背撞上株老槐树,树皮竟渗出暗红汁液。
那七只手臂突然僵住,婴儿面孔从雾中浮现,个个眼眶空荡荡的,嘴角却咧到耳根。
他这才看清,每个婴孩额间都钉着枚铜钱,与当年龙王庙前父亲所用的如出一辙。
“二十年轮回,该还债了。”沙哑的嗓音自头顶传来。
王老汉抬头,见槐树枝桠间倒悬着个佝偻老妪,白发间缠着水草,脖颈处生着鱼鳃,手中竹篾灯笼里燃着惨绿鬼火。
灯笼纸绘着北斗七星,此刻正与罗盘上的铜钱遥相呼应。
老妪突然甩出灯笼,鬼火化作锁链缠住王老汉双足。
他只觉天旋地转,再睁眼已站在龙王庙废墟前。
残垣断壁间升起七座石棺,棺盖缝隙渗出黑水,水面浮着层油亮的磷火。
第一座石棺轰然洞开,爬出个赤身男童,胸口插着半截桃木剑——正是王老汉幼妹的模样!
“哥哥……”男童拖着桃木剑爬来,每走一步,地面就绽开朵血莲。
王老汉浑身血液凝固,想起二十年前那个雨夜,父亲将妹妹按在祭坛上时,桃木剑也是这样缓缓刺入。
男童突然加速,桃木剑尖挑起串铜钱,钱眼儿里垂着缕缕黑发。
“天地玄宗,万炁本根!”清越的剑鸣破空而来。
游方道士踏着北斗步法闯入,手中铜钱剑挑开男童。
剑锋触及桃木剑时,迸发出刺目金芒,男童发出非人的惨叫,化作滩黑水渗入地下。
其余六座石棺同时震动,棺盖缝隙里伸出森森白骨。
老妪在雾中冷笑:“道长来得正好,这七具童尸炼了二十年,正缺个道门真血开光!”她话音未落,石棺齐齐炸裂,七具童尸破棺而出。
每具尸体都生着双色瞳仁,左眼金黄如日,右眼碧绿似月,口中吐出蛇信般的红绸带。
道士甩出七张雷符,符纸在空中结成北斗诛邪阵。
童尸却突然首尾相连,组成个血肉磨盘,将雷符尽数碾碎。
王老汉趁机扑向最近具童尸,想要拔出桃木剑,指尖刚触到剑柄,就听见无数童声在耳边尖叫:“还我命来!
还我命来!”
剧痛自指尖蔓延,他低头看见手掌正在碳化,裂纹中渗出黑血。
道士见状大惊,咬破舌尖喷在铜钱剑上:“这是以龙涎香混着童男童女骨灰炼的尸傀!
王兄快用避水丹!”王老汉闻言,心口玉佩突然化作小龙钻入掌心,伤口处涌出清泉,所过之处焦黑尽褪。
血肉磨盘突然转向道士,七具童尸同时张开血盆大口。
道士急退三步,从怀中掏出面龟甲镜。
镜面闪过河图洛书的虚影,童尸们竟齐齐僵住,眼中日月流转,映出二十年前龙王庙的场景:暴雨倾盆的祭坛上,七个孩童被红绳串成北斗状,父亲手持桃木剑高呼:“以童男童女之命,换我王家百年富贵!”
“原来如此!”道士剑指苍穹,“你父亲当年献祭时,将自家血脉刻进北斗阵眼。
这些童尸实则是被龙宫叛徒炼化的王家因果!”他突然将铜钱剑刺入自己心口,鲜血顺着剑身纹路流淌,在龟甲镜上绘出幅星图。
星图亮起的刹那,童尸们同时抱头惨叫。
王老汉看见妹妹的魂魄从其中具尸体中浮现,手腕红绳化作利刃,斩向其余六尸。
老妪在雾中发出尖啸,竹篾灯笼轰然炸裂,万千萤火虫般的绿点涌向星图。
道士面色惨白,手中剑却愈发璀璨:“王兄,借你龙血一用!”
王老汉不假思索,以铜钱划破掌心。
鲜血滴在龟甲镜上,星图骤然化作实体,化作条金龙冲天而起。
绿点触到龙息便化作青烟,童尸们七窍流血,皮肤下凸起无数蛇形纹路。
老妪突然现出原形,竟是条三丈长的鲶鱼精,背鳍上插着七枚铜钱。
“二十年谋划,竟毁在你这凡人手里!”鲶鱼精甩尾扫来,带起腥臭的罡风。
道士拽着王老汉滚向石棺后方,铜钱剑深深刺入地面。
剑身突然迸发金光,地底传来锁链拖动的巨响。
鲶鱼精惨叫着被拖入地下,地面浮现出幅巨大的河图,七枚铜钱正好落在星位上。
尘埃落定时,东方既白。
王老汉发现掌心伤口已愈合如初,唯有道血绘制的星图烙在皮肤上。
道士跪坐在地,怀中龟甲镜裂成蛛网纹:“那叛徒将炼魂炉藏在黄河龙宫,这些童尸不过是开胃小菜。
若不夺回炼魂炉,不出三月,沿河九省都要生灵涂炭。”
他突然抓住王老汉手腕,瞳孔映出星河倒转:“你体内既有龙血又有凡人魂,正是开启龙宫的钥匙。
只是……”话音未落,河面突然传来龙吟。
二人望去,只见朝阳映照下,整条黄河化作金鳞巨龙,龙首处立着个青衫书生,手中捧着座青铜小炉。
“道长好眼力。”书生轻笑,脚下浪涛化作万千鬼面,“不过这炼魂炉,此刻已认我为主。”他突然抬手,黄河水倒卷而上,在半空凝成面水镜。
镜中景象让王老汉如坠冰窟——春娥正在院中晾晒草药,身后却站着七个童男童女的虚影,每个都对她脖颈虎视眈眈。
“你媳妇当年本该是第七个祭品。”书生指尖轻点水镜,“若非青驴将军捣乱,何至于等二十年?
如今炼魂炉已成,只需用你王家血脉激活,我便能重开龙宫,让这些小家伙都活过来。”他突然弹指,水镜化作利箭射向王老汉。
道士挥剑格挡,剑身却结出冰霜。
王老汉怀中玉佩再次发烫,化作小龙缠上手臂。
书生见状面色微变:“倒是小瞧了你这凡胎。”他突然将炼魂炉抛向空中,炉盖洞开,九百九十九道生魂化作黑烟扑来。
王老汉只觉神魂欲裂,眼前闪过无数画面:妹妹在祭坛上的哭喊、春娥被青驴将军附身时的青痕、小宝枕边的红绸带……突然间,他福至心灵,咬破舌尖将精血喷在玉佩上。
小龙长啸一声,化作金芒没入炼魂炉。
炉身浮现出河图洛书的纹路,将黑烟尽数吸入。
书生大惊失色,正要抢夺,黄河水突然沸腾。
十八道水柱冲天而起,化作十八条蛟龙围住书生。
每条蛟龙额间都嵌着枚铜钱,与当年老鳖背甲上的如出一辙。
道士趁机结印:“北斗注死,南斗注生!
疾!”龟甲镜碎片突然悬浮半空,射出七道金光刺向书生。
书生怒吼着化作本体,竟是条千丈长的黑龙。
它摆尾扫开蛟龙,龙爪抓向炼魂炉。
王老汉不知哪来的勇气,纵身扑向炼魂炉。
指尖触到炉身的刹那,无数童声在脑海中响起:“大哥哥,我们好痛……”
剧痛自指尖蔓延,王老汉却死死抱住炼魂炉。
他看见妹妹的魂魄从炉中浮现,手腕红绳化作利刃,斩向黑龙龙爪。
其余生魂也纷纷效仿,化作万千光刃。
黑龙发出震天动地的惨叫,龙鳞纷飞如雨,每片鳞片落地都化作具童尸。
道士趁机抛出最后张雷符。
符纸在空中结成太极图,将黑龙困在中央。
十八条蛟龙同时吐出龙息,太极图急速旋转,将黑龙逐渐压缩成团黑雾。
王老汉怀中玉佩再次发烫,小龙飞出吞噬黑雾,每吞一口,龙身就凝实三分。
当最后一丝黑雾消失时,朝阳正好跃出地平线。
黄河水恢复平静,炼魂炉化作齑粉随风而散。
道士瘫坐在地,道袍被冷汗浸透:“那叛徒的神魂被玉佩吞了,只是……”他望着王老汉手臂上的小龙纹身,面色凝重,“这龙魂有了实体,怕是会引来更大的麻烦。”
归家途中,王老汉发现掌心星图正在游走,所过之处浮现出条金色脉络。
路过龙王庙旧址时,他鬼使神差地停下脚步。
废墟中立着块无字碑,碑前摆着七碗清水,水中各浮着枚铜钱,组成北斗状。
当他将掌心按在碑面时,铜钱突然沉入水底,碑文缓缓浮现——竟是幅黄河水脉图。
当夜王老汉梦见黑龙。
它蜷缩在片星空中,龙角上站着个青衣童子。“恩公,当年我盗炼魂炉是为救龙宫三公主。”童子指着黑龙腹部,“她被叛徒抽去龙筋,如今魂魄就寄在这龙魂里。
若想救她,需在七月十五前找到三样东西:龙涎香、河图玉、洛书骨。”
王老汉惊醒时,发现小宝正趴在炕边玩红绸带。
那绸带不知何时变成了水蓝色,上面绣着条小龙。
春娥端着药碗进来,颈后青痕彻底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枚水滴状印记,正随着呼吸明灭闪烁。
“当家的,昨夜村里来了个货郎。”她将药碗放在桌上,“说是在黄河滩捡到块玉,看着像河图纹样。”王老汉心中一动,掀开药碗,碗底沉着枚青铜鱼符,正是当年父亲祭河神时用的信物。
窗外忽然传来龙吟。
王老汉冲出门去,只见北斗七星倒悬天际,每颗星子都连着条金线,指向黄河方向。
十八条蛟龙在云中若隐若现,龙首皆朝着王家方向低垂。
他低头看去,掌心星图已蔓延至肘部,金色脉络中流淌着细小的光点,宛如黄河水中的泥沙。
五更梆子响时,王老汉背着包袱走出家门。
春娥抱着小宝站在门槛上,月光将三人的影子拉得很长。
小宝突然挣脱母亲怀抱,跑到王老汉面前,将红绸带系在他手腕上:“爹爹早去早回,小龙会保护你的。”
王老汉抚摸着儿子头顶的旋,忽然发现那旋涡中心嵌着枚金鳞。
他心中剧震,却强作镇定地笑笑,转身踏入夜色。
身后传来春娥的轻唱,是首古老的船歌,调子里带着龙宫特有的颤音。
行至黄河渡口时,东方泛起鱼肚白。
摆渡的老艄公戴着斗笠,竹篙点处,水面浮起朵朵金莲。
王老汉踏上船头,忽觉掌心发烫,星图竟与河面倒影的北斗七星遥相呼应。
老艄公突然开口:“客官可曾听过,黄河底下有座水晶宫?”
话音未落,船身突然剧烈摇晃。
王老汉抓住船舷,看见水下浮起无数青铜灯笼,灯笼纸绘着河图洛书。
十八条蛟龙破水而出,龙首低垂,托着船身向河心驶去。
老艄公的斗笠被风吹落,露出张布满鳞片的脸——竟是当年被道士收服的蛇女!
“龙宫叛徒未除,炼魂炉虽毁,因果犹在。”蛇女甩尾搅动河水,露出河床上的巨大封印,“三公主的龙魂困在此处二十年,就等王家血脉来解。”她突然化作人形,手中捧着个玉匣,匣中盛着半截龙筋,隐隐传来心跳声。
王老汉接过玉匣时,掌心星图突然暴涨。
黄河水倒卷而上,在头顶凝成面水镜。
镜中景象让他呼吸停滞——春娥正在院中给小宝梳头,梳齿间却缠着缕缕黑发。
小宝脖颈后浮现出片龙鳞,鳞片上刻着微缩的河图纹。
“时辰到了。”蛇女突然将王老汉推入水中。
冰凉的水流灌入口鼻时,他听见无数童声在欢笑。
下沉过程中,看见河床裂开道缝隙,缝隙中透出七彩霞光。
十八条蛟龙在头顶盘旋,龙吟声与黄河涛声交织成曲。
当指尖触到裂缝的刹那,王老汉终于明白——这二十年来的种种异象,不过是场跨越阴阳的棋局。
而他自己,既是棋子,亦是执棋人。
掌心星图游走到肩头时,裂缝中传来熟悉的呼唤:“哥哥,快来救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