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CE读书会
复杂网络驱动智能涌现
还记得《E.T.》里那个灯泡般的大眼睛和浑圆脑袋吗?或者《异形》中光滑巨硕的透明头骨?《超体》里的露西更是直接把大脑开到100%,颅骨像气球一样鼓胀。人类对外星人的想象除了异形,似乎总逃不开一个母题——脑袋必须大。
大脑袋=高智慧,这条视觉公式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它成了科幻电影最偷懒也最有效的设定稿:只要把颅骨拉长、额头加宽,观众立刻心领神会——“哦,这家伙很聪明。”但问题来了:如果大脑袋真的那么厉害,为什么地球上千百万年的进化没有把我们全部变成“行走的脑花”?更大的脑,究竟会带来怎样的语言、思维、意识乃至社会形态?是会让我们瞬间解锁宇宙终极奥秘,还是直接把大脑拖入“计算不可还原”的泥潭,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
这篇文章,我们就从银幕上的“大脑袋外星人”出发,沿着神经科学、计算理论与语言学的边界,严肃地追问一句:假如人类的大脑更大更强,会发生什么?我们能否理解更复杂的语言?能否拥有更高的抽象能力?能否突破“计算不可还原性”的壁垒,进入一种全新的心智状态?
一、从“大脑袋”到“大网络”:科幻设定背后的科学伏笔
在灵长类演化史上,“颅骨变大”确实与认知能力跃升同步出现。化石记录显示,南方古猿的脑量约400–500ml;能人突破600ml;智人则稳定在1300–1500ml。这种“脑量-工具-社会”三者同步放大的现象,被人类学家称为“认知镍币”:每多100ml,似乎就能多容纳一层社会关系、多记住一种工具制法。于是,电影美工把颅骨加宽视为智能外挂的速记符号,其实暗合了我们对演化史的直觉。
然而,演化也给出反例:抹香鲸脑重约7-8kg,人脑约1.3-1.5kg,但抹香鲸并没有比人更聪明。原因在于抹香鲸整个脑神经元总量估计只有20-30G(10亿),且大部分挤在小脑,新皮层神经元反而比人少(≈10-12G,人脑皮层神经元≈16G)。也就是说,鲸的“多余”脑组织主要是给巨型身体做实时运动控制,而不是做抽象推理。且鲸体重30–50t,人只有60-80kg,人的脑化指数(Encephalization Quotient,EQ,与可观测的认知灵活性在哺乳动物里高度相关)为7,抹香鲸仅为1.5–2,与黑猩猩持平。换言之,“大”不等于“密”,更不等于“高效”。科幻电影忽略的是:如果仅仅放大颅骨而不重构折叠模式、轴突直径与髓鞘厚度,信号延迟将随距离线性放大,“思维网速”反而下降。
过去十年,GPT、PaLM、Gemini 等系列模型让我们首次系统观测到“脑规模放大效应”——随着人工神经网络规模的不断扩大,它们似乎依次跨越了一系列能力上的“门槛”:
图1 不同规模人工网络跨越的能力阈值
从识别手写数字,到生成流畅的自然语言文本,这些“能力阈值”并非线性出现,而是在特定参数量、数据量、训练深度组合下突然涌现——就像电影里的外星人突然开口说莎士比亚。
二、语言:三万个词,够了吗?
人类语言大约有3万个常用词。这个数量看似随意,却并非偶然。它与我们大脑的工作记忆、感知通道、社会交流需求密切相关。我们之所以不需要更多词,是因为我们的大脑只能处理有限的概念,并通过抽象将大量具体事物“打包”成更少的类别。若一个词对应一个“涌现概念”,则3万约等于大脑可稳定区分的“吸引子”数量。
但如果我们拥有更大的大脑,是否就能处理更多词汇?答案是肯定的。但问题不在于“能不能”,而在于“有没有必要”。更大的大脑可以支撑更丰富的概念空间,甚至可以将原本需要嵌套表达的内容压缩为单个词汇。想象一下,你要为“第257种云朵波纹”单独记一个单词,而它只在赤道太平洋出现——大脑会抗议:“这不值得占一个突触。”
这种“语法扁平化”可能带来更快的交流速度,但也可能牺牲表达的灵活性和细微差别。我们已经在专业术语中看到这种趋势:一个“熵”字可以代替一整段描述,但只有经过长期训练的人才能理解其真正含义。这类词让同行“一句话跑完一段程序”,却让外行“一句话坠入深渊”。更大的大脑或许能将这种“术语化”推广到日常语言中,从而构建一种“高密度语言”——更少的词,更高的信息密度——届时,一句寒暄可能等价于一篇博士论文。
三、语法:嵌套的极限与计算的边界
人类语言的语法大致处于“上下文无关”这一层级。我们可以理解嵌套结构,如“那只被狗追的猫咬过的老鼠死了”,但嵌套层数通常不超过4层[1]。超过4层嵌套这个认知悬崖后,理解错误率指数上升。这是因为我们的工作记忆只能容纳4±1个“组块”。
更大的大脑可以支持更深层的嵌套,甚至可以使用“上下文有关”的语法结构——例如跨越多层的主谓一致、元音和谐等。电影《降临》中的七肢桶语言正是“超嵌套”极端[2]:一个符号同时包含过去、现在、未来所有时态,主语、宾语、从句、修饰语被折叠成同时并存的枝节。人类读者必须瞬间整体接收——任何试图“从左到右”扫描的企图都会破坏信息完整性。人类只能一眼看完,无法逐字说出——因为我们没有非线性输出硬件。
图2 电影《降临》中的外星七肢桶语言
上下文有关的语法结构也意味着解析时间呈指数级增长,最终陷入“计算不可还原性”的泥潭。计算不可还原性是大脑无法翻越的墙。许多复杂系统(如天气、湍流、市场)都具有这种性质。大脑之所以能理解语言,不是因为它能模拟整个系统,而是因为它能抓住系统中的“可还原小口袋”,在几百毫秒内把感官洪流压缩成单一决策。它必须忽略 99.99% 的微观细节,只抓住那些可还原的宏观序参量(对称性、守恒量、吸引子)。“不可还原”不是缺陷,而是背景——正是它衬托了“可还原”的珍贵。
更大的大脑可以抓住更多的小口袋,但它仍然无法突破“通用计算”的壁垒。因为一旦进入通用计算,你就需要无限时间和无限内存,而这是任何有限系统(包括大脑)都无法承受的。
四、抽象:从概念到元概念,再到“规则域”
抽象是人类最强大的能力之一,其价值在于:用低计算量预测大范围行为。我们从“老虎”“狮子”中抽象出“大型猫科”,再从“猫科”中抽象出“哺乳动物”,最终进入“生物”“系统”“复杂性”这样的高阶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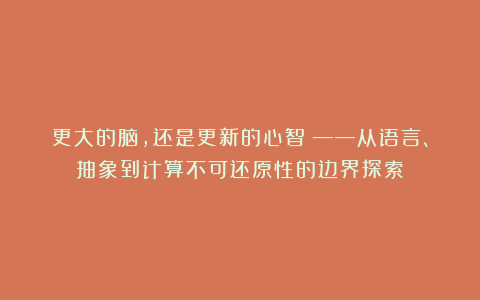
但抽象并不是无限的。它依赖于“可还原性”——即世界中存在的规律性和结构性。任何抽象,底层都是某个可还原小口袋的映照:若某抽象有用,意味着可“总结”或“跳步”,无需走完所有计算或细节。抽象之塔便可视为可还原小口袋的网络。我们可以想象的底层抽象针对概念空间(如数学定理推导),再往上针对方法空间(研究生成定理的方法),再往上则针对方法的方法(如哥德尔不完备定理)……
这座塔的终极顶点,是一个被称为ruliad(规则域)的概念——所有可能计算、所有可能数学、所有可能物理的总和。它不是一个系统,而是所有系统的纠缠极限,是所有可还原小口袋构成的无限网络。
图3 ruliad无限网络
受到生理结构的限制,我们这种大脑从 ruliad 中所能感知的,正是我们目前所知的物理(与数学)核心定律——只是ruliad网中的一个极小角落,或者说某条特定路径。不同的路径在ruliad中有无数条,每一条可能都对应一种不同的大脑的演化历史。我们拥有更大的脑,也许可以在这条路径上走得更深远,但很难跨越到别的路径上。更别说一览整个ruliad,因为那需要无限的计算能力。
五、多线程心智:从“意识流”到“意识图”
我们的大脑只能维持一条“意识流”。这不是巧合,而是因为人类作为动物需要做出统一决策——下一步往哪走?说什么?我们一次只能朝一个方向走,只能说一件事,脑似乎才进化出“只生成单一决策流”这一根本特征。
但是我们的意识流只占全部神经活动的极小一部分。大部分活动更像自然界中的典型过程,无数元素各自为政。可将其视为“无意识神经活动之海”。
但如果我们拥有多线程心智,会怎样?我们将不再是一个“我”,而是一个“我们”——一个由多个并行经验流构成的复合体。这种心智不再是“类脑”的,而是“类社会”的,在其中经验流可以分支与合并。事实上,社会本身就是一种多线程系统。每个个体都是一个线程,语言等工具则是线程之间的通信协议,将个体编织成一个连贯的社会。这种类社会的心智和我们在物理宇宙的低层结构中所设想的情况一样,尤其是在量子力学中。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一个“类量子”的大语言模型系统,它能生成一个不同文本序列的图结构。但仅仅增加大脑中的神经元数量,而不改变整体架构,是无法实现这一点的。我们必须采用一种不同的、多路的架构——在这种架构中,我们拥有的是一个“意识图”,而非原来的意识流。
支持多线程心智的全新语言也会出现,它将不依赖于“线性序列”——它可以是一棵树、一张图,甚至是一个超图。我们可以通过肢体语言进行辅助交流,但我们没有支持图像输出的硬件使新的语言成为主流。
但要这样,我们需要的就不仅是更大,而是不同。
六、超越我们的心智
人类总倾向认为——或希望——自己的心智已“登顶”。但自然界处处皆计算,我们的大脑相比于自然界的计算被设为更定向、更受限的模式:海量感官进,少量行动出。
我们今日的三万词汇、四层嵌套、单线意识,不是进化的终点,而是“类脑系统”在有限资源下的最优解。维特根斯坦说“语言的界限即世界的界限”。若总体架构不变,脑更大后,我们可以存储更多的抽象概念,可以使用更深的嵌套深度,但会否出现质的不同?若抛开“类脑”限制(不再把海量感官压成少流决策),我们便进入通用计算疆域,处处不可还原,难以谈论。
与“更大脑”互动会是什么体验?从根基看,任一心智都可视为位于 ruliad 某点。心智交流时,交换的是 ruliad 里似粒子般稳健的“概念”,它们在 ruliad 中传播而不变。更大脑内部或许使用我们闻所未闻的海量词与概念,但它仍能生成“傻瓜版”粗糙翻译供我们懂。我们或对其众多抽象与高阶构造基本盲然,一如狗听人聊哲学。
更大、更新的脑极限何在?是否存在可以全视整个 ruliad 的心智,它将蕴含一切可能计算。但那样的存在已非类人心智,因“是一切即什么都不是”,再无从辨识个体经验线程。
井蛙不可语海,夏虫不可语冰。我们所能想象的,仍然困于我们的这一条抽象路径。我们所不能想象的,才是真正的不可达之境。我们能做的,不过用有限的目力,向无限的苍穹,投一瞬间的仰望。
参考资料
[1] Gibson, E. (1998). Linguistic complexity: Locality of syntactic dependencies. Cognition, 68(1), 1–76. https:///10.1016/S0010-0277(98)00034-1
[2] Alberto P. (2020). Crossing the Threshold of Temporality: Story of Your Life and Arrival. Journal of Art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University of Turin).
https://ojs./index.php/jamit/article/download/4152/4155/14288
[3] Wolfram S. (2025). What if we had bigger brains? Imagining Minds beyond Ours.
https://writings./2025/05/what-if-we-had-bigger-brains-imagining-minds-beyond-ours/
#artContent h1{font-size:16px;font-weight: 400;}#artContent p img{float:none !important;}#artContent table{width:100% !import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