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的凤凰花一年两季盛开,热烈得像从未熄灭的火焰。
15 岁的那个夏天,当凤凰花将校门前的道路染成通红时,一个穿蓝裙的女孩 “阿蓝”,也就是我的幻觉,随着精神分裂症的阴影,悄悄闯进了我的青春。
她曾是耳畔引导我走向黑暗的暗语,是推我走向孤立的推手,是握在手中冰冷的小刀,甚至给了我自杀的命令…直到咖啡香漫过老骑楼的窗台,在我每天都去的“屿你咖啡”里研磨咖啡豆的沙沙声里,我才慢慢懂得 —— 与“她”共处,或许是和这个疾病和解的另一种方式。
920郁友节来了,欢迎报名参加
厦门的凤凰花刚落满枝头时,15岁的我第一次听见了她的声音。那声音起初像沙茶面蒸腾的热气,模糊又温热,后来变成轮渡码头的潮声,带着尖锐的回响,最后具象成穿蓝裙的女孩“阿蓝”——她会在课堂上扯我的衣角,会在同学说笑时凑过来喊“他们在骂你”,更会在我躲在阳台哭时,递来一把削铅笔的小刀。
这是一段被精神分裂症困住的青春,在厦门的老骑楼与新校舍间,我经历了人际关系的崩塌、三次想逃离校园的挣扎,直到辍学后走进那家满是咖啡香的小店,才慢慢学会:不必把阿蓝当成敌人,或许我们可以一起,在研磨咖啡豆的沙沙声里,找到和世界相处的方式。
厦门的夏天总是又湿又热,2023年九月,我背着新书包走进高一教室时,凤凰花正把校门口的路染得通红。那时候的我还不知道,有个穿蓝裙的女孩,会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悄悄住进我的生活。
刚开始只是些细碎的“异常”。早读课上,我盯着语文课本上的“鼓浪屿”三个字,突然听见有人轻轻喊我的名字,像从很远的地方飘来,带着海风吹过的咸涩。我猛地回头,后桌的同学正低头刷题,窗外只有蝉鸣和扫地阿姨的扫帚声。“肯定是太紧张了”,我揉了揉耳朵,把注意力拉回课本,可那声音像根细针,时不时扎我一下。
真正注意到她,是在第一次月考后。我数学考砸了,坐在操场的看台上哭,眼泪掉在校服裤上,晕开一小片湿痕。突然,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我抬头,看见个穿天蓝色连衣裙的女孩,梳着齐刘海,眼睛像厦门的海水一样亮。“别难过啦,他们都不懂你”,她蹲在我身边,声音软乎乎的,手里还拿着一朵刚摘的凤凰花。
我以为是隔壁班的同学,想问她名字,可转头的瞬间,她就不见了。风卷着凤凰花瓣落在我腿上,我揉了揉眼睛,怀疑是自己哭花了眼。那时候的我,还把这当成青春期的小插曲,就像厦门偶尔的雷阵雨,来得快去得也快。
可她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多。上课时,我会突然听见她在耳边说“老师讲错了”,害得我忍不住举手反驳,被全班同学盯着看;放学路上,她会指着迎面走来的同学,小声说“他们在背后说你坏话”,让我攥着书包带,快步躲开;甚至晚上躺在床上,她会坐在我的书桌前,翻我的日记本,念出那些我写给自己的秘密。
我开始变得越来越敏感。同桌借我的橡皮,我会觉得她是想偷偷看我的笔记;组长催我交作业,我会觉得她是故意针对我。有次班会课,老师让大家自由组队做项目,我看着同学们三三两两凑在一起,阿蓝在我耳边说“没人愿意跟你一组”,我突然站起来,大喊“你们都别装了”,然后哭着跑出了教室。
那天晚上,妈妈带我去了厦门市精神卫生中心。医生拿着我的量表,跟妈妈低声说着什么,我坐在走廊的椅子上,阿蓝蹲在我脚边,拉着我的衣角说“他们要把你关起来”。最后,医生把诊断书递给妈妈,我瞥见上面写着“精神分裂症(偏执型)”,像一块冰凉的海蛎壳,砸在我心上。
确诊后,我开始吃药。白色的药片吞下去,白天总是昏昏沉沉,晚上却翻来覆去睡不着。阿蓝好像也怕那些药,出现的次数少了些,但只要药效一过,她就会立刻冒出来,比以前更凶。
学校成了我的“噩梦场”。我坐在教室里,总觉得同学们在偷偷议论我,他们的笑声、咳嗽声,在我听来都是嘲笑。有次上体育课,我跑八百米时不小心摔了一跤,膝盖擦破了皮,阿蓝在我耳边喊“他们都在看你笑话”,我爬起来,不管不顾地冲出了操场,跑过校门口的凤凰花树,跑过老骑楼底下卖沙茶面的小摊,一直跑到海边才停下。
海风裹着咸湿的味道吹过来,我坐在沙滩上,看着远处的鼓浪屿,阿蓝坐在我身边,手里拿着一根树枝,在沙子上画圈圈。“你看,连海都知道你很没用”,她的声音像海浪一样,一下下打在我心上。我捡起脚边的石头,想扔向大海,可手却不听使唤,反而砸向了自己的膝盖,直到妈妈找到我时,我的膝盖已经肿得老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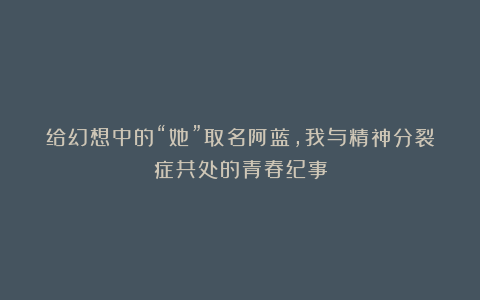
妈妈跟学校申请了休学,我把自己关在家里,不出门,不说话,每天抱着枕头坐在窗边。我们家住在老骑楼里,楼下就是热闹的菜市场,卖鱼丸的阿婆会喊着“新鲜的鱼丸哦”,卖水果的大叔会跟顾客讨价还价,可这些声音在我听来,都像是阿蓝故意放给我听的噪音。
有次妈妈让我下楼买瓶酱油,我戴着口罩,低着头,快步走向小卖部。路过一家卖海蛎煎的小摊时,摊主阿姨笑着跟我打招呼:“小姑娘,好久没见你啦”,阿蓝突然在我耳边喊“她想害你”,我吓得把手里的钱掉在地上,转身就跑,连阿姨喊我的声音都不敢回头听。
我尝试过赶走阿蓝。我把她“坐过”的椅子搬到阳台,用消毒液反复擦;我把她“念过”的日记本锁进抽屉,钥匙藏在鞋底;我甚至在房间里贴满了“不许进来”的纸条,可她还是能轻易找到我,在我吃饭时抢我的筷子,在我洗澡时敲浴室的门,在我睡觉时趴在我的床头,跟我说话到天亮。
最严重的一次,是我偷偷停了药。那天晚上,阿蓝变得特别兴奋,她拉着我的手,让我跟她一起“离开这个讨厌的地方”。她带我走到阳台,指着楼下的巷子说“跳下去就自由了”,我爬到阳台的栏杆上,冷风灌进我的衣服,就在我要往下跳时,妈妈突然推开房门,把我抱了下来。
妈妈抱着我哭,说“慧慧,我们再去看医生,好不好”,我看着妈妈红肿的眼睛,阿蓝在我耳边说“她只是假装关心你”,可我第一次没有听她的话,而是点了点头,因为我突然发现,妈妈的肩膀,比阿蓝的手更温暖。
第二次从医院出来,医生跟我说,除了吃药,还要试着“找一件能让自己静下心来的事”。妈妈想让我去学画画,可我看着画板,阿蓝就会在我耳边说“你画得真丑”;妈妈想让我去学钢琴,可我坐在钢琴前,阿蓝就会把琴键按得乱七八糟。
直到有天,妈妈带我去中山路的一家咖啡店。那家店藏在老骑楼里,门口挂着一块木牌子,写着“屿你咖啡”,念起来软乎乎的。老板娘是个三十多岁的姐姐,笑着跟我们打招呼,店里飘着浓郁的咖啡香,混合着烘焙面包的味道,让人觉得很踏实。
“要不要试试磨咖啡豆?”老板娘递给我一个手动磨豆机,还有一把咖啡豆。我握着磨豆机的手柄,慢慢转动,咖啡豆被磨成粉末的沙沙声,像厦门雨季里的雨声,很轻,很柔。阿蓝站在我身边,没有说话,只是歪着头,看着我手里的磨豆机。
那天之后,我每天都会去那家咖啡店。老板娘教我认咖啡豆,告诉我阿拉比卡豆的酸,罗布斯塔豆的苦;教我打奶泡,看着牛奶在蒸汽枪下变成绵密的泡沫;教我拉花,虽然我总是把爱心拉成歪歪扭扭的圆圈,但老板娘总会笑着说“没关系,下次再试试”。
刚开始,阿蓝还会在我操作时捣乱。我称咖啡豆时,她会喊“少了少了”;我打奶泡时,她会凑过来说“烫到手啦”。有次我给客人做拿铁,她突然在我耳边尖叫,我手一抖,咖啡洒在了吧台上。我红着眼圈想躲进后厨,老板娘却递来抹布:“没事呀,刚开始都这样,我以前还把浓缩咖啡倒进糖罐里呢。”
客人也大多是温和的。有个常来的老爷爷,每次都点一杯美式,会笑着看我磨咖啡:“小姑娘磨得仔细,咖啡都香些。”有次阿蓝又在我耳边说“他在偷偷笑你笨”,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小声问老爷爷:“我是不是磨得太慢了?”老爷爷愣了愣,随即笑了:“慢工出细活嘛,喝咖啡就是要慢慢来。”
那天晚上,我坐在店里的窗边,看着窗外老骑楼的灯光,阿蓝趴在吧台上,手指戳着磨豆机的纹路。“他们好像……没那么讨厌?”她小声说,声音比以前轻了些。我没说话,只是把一颗没磨的咖啡豆递给她,她捏在手里,转了转,没再吭声。
后来阿蓝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少,就算来,也大多是安安静静地待着。我做咖啡时,她会坐在角落的椅子上看;我收杯子时,她会偶尔指一指“那个杯子没摆好”。有次厦门下大雨,店里没客人,老板娘放着舒缓的音乐,我磨着咖啡豆,阿蓝突然说:“这个声音好听。”我抬头看她,她的蓝裙子在暖黄的灯光下,好像柔和了许多。
现在我已经在咖啡店做了半年多,老板娘说我可以算半个咖啡师了。我学会了根据客人的口味调整咖啡的浓淡,还能拉出勉强像样的树叶拉花。妈妈偶尔会来店里看我,坐在角落的位置,看着我忙碌,眼里的担忧慢慢变成了笑意。
前几天凤凰花又开了,落在咖啡店的窗台上。我捡起来放在吧台上,阿蓝蹲下来,用手指轻轻碰了碰花瓣。“以后……我们就在这里好不好?”她问。我点点头,给她倒了一杯凉白开——以前总觉得她是要把我拖进黑暗的影子,现在才明白,或许她只是我心里那个害怕孤单的小孩,而咖啡香、老骑楼的灯光和温柔的人们,让我们都慢慢找到了停靠的地方。
厦门的雨季还会来,但我不再怕了。研磨咖啡豆的沙沙声里,我和穿蓝裙的她,正一起学着和这个世界好好相处。
备注:每个人的成长经历和家庭情况都不一样,因此,文章中的分享,仅做参考。如果你喜欢这篇文章,欢迎在文末打赏,支持原创。欢迎分享自己抗郁路上的故事,有公益稿酬喔。点击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