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洲子
全文刊载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3年第2辑,第85-95页,注释从略。
一般而言,讨论禅宗佛教某一派别的兴盛,当从思想史的路径入手:独特的教义风靡于世,是佛教派别取得成功的基础。宗教社会学的研究却表明,“大多数人是在归信以后才开始对某种宗教的教义产生情感”。在中国历史上,士人普遍具有文化身份的混合性,并不存在专注某家教义的倾向。至于普通民众,更注重宗教的功能性,对教义差异的关注微乎其微。
另一方面,思想史的研究方式必须选择思想具有代表性的禅师展开研究,而代表性禅师的确定实际上是一个颇为主观的问题。无论“代表性”禅师数量在研究中如何增长,始终不可能将宗派内僧人全数涵盖。那么,置“非代表性”禅师于不顾,是否能如实反映整个僧团传法的全貌便令人生疑。
由于以上两方面原因造成研究过程中的内在矛盾无法调和,既有思想史研究路径并不适合解释禅宗僧团兴起的具体原因。现代宗教社会学研究提示:“当人们改换教会甚至宗教时,通常不是因为他们的喜好改变了,而是因为新的教会或信仰更有效地吸引了人们一直就有的喜好”。那么,是否可以在既有思想史研究路径之外,找到僧团成功迎合信众喜好的内在原因,成为研究者需要思考的问题。
北宋时期的云门僧团为我们探究禅宗僧团兴起之因提供了绝佳案例。该僧团由五代时期云门文偃禅师创始,发展至北宋其道大振,“天下尚之,号为云门宗者”,列于禅宗“五家宗派”之一。目前确切可考的北宋云门禅师总数有1180人之谱,其中不少禅师有丰富行迹资料存世。前贤虽已注意到该僧团在北宋的快速发展并试图解释其原因,但所论却脱离了时代背景。关于北宋时期云门僧团兴起的具体原因,尚待进一步揭示。
为了排除“代表性”禅师干扰、展现僧团传法全貌,笔者首先试图复原北宋云门僧团传法的时空过程。通过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制作核密度分析图,展示、归纳出云门僧团传法的代际空间分布特征(下文图中颜色越红,核密度值越高,表示越聚集;颜色越绿,核密度值越低,表示越离散)。进而以时空分布特征为线索,探寻云门僧团传法在局部地区形成集聚的原因。最后探讨云门僧团获青睐的思想基础,及其对整个僧团兴盛的具体影响。
一 北宋云门僧团兴起的时空过程
(一)云门二、三世传法分布
云门二世禅师传法时期,云门僧团发源地南汉仍是其主要化区,于此弘法者多达32人。另外,云门僧团在南唐亦迅速发展,荆湖一带也成为云门二世的重要化区。云门僧团传法扩张与南汉、南唐的开疆拓土相始终。乾祐三年(950)“荆南、岭南(南汉)、江南(南唐)连谋,欲分湖南之地”。广顺元年(951)十月,南唐攻占南岭以北除朗州之外的南楚旧境;是年十一月,南汉趁南唐在楚地立足未稳,夺取南岭以南的南楚之地。两个支持云门僧团的政权进占南楚,为云门二世在该地的弘法奠定基础。观察图1可以发现,其北上路径,大致与隋唐时期佛教活动沿湘水中游分布的旧有格局相合,并一直波及荆襄地区。文偃法嗣慧通归柔开法郢州可以为证。由此可见,随着南唐与南汉吞并南楚,云门僧团往荆襄进发的通道已经打开。此外,蜀地也是云门二世开法者集中之处(图1)。
图2 云门三世传法分布示意图(1004年)
(二)云门四世传法分布
云门四世总人数为110人。灯录未记载福昌惟善法嗣开圣道如、开福昌贤法嗣日芳上座、智门光祚法嗣太平清3人住持寺院的府州地理信息。而开圣寺、太平寺在北宋版图内又有多处,难以遽定,故暂不予出图显示。图3中实际显示107名云门四世禅师的传法分布。如图3所示,云门四世传法格局在云门三世的基础上有了一些变化。
图3 云门四世传法分布示意图(1030年)
其一是岭南的云门禅学开始衰落。除去图中直接显示岭南地区开法禅师数量的减少之外,时人观察也透露出这种变化。余靖《韶州乐昌县宝林禅院记》记载:宝林圆祐被韶州官方远邀至岭南开法,当地禅学人才的匮乏于此可见。仁宗时朝廷要绍隆南宗祖席韶州南华寺,“诏于衡庐择人”也是其例。余靖为净源邵思所作塔铭,对于岭南禅学凋敝的反映更为明确。《塔铭》记载,净源邵思为韶州曲江人,于韶州南华寺出家、受具。其叹曰:“身居曹溪,漫不知其门域,当自愧其名”,遂起游方之念。可见岭南禅学之衰落。而邵思自云门五世洞山晓聪处得悟以归,韶州官员“以近郭名蓝,宜择知宗乘者统领其众”,召其住持净源山定慧禅院。此事表明士人也察觉本地禅学滞后,向江西、湖南学习成为提升本地禅学格调的途径。
其二是云门僧团在长江中游地区分布密度增大,特别是在江南西路的发展尤为显著。余靖《筠州洞山普利禅院传法记》虽然仅记洞山一寺之事,却可看出云门僧团在江西发展的反复:云门二世清禀继玄沙四世文坦之后住持洞山。不过,洞山并未从此完全进入云门僧团的掌控。清禀继任者“豫章彦闻”,灯录、僧传失其名,不可考。继彦闻者守诠(《景德传灯录》卷26作“义诠”)乃雪峰四世归宗道诠法嗣。自晓聪以降,洞山法席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由云门僧人世袭:晓聪嗣法云门三世文殊应真,并在示寂前将法席交付云门三世五祖师戒的法嗣自宝,自宝再传法席予弟子鉴迁。此所谓“聪与迁皆云门之嗣孙”。值得注意的是,彦闻欲传寺其徒,被外护阻断。晓聪传寺予法眷自宝,却获得通过。后先对比,反映出云门僧团在江西的传法根基逐渐牢固。自宝住持洞山期间,“自江湖之南及岭之南二十余州闻其名者,岁奉钱共数十万以供其堂”。
其三是云门僧团势力进一步向王朝版图的东面挺进。自从吴越时期清凉文益法脉传衍至此,该地渐成玄沙—法眼化区的核心。宋代地方官有意打破这种垄断。具有标志意义的事件是号为“天下胜处”的杭州灵隐寺住持人选的更替。《故灵隐普慈大师塔铭并序》记载,普慈幻旻(999—1059)得法于玄沙七世、灵隐住持惠明延珊。及延珊示寂,延珊同门、玄沙七世惠照蕴聪继主灵隐。此后,官方阻断了灵隐住持甲乙相传。虽然后来杭州知州孙沔(990—1066)“特迁之(幻旻)主灵隐”,但是玄沙法裔世代住持灵隐寺的惯例已被打破。与玄沙僧团的处境不同,云门四世盛勤、重显纷纷开堂说法于原属玄沙僧团的寺院。
(三)云门五世传法分布
云门五世禅师共计205人。泐潭怀澄法嗣令滔首座、云盖继鹏法嗣白霞安、育王常坦法嗣湖山择贤住持寺院信息失载,故图4实际显示202人传法分布。如图4所示,云门五世的传法分布在王朝版图东部的密度进一步增大,成为与长江中游地区并重的传法重心。这与雪窦重显、资圣盛勤等先期进入两浙路化区传法的云门四世禅师有着直接关系。作于宝祐三年(1255)的《本觉禅院记》记载:资圣盛勤法嗣本觉省文熙宁间受命住持本觉禅院。其得以从蜀地跋涉千里至秀州嘉兴县开法,离不开其师盛勤皇祐初“领徒于此(秀州)”开拓之功。
图4 云门五世传法分布示意图(1059—1064年)
图5 云门六世传法分布示意图(1077年)
自唐以来,禅家盛行于世者,惟云门、临济两宗。是时云门苖裔分据大刹,相望于淮浙之上。临济之后,自江以北,惟师一人。
图6 云门七世传法分布示意图(1100年)
临济九世建隆昭庆(1027—1089)在长江以北势单力薄,反衬出云门僧团在此地区的强盛。通观其时北宋版图内的传法形势,云门僧团的传法重心已经转移至北宋版图北部和东南。
今之禅宗最盛者天衣之徒。天衣之大弟子曰北京元公、慧林本公、法云秀公,隐然名闻于天子,而累朝耆徳、大臣暨公卿大夫士,莫不降辞气以礼之。而三公之嗣法者,其盛尚胜计耶。惟是二〔三〕公之外,又有长芦夫公,则高山在四岳之外者也。
始,径山祖师有约,后世止以甲乙住持。予谓以适事之宜而废祖师之约,当于山门选用有德,乃以琳嗣事。众初有不悦其人,然终不能胜悦者之多且公也,今则大定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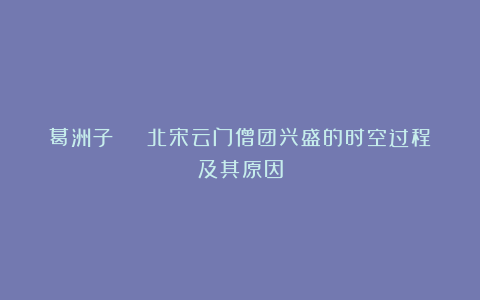
洪州奉新县惠安院,门临道左。衲子往还泐潭、黄龙、洞山、黄蘗,无不经由。偶法席久虚。太守移书宝峰真净禅师,命择人主之。······时有渊首座,······渊白真净曰:“慧渊去得否?”真净曰:“你去得。”遂复书举渊。渊得公文,即辞去。
(云居了)元谓其徒曰:“吾与伊人(寿圣海渊),同灯分焰,宜有契分。”
自唐以来,天下士大夫争以排释老为言,故其徒之欲求知于吾士大夫之间者,往往自叛其师以求其容于吾。而吾士大夫亦喜其来而接之以礼。
是时北方之为佛者,皆留于名相,囿于因果,以故士之聪明超轶者皆鄙其言,诋为蛮夷下俚之说。(怀)琏独指其妙与孔、老合者,其言文而真,其行峻而通,故一时士大夫喜从之游。
惠远和尚以有道称于四方,在天禧、乾兴间,其名甚振,学者无远近,归之如水沛然就下。予少闻之,恨不识其人。晚游吴,得其语于勤、暹二师。观其发演详悉,应对次序,语言必文,不以凡近杂出,虽出入大经大论,傍及治世文书、老子庄周之说而不疑。
天禧间,值于淮甸。会将《中庸》《大学》,参以《楞严》符宗门语句质显。显曰:“这个尚不与教乘合。况《中庸》《大学》耶?”
三 云门僧团“列派皇都”与最高统治者的支持
(一)“列派皇都”:云门禅师开法东京的取向
北宋云门僧团的另一个空间分布特征是密集开法于都城东京。在“十方住持”的背景下,获取地方官员支持其实是各个僧团一致的努力目标和践行方向。然而,过分依赖禅师与士人的私交,很容易落入人亡政息的危险中。《补续高僧传》记载惟琳的例子足以为鉴:
熙宁中,东坡倅杭,请住径山,继登慧渊公法席。丛林蔚然,众心归附。久之惮烦,退静于邑之铜山,结庵名无畏,自号无畏大士。······始师之居铜山也,院有松合抱,县大夫将取以治廨。······宣和元年,师既老,朝廷崇右道教,诏僧为德士,皆顶冠,师独不受命。县遣使谕之,师即集其徒说偈趺坐而逝。
云门六世无畏惟琳与苏轼私交甚笃,受苏轼青眼而入主径山。苏轼被贬离杭后,惟琳便因失去外护而不断遭遇传法困境。从另一角度看,云门四世以降云门禅师出世开法形成全国性风潮,显然也不可能单纯依凭几个地方官员可以实现。
宋真宗曾于大中祥符二年(1009)诏云门三世西峰豁至内廷问询宗要,此后整整40年未见云门僧团僧人再涉足帝京传法。直至南华宝缘受宋仁宗敕命住持韶州南华寺,才将云门僧团与最高统治者再度联系起来。皇祐元年(1049)内侍李允宁奏以汴京第宅“创兴禅席”,仁宗赐额“净因”,“诏求有道者居之”。作为王朝首善之地建立的第一座禅宗寺院的示范意义不言而喻。最后云门五世大觉怀琏领命住持,“效南方禅林仪范,开堂演法”。
元丰五年(1082),宋神宗诏东京相国寺辟六十四院为八禅二律,“以东、西序为慧林、智海二巨刹,诏净慈宗本禅师住慧林,东林常总禅师住智海”。圆照宗本与东林常总分别为当日云门禅师和临济禅师之翘楚。从人事安排推测,朝廷本意是对当日两大禅宗派别的拉拢。然而常总固辞,神宗遂诏本逸住东京大相国寺智海禅院,“赐号正觉。朝中搢绅益钦道望”。慧林、智海两院住持之位遂均落入云门僧人之手。皇帝敕住的案例在云门六、七世僧人中的案例又有增加,法秀受神宗诏为东京法云寺“开山第一祖”,“云门宗风自是兴于西北,士大夫日夕问道”。
云门五、六、七世禅师连续出住东京名刹,云门僧团抢占了开法京师禅席的制高点,呈现出“云门列派皇都”的盛况。京师是王侯显贵聚居之地,怀琏住持的净因寺作为云门僧人在京师活动的据点,拉近了他们与高层统治者的空间距离,对于拓宽云门僧人开法渠道的作用不可小觑。云门七世佛国惟白利用住持东京法云寺的便利,继续“同灯分焰”的使命。《续灯录》记载:云门七世开先智珣历住延昌、开先。惟白为高其道誉,“回奏帘赐章服”。而云门六世招提惟湛得以入阙问对更是以“侍佛国白禅师”为契机。而后,惟湛“出世招提,屡迁巨刹”。
(二)“道合圣心”:云门僧团受皇帝支持的思想基础
将考察范围拓展可以发现,争取最高统治者支持大抵是禅宗僧团在五代宋初的共识。然而,最终呈现出“列派皇都”的却是云门僧团。上文的梳理显示,宋都开封禅寺住持多属敕差,“列派皇都”并非单纯依靠云门禅师的主观意愿和努力便可实现。宋仁宗与大觉怀琏发生的问对,给予观察者一点线索。据记载,仁宗曾召怀琏入化成殿,问佛法大意。《禅林僧宝传》称其“奏对称旨”,《续灯录》则表述为“道合圣心”。那么,云门禅师身上的哪一点特质符合了北宋皇帝的“圣心”?《禅林宝训》引《九峰集》记载大觉怀琏告诫弟子说:“前辈有聪明之资,无安危之虑。如石门聪、栖贤舜二人者,可为戒矣。”
这段话透露出怀琏强烈的居安思危意识。“石门聪”和“栖贤舜”身上发生何事,使得怀琏不得不引以为戒?《大慧普觉禅师宗门武库》记载:
慈照聪禅师,首山之子。咸平中住襄州石门。一日太守以私意笞辱之。
“石门聪”即临济六世“慈照蕴聪”,“慈照”是其师号,因住持襄州石门寺又名“石门蕴聪”。或许事关佛门受辱,“《石门录》独不载二事。此皆妙喜(大慧宗杲)亲见无尽居士(张商英)说”。又《罗湖野录》记载:
云居舜禅师,世姓胡,宜春人。以皇祐间,住栖贤而与归宗宝公、开先暹公、同安南公、圆通讷公,道望相亚。禅徒交往,庐山丛林于斯为盛。居无何,郡将贪墨,舜不忍以常住物结情固位。寻有谮于郡将,民其衣,乃寓太平庵。
“栖贤舜”即云门五世云居晓舜,因住持栖贤寺又名“栖贤舜”。尽管晓舜后被“大觉(怀琏)迎至净因,居以正室”,终由仁宗认可其道行,命“依旧为僧,再住栖贤寺”。但怀琏仍认为“祸患藏于隐微,发于人之所忽。用是观之,尤宜谨畏”。而晓舜“言忤郡将而获谴,名闻天子而被宠”的经历,大概也加深了云门禅师对至高权力作用于传法的认识。《林间录》记载惠洪观怀琏著述的感受有云:
惠洪虽有意回护怀琏,但不能改变怀琏“委曲事君”的事实,只能承认怀琏“应机之法不得不尔也”。怀琏的处事态度非其首创,追溯渊源发端于云门祖师。自云门僧人跻身汴京敕差住持的高位,臣属于人主的姿态越发明显起来。《禅林僧宝传》记载神宗召宗本入延和殿的对话:
上问:“受业何寺?”对曰:“承天永安。”上喜其真喻,以方兴禅宗,宜善开导之旨。既退,上目送之,谓左右曰:“真福慧僧也。”
按:宗本出家后师事苏州承天永安道升禅师。“承天永安”一词在此处却又一语双关指受到皇帝眷顾。宗本巧答使其地位更上一层,“都邑四方,人以大信”。
与宗本住持慧林相对,同宗本开法智海,更是将云门僧人依附皇权的一面加以发扬。《建中靖国续灯录》记载本逸上堂有云“臣僧奉敕开堂”。云门禅师摇身一变为天子臣属,“为国开堂”就成为传播云门法脉的合法理由。宋朝统治者本就相信“浮屠氏之教有裨政治”。云门禅师关注世间法、关怀人间秩序重建的倾向,以及对人主的绝对臣服,正好使其成为王朝教化体系的一部分。如石熙载与赵普上奏称云门二世洞山守初“化于此邦,补助圣化”;又如宋朝出使按察夷人所献地,使者遣云门五世惠立“先入示信,夷人屈膝受指”;再如荆湖南北察访使章惇请云门五世兴化绍铣开谕群蛮。
相形之下,同时代的临济禅师却表达了另一种倾向。《禅林宝训》引《坦然庵集》记载五祖法演对郭功辅说:
自古佛法虽隆替有数,而兴衰之理,未有不由教化而成。······今之人不如古之人远矣。必欲参究此道,要须确志,勿易以悟为期。然后祸患得丧,付之造物,不可苟免。
四 结论
综上所述,云门僧团在北宋迅速兴起的原因在于:第一,云门僧团传法体系与王朝统治相协调。禅宗世系类似海量扩张的宗族,为试图创立服从于王朝政治统一的佛教秩序提供了一种意识形态上的框架。第二,云门禅师说法兼容儒道的思想特性,使其获得士人、特别是东南地方官员的支持。十方住持制度的背景下,禅师唯有通过官方任命方可出世传法。因此,取得地方官员支持是云门僧团崛起的必由之路。和其他禅宗僧团不同的是,云门僧团加强了内部的团结,即便僧团内各支代有兴替,僧团整体传法得以延续。第三,云门僧团在取得地方官员支持之外,更积极谋求在都城开法,赢得最高统治者的支持。向最高统治者臣服并成为王朝教化体系的组成部分,成为其在北宋时期禅宗僧团中脱颖而出的关键。
不过宋金易代之际,云门僧团却盛极而衰,走上了败亡的道路。经统计,云门八世禅师共172人,人数较七世出现断崖式下跌,终断了自云门二世时期起稳步上升的基本趋势。而将云门八世僧人的分布标示在地图上可以发现,秦岭—淮河以北传法的云门僧人较之云门七世时期已经大幅减少,仅有5人。出现这种现象的最重要原因是南宋撰修《联灯会要》《嘉泰普灯录》对于北方云门禅师的遗漏。靖康之难后,原先北宋包括东京在内的大片疆土沦于金人之手。云门僧团因“列派皇都”,有相当部分禅师滞留于金朝境内。但不可否认的是,云门僧团确实衰落了,至明代其竟“嗣法莫可考”。
与王朝统治者的密切关系造就了云门僧团在北宋的辉煌。也因其与政治的过分亲近,导致其在王朝易代时遭受比其他僧团更大的打击。《禅林宝训》引《庐山野录》记载圆通居讷警句:“挟外势以为重者,一旦失其所挟,皆不能免颠溺之患”,真可谓一语成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