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正如黑格尔所说,传统文化下的中国人缺少自我意识。而“我”在中国的诞生其实是在白话文之后。西方文化传入,开始让中国人逐渐形成法权、人格意识。这样的“我”,其实兼具“个我”与“大我”的含义,“我”于是同时具备了个体性与普遍性。
但大多数中国人还没有真正养成这一现代人意识和品质。中国人的“我”仍然是持戈防敌式的戒备型人格特征。因此,中国人一方面天生就有政治性,一辈子都在搞政治,但另一方面,却从来不曾走出自身,与他者进行真正的较量,而只有在真正的较量之后,才能走向和解,从主奴关系变成所有人的自由平等。
也就是说,中国人的“我”仍然是原始的、无法异化的,因此他无能走向自由之路。这种原始的“我”是沙粒化的,因此,谁暴力谁就可以奴役他人。尽管在甲骨文中“我”是用刑杀人或肢解动物的凶器,但由于这样的“我”是无人格的,因此他并没有反抗能力。
而在拉丁文中,表示“我”的词汇主要有以下两个:ego,是第一人称单数主格,直接表示“我”或“我自己”,常用于强调主体身份;me,是第一人称单数宾格,用于动词或介词后的宾语位置,意为“我”或“我的”。可见,拉丁文中的“我”,既有主体、受动等意识,又将我与非我合于一身。它代表了一种真理普遍性,正如黑格尔的“我即我们”。
中国人说“我爱你”,都是从电影中学来的。所以当我们对别人说“我爱你”时,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不自然。因为这不是我们的语言,我们缺少那样的思维方式。
尤其是,中国人都有自己的方言,在我的方言中是没有“我爱你”的。所以当我第一次想表达“我爱你”时,就感觉到了尴尬。于是只能选择普通话“我爱你”,但它仍然没有书面语的“我爱你”或英语的“I love you”自然。
“我爱你”是中文对应世界的创造物。“她”也是文化碰撞出来的。“她”字虽然在古代已有,但它读作“jiě”,是“姐”的古文。在现代汉语中,作为女性第三人称代词的“她”字,是20世纪20年代才出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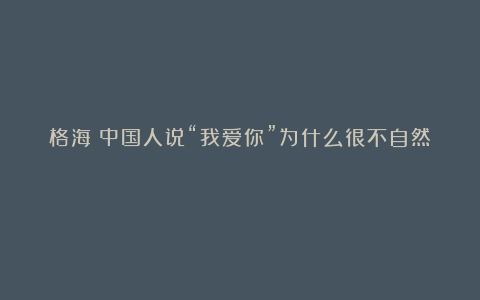
1917年,《新青年》的编辑部就“she”字的翻译问题展开讨论,刘半农第一次提出,可以新造一个字来用作女性的第三人称代词,这个新字就是女字旁的“她”。1920年在英国留学的刘半农因思念亲人,挥笔写下了《情歌》一诗,后来在赵元任为这首诗谱曲后改名为《教我如何不想她》。
日本人为了融入世界文明,非常注意日常的一言一行。但在日语中,“我爱你”也是外来的。日本人一般用“我喜欢你”“我珍惜你”之类,来表达爱意。
可见,每一种语言都代表了一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要看到自身文化的有限性,就得学习他者的语言。多语者思维更活跃,语言外语越多,思维也就越理性。
海德格尔说过“语言乃存在的家园”,实际上,语言才是一个国家真正的统治者。美国心理语言学家、认知科学家维奥丽卡·玛丽安的《语言塑造人类思维》一书认为,“我们使用的语言不仅影响着我们的大脑、身体、思想与感情,语言本身、语言多样性以及多语制对社会结构和功能的影响也深入骨髓。”
这本书谈到《圣经》中“巴别塔”的故事。当上帝降临人间,见到人类说着一样的语言,妄图造塔上天,便将人们分散于世界各地,并替他们创造了不同的语言,这样人们便无法相互交流,造塔之事自然无法达成。
巴别塔的故事说明了,语言具有非凡力量。语言既能促进交流,也能阻碍沟通。要想看到更大的世界,除了学习他人之外,没有捷径可走。
按照海德格尔的思想,语言既“解蔽”(让存在显现),也“遮蔽”(让某些存在隐而不显)。语言就像是一束光,照进世界的某个角落,让我们看清了那儿的模样(解蔽);但同时,光的照射也让其他地方陷入了阴影,我们看不见那些没有被光照到的部分(遮蔽)。正因如此,我们在使用语言、思考存在时,需要保持一种开放、反思的态度,意识到语言本身的这种双重性。
但中国人的生活态度是自我禁锢的。中国人对他人的戒备,最日常的表现就是语言上的戒备。对“我爱你”这种大胆表达,中国人往往报以怀疑甚至嗤笑。只有现代意识较强的人,才能将其变为日常。
祝福所有陌生人,无论世界怎么变化,只要去爱,世界就是我们的。法国哲学家巴迪欧说过,“爱是共产主义的最小单元。”爱是挣脱自我、回归自然的超越之路。哪一天中国人能够大声呼唤“我爱你”,让天空听得见,让白云看得到,那么,我们就真的成了一个高信任度的文明。
#artContent img{max-width:656px;} #artContent h1{font-size:16px;font-weight: 400;}#artContent p img{float:none !important;}#artContent table{width:100% !import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