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薇
【内容提要】南梁萧统所编的《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其在历史传承中经历了辗转传抄与刊刻的过程,逐渐形成今人所见的文本形态。其间,在唐代出现两个极为重要的注本——李善注本和五臣注本。自《文选》付诸版刻以来,李善注、五臣注及合注等多种刊本流行于世。在校勘整理并刊刻《文选》的过程中,人们逐渐塑造了一种仅在二注关系当中思考《文选》异文来源的“二元对立”认知方式。这表现为人们往往好将《文选》异文的产生归咎于二注。然而近代以来,随着《文选》新材料的发现,仅凭二元对立的认知方式来思考《文选》异文来源,既不符合部分异文的实际情况,亦无法满足当下对《文选》的继承与学习的需要。突破二元对立的认知限制,将《文选》纳入更为广大的传抄、刊刻与编注的发展过程之中进行思考,方能更为准确地理解《文选》异文来源,探求《文选》的本来面貌。
【关键词】李善本 五臣本 二元对立 《文选》异文
作为一部收录先唐作品的文学总集,《文选》在中国传统社会乃至整个东亚汉文化圈当中长期发挥着文章典范的作用。然而今人所见《文选》的面貌,则经历了相当漫长而曲折的演变过程。从南朝梁代诞生之初至隋唐时期,《文选》由最初的三十卷白文本,逐渐发展出释音、释义等内容有别、卷数各异的诸家注本,其中以李善和五臣的影响最大。五代迄至两宋,《文选》的传播方式从手抄逐渐转变为雕版印刷。官方与民间涌现出善注刊本和五臣刊本,随后又出现了李善与五臣的合注刊本,一种是五臣注在前、李善注在后的六家注本,一种是李善注在前、五臣注在后的六臣注本,由此奠定了《文选》流传至今的文本形态。
《文选》的文本面貌也在此传承过程中产生许多变化。一方面,李善本、五臣本及合刊本的流行,让白文本及其他诸家注本无人问津以致失传。另一方面,作品及注释在辗转传抄过程中产生的讹脱衍倒,虽经刊刻整理有所减少,但是仍然存在、甚至新增不少鲁鱼亥豕的现象。
因此,恢复《文选》原貌,成为历代整理与刊刻《文选》者追求的目标。这个目标涉及一个重要的工作步骤:校出异文,审订是非。这便涉及如何理解《文选》异文的来源。而以清代胡克家《文选考异》为代表的历代《文选》校勘成果,普遍将异文来源归咎于李善本与五臣本的区别,甚至进一步认为是“五臣乱善”,意即乃是五臣所致。
这种仅从二注身上寻找解决问题答案的思路,体现的是一种“二元对立”的认知方式。这种认知方式虽有其形成的背景与脉络,却将二注本的关系高度对立起来。而且,正如前人留下了不少“无可考”的阙疑之处,《文选》尚有诸多异文,难以依靠此认知方式形成圆满的解释。
幸运的是,近代以来进入学界研究视野的敦煌、吐鲁番出土的残卷,日本保存的古钞本,乃是属于刊本之外的传抄系统,而且“天下孤本”《文选集注》还保存了许多二注以外的亡佚注释,提供了《文选》合刊前的丰富信息。这对于帮助我们打破该认知方式,重新审视《文选》异文的复杂来源,了解《文选》文本面貌的形成过程,进而深刻认识中国经典从手抄到刊刻过程中的文本变化,将有极大的帮助。
五臣注自诞生之际起便具有与李善注针锋相对之意。唐开元六年(718),吕延祚进呈注本。其《进〈集注文选〉表》曰:
往有李善,时谓宿儒,推而传之,成六十卷。忽发章句,是征载籍,述作之由,何尝措翰。使复精核注引,则陷于末学。质访指趣,则岿然旧文。只谓搅心,胡为析理。
以吕延祚为代表的五臣,上表指摘善注“陷于末学”。二注关系本就有紧张之势,是不可忽视之事实。
二注之不同,可从“底本有别”与“注解有异”这两个层面进行理解。“底本有别”是指各注家所据底本不同,主要表现在个别用字、文章科段、分卷结构等存在差异。而这自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字、词、句的理解乃至全文主旨的把握。底本的差异可认为是影响注家的基础因素。“注解有异”则指各注家在各自底本的基础上,遵从各自师承传统,沿着不同的注释体例、方法和风格,形成对同一文本的不同理解。从《文选》二注来看,李善、五臣的注释行为皆围绕萧统《文选》展开,理论上底本差异不会非常大。但是作为一部集录经典诗文的总集,《文选》选录的作品多行于当世,再加上全书编成之后,曾长期以手抄的方式传播,“母本”会衍生出不同的“变本”,底本自然可能存在“变本”的情况。二注的底本究竟源自哪个“变本”,尚值得仔细琢磨。再者,五臣本原为异于李善注而生,重在“措翰”串讲辞章,因此势必与之分道而驰。自五臣注诞生,唐宋笔记多有比较二注的记载。如李匡乂《资暇录·非五臣》、邱光庭《兼明书》痛批五臣,而苏轼《东坡志林》、王得臣《麈史》认为善注可取。
尽管二注的紧张关系被反复言说,但是真正将二者进行系统、全面的比较,却是在二注合并刊刻校订的过程中才正式出现,而将《文选》异文的缘由完全归咎于二者的想法,也是在此后不断校勘的过程中被逐渐提炼出来。现存二注合刊本如奎章阁本的校语揭示了比勘过程。
目前学界所知首个将二注进行合并刊刻的本子,乃是五臣注置前、李善注置后,由秀州州府学在北宋元祐九年(1094)上梓的“秀州本”。该本今已亡佚,幸有朝鲜以之为底本的古活字排印本(学界称为“奎章阁本”)可窥一二:
今平昌孟氏,好事者也,访精当之本,命博洽之士,极加考核,弥用刊正(旧本或遗一联,或差一句,若成公绥《啸赋》云:“走胡马之长嘶,回寒风乎北朔。”又屈原《渔父》云:“新沐者必弹冠。”如此之类,及文注中或脱误一二字者,不可备举,咸较史传以续之。字有讹错不协,今用者皆考五经、《宋韵》以正之。)小字楷书,深镂浓印,俾其帙轻可以致远,字明可以经久。其为利也,良可多矣。——平昌孟氏《五臣本后序》(奎章阁本卷尾)
秀州州学今将监本《文选》逐段诠次,编入李善并五臣注。其引用经史及五家之书,并检元本出处,对勘写入。凡改正舛错脱剩,约二万余处。二家注无详略,文意稍不同者,皆备录无遗。其间文意重叠相同者,辄省去留一家。总计六十卷。元祐九年二月日。——秀州本《文选》跋(奎章阁本卷尾)
秀州本的李善注来自北宋监本,五臣注来自平昌孟氏本。秀州州学将经过官方严格校勘的北宋监本,和经由民间精心整理的平昌孟氏本合二为一。二注合刊的具体做法乃是直接以平昌孟氏本为底本,将监本李善注“逐段诠次”,“其引用经史及五家之书,并检元本出处,对勘写入”,在此过程中核正“舛错脱剩约二万余处”。尤值得注意的是,二注合并遵循了一定的体例:
1.二家注无详略,文意稍不同者,皆备录无遗;
2.其间文意重叠相同者,辄省去留一家。
这一点正体现为奎章阁本中“善本作某字”“善同某注”“善注同”等合并校语。这些校语作为一种事实陈述,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校勘整部《文选》过程中发现的异文情况。这也是李善本同五臣本从正文到注文的首次全面“交锋”。随后同出六家本系统的政和元年(1111)广都裴氏本(今据明代袁褧重刊本)、明州本(今据绍兴二十八年递修本),莫不沿袭着秀州本的校语。
而通过调换二注顺序(即将李善注置前、五臣注置后)所获得的六臣注本,如赣州本、建州本(咸淳七年前后,1271),校语便直接在原来六家本校语的基础上进行相应调整,径改为“五臣本作某字”“某注同”。这个过程也伴随着一系列核对工作,然而由于全书体量庞大,二注面貌及校语难免存在错讹。再加上二注合刊之际采用的省略体例,也对二注的原貌造成极大的改变。在以李善本为底本的六臣注本当中,五臣注为被省略的一方;而在以五臣本为底本的六家注本当中,被省略的一方反成了李善注。省略之后的原文不复保留,二者的注文面貌由此均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于是在单注本逐渐消亡,而合刊本渐为流行的情况下,时人为了恢复被省略的内容,在所见文本有限的情况下不得不取五臣注以补李善注,或取李善注以补五臣注。南宋淳熙八年(1181),尤袤深感“四明赣上,各尝刊勒,往往裁节语句”,时下流行的合刊本已失二注原貌。于是他“亲为校雠”,自己动手校订李善注,刊刻李善本。书末还附有《李善与五臣同异》,通过列出五臣异文的方式,体现二注之异,以析二注之貌。这种区分二注的做法,目的在于解决合刊本所造成的文本混乱,提供一个完善的《文选》读本。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比勘工作处理的是一些具体版本,所涉校语往往有着明确的指向。正如前举合刊本校语,其所谓“善本”“善”“善注”指向的是北宋国子监本所见李善异文;而所谓“五臣本”“五臣”同样指向那个具体的版本——平昌孟氏本所见五臣异文。然而,尤袤的校语未见相关的版本依据,尤袤仅提过“四明赣上,各尝刊勒”一句,或使用过今人仍可得见的明州本、赣州本。但其所说“五臣”是否纯出平昌孟氏本,而其所刊“李善本”又与今人所见北宋本并不完全一致,故其底本、校本等信息至今尚未得到证实。这就导致后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容易将具体版本当中的二注差异,理解成普遍意义上的二注差异。
果不其然,清代胡克家在整理尤袤所刊的李善本之时,进一步扩大了二注差异的适用范围,并将此视为《文选》异文的来源。他邀请顾广圻、彭兆荪细加考订尤本,撰成《文选考异》。其序文旨在批评尤本已失崇贤旧观,但是开篇却说:
《文选》之异,起于五臣……观其正文,则善与五臣已相羼杂,或沿前而有讹,或改旧而成误,悉心推究,莫不显然也。观其注,则题下篇中,各尝阑入吕向、刘良,颇得指名,非特意主增加,他多误取也。观其音,则当句每未刊五臣,注内间两存善读,割裂既时有之,删削殊复不少。崇贤旧观,失之弥远也。
所谓“《文选》之异,起于五臣”,便是视五臣注为造成《文选》差异的缘由。言外之意即李善本保留了萧《选》原貌,而五臣注破坏了崇贤旧观,也便破坏了萧《选》旧貌。《考异》也的确依据李善与五臣之别,从“正文”“注”“音”三个层面,提出了“各本所见以之乱善”“其本误衍,后又以之乱善”“五臣注错入”等批评五臣的说法,由此试图坐实五臣注乱善兼乱《选》的罪名,也不断渲染李善本与五臣本之间对立的紧张关系。
然而,上述“五臣乱善”等说法,显然并不符合另一种合刊系统的情况。在并五臣入善的六臣注本中,应当还存在“善乱五臣”的情况。但是,《考异》并未充分考虑其他具体的版本现象。胡克家覆刻尤本的目的在于提供一个李善本,乃是以善注为本位,因此对善注原貌的追求,自然容易使之视五臣注为导致善注已失原貌的“罪魁祸首”。而从李善本受到关注这一点来看,李善本和五臣本的地位孰高孰低亦是一目了然。从来只有地位低者才会被认为“乱入”“错入”地位高者。李善本与五臣本的对立关系,捧李善而杀五臣的认识,在清代《考异》当中达到了顶点。
当事实陈述被反复言说,便可能逐渐脱离诞生的文本环境,演变成一种价值判断,一种思考倾向。《文选》的异文来源非李善即五臣——一种二元对立的认知方式,从合刊本的校语,到单李善刊本的校勘记,逐渐清晰地浮现出来。
必须承认的是“二元对立”的认知方式是一个相当有力的工具,的确有助于剖析事实,厘清二注合刊本造成的问题。其发挥作用的文本现实条件是:二注有别是必然存在的现象,一部分异文的确能够作为善注与五臣注的区别性特征。前人在合并刊刻《文选》的过程中,通过系列校语清楚地标识出具体版本之差别,这一行为当然没有问题。兹举例如下:
尤本《洛神赋》“容与乎阳林”句之“阳林”,《考异》认为:“袁本、茶陵本’阳’作’杨’,云五臣作’阳’。按:二本是也。尤所见以五臣乱善。”
笔者按:《考异》认为“尤所见以五臣乱善”,意思是说尤本原作“阳”字,乃是根据五臣本改字。其实今人所见日藏白文古钞当中的杨守敬本、九条本和静嘉堂本均作“杨”,而监本系统亦作“杨”,如北宋本同,奎章阁本注记称:“善本作杨字。”这说明白文本和李善本有作“杨”者,所以《考异》认为“阳”为五臣本特征的结论可以成立。又,该句相应的善注曰:“阳林一作杨林,地名,生多杨,因名之。”《考异》曰:
袁本、茶陵本无“阳林一作”四字。按:二本是也。此尤所见盖有“阳林”,善作“杨林”,乃校语错入注,因改“善”作“一”以就之耳。
笔者按:《考异》依据袁本、茶陵本,判定善注没有“阳林一作”四字。此乃尤袤改校语“善作杨林”为“一作杨林”,并入注文。
上述例子展现出《考异》运用的三个本子:“袁本五臣居前、善次后,茶陵本善居前、五臣次后,皆取六家以意合并如此。凡各本所见善注,初不甚相悬,逮尤延之多所校改,遂致迥异。说见每条下。”即尤袤李善本作为覆刻底本,五臣在前的袁本和李善在前的茶陵本作为参校本。其中,袁本属于六家本系统,乃是以五臣本为底本,并善注入五臣本,因此善注原貌多被破坏。依据这样的本子来甄别善注并不可靠,故而还需参照当时所能找到的质量较好的其他版本系统,《考异》利用的是茶陵本。该本属于六臣本系统,乃是以李善本为底本,并五臣注入李善本,因此多得李善原貌。在所见版本有限的历史条件下,结合两个系统的合刊本校语和文本实际情况,辨析并厘清李善注和五臣注的各自内容,《考异》如此做法与判断合乎文献现状,也有助于甄别出二注的大致轮廓。
但是,这种做法从校出异同到分析原因再到审订是非,都仅从二注入手。做法行之有效的同时却也逐渐固化成一种非此即彼的认知死循环:《文选》之异在于二注。这种认知影响很大,从陈景云《文选举正》,到胡绍煐《文选笺证》、梁章钜《文选旁证》,均概莫能外。甚至,这种思维定式依然盛行于今天的学界。即便是面对最早的李善刊本北宋国子监本,日本学者冈村繁仍然提出了李善本在宋代刊刻时“剽窃五臣注”的说法,依然在二注关系当中展开思考。
当然,毕竟前人所作判断完全受制于客观条件。正如胡克家既没有看到比尤本更早的北宋国子监本,也没有看到单五臣注刊本陈八郎本,更没有发现手中的尤本并非初刊本。种种客观条件,既强化了原有的认知方式,也抹杀了成立的背景和范围,最终还留下了许多“无可考”之处。人类的认识往往深受客观条件的限制,我们无法据此苛责前人。
但是幸运的是,今天的我们能够掌握十分丰富的早期材料。除了《文选》白文本在敦煌、吐鲁番和日本已有发现之外,关于李善注的早期材料也惊现于世,主要有以下四类文本:
1.敦煌写本P.2528、P.2527中的李善注,涉及篇目《西京赋》《解嘲》《答客难》。又有一些零碎残卷,如郭璞《江赋》Дx.18292;张协《七命》有大谷10374;大谷11030;Дx.08011;Дx.01551;Дx.07305v;Дx.08462;Ch.3164等。
2.日本正仓院李善注拔萃。
3.若干古笔切,如传圆珍笔三井寺切,石川县立历史博物馆及立命馆大学藏古笔切。
4.日藏《文选集注》中的李善注。考虑到《文选集注》(以下简称“《集注》”)是一个合注本,各家注的汇集遵循一定的编纂体例,当中的善注能否真实展现李善本的面貌,暂且存疑。
五臣本的早期材料较为有限。敦煌、吐鲁番出土的残卷缺乏五臣注相关材料,导致五臣本的早期参照文献不足。但好在日本保存有三条家公爵所藏的单五臣注卷子本,《文选集注》也保留了数量可观的“五家本”。前者十分珍贵,为目前所见《文选》写钞本文献当中唯一的单五臣注写卷。
面对前人难以想象的丰富文献,我们不禁认识到以往认知方式有限的适用范围,而重新审视起《文选》异文的复杂来源。下文将借助写钞本材料,尝试通过校勘异文举例对“二元对立”认知方式展开突破。以下讨论所引正文使用胡刻本。
前人在校订《文选》的过程中得出这样一个判断:李善本与五臣本之异,即是《文选》异文的缘由。《考异》所说的“《文选》之异,起于五臣”,便是默认李善注的底本直接源自萧《选》,优于五臣注的底本,而且也默认早期文本亦是如此,进而推断《文选》所有异文的来源在于二注之别。
但是,二注在刊本当中呈现出来的差异并不意味着在写钞本当中也必然能够成立。善注钞本与五臣钞本的区别性异文为刊本系统所继承,固然是文本面貌的主流,但并不反映文本面貌的全部。通过校勘可知,善注写钞本可能异于善注刊本,五臣写钞本亦可能异于五臣刊本,甚至可能出现二注刊本有异而写钞本不异的现象。从这些异文现象来看,二注已各自存在混乱失次的情况。分析如下:
首先,二注在刊本当中出现的异文,在早期材料当中并不存在,可直接推翻既定认知。
《讽谏诗》“正遐由近,殆其兹怙”句,“兹怙”敦煌Φ242和杨守敬本、九条本、静嘉堂本均作“怙兹”。陈八郎鲜朝本、正德四年本、奎章阁本亦作“怙兹”。九条本、静嘉堂本旁注:“兹怙,关(笔者按,“关”指代“善”)。”奎章阁本注记:“善本作兹怙字。”尤袤《李善与五臣同异》:“五臣作怙兹。”
笔者按:“兹”,此,指汉戚身份。“怙”,依靠,凭恃。该句为韦孟劝诫元王之孙刘戊,不能怙恃汉戚身份,放纵横行以致危殆。二注的早期写钞本不异,均作“怙兹”,当为萧《选》旧貌,而非五臣本独有特征。《考异》曰:“袁本云善作’兹怙’,茶陵本云五臣作’怙兹’。按:各本所见皆非也。此但传写误倒,非善独作’兹怙’。何云当从《汉书》作’怙兹’,于韵乃协。陈同。”何焯、陈景云以为该句当作“怙兹”,一是从《汉书》,二是协韵。“兹”正与下文“嗟嗟我王,曷不斯思”之“思”协支部平声韵。
《与嵇茂齐书》“翅翮摧屈”之“翅”字,《集注》和杨守敬本、九条本均作“六”。陈八郎鲜朝本、正德四年本、明州本、奎章阁本同作“六”。奎章阁本注记:“善本作翅字。”明州本校语同。赣州本作“翅”,校语云:“五臣本作六。”而据《集注》中《钞》云“今此言六翮摧屈”和天津艺术博物馆藏107号敦煌单注本“自然摧屈六翮”句,可推知此二本正文当作“六”。
笔者按:原文抒发立功于世的雄心壮志,虎啸龙吟,极喷薄宇宙之致,惜遭司马氏篡魏乱世,有志不得舒展,所以是未能获得合适时机,只能垂下羽翼黯然远离,锋芒力量无处可使,翅膀羽毛摧残脱落。李善刊本作“翅翮”,可以解释得通。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五臣刊本所作“六翮”,多见于早期流传版本。除了白文本系统杨守敬本、九条本,还有注文本系统《集注》,可见李善注在写本中有作“六翮”的版本。另外《钞》和敦煌单注本也可以证明,传抄过程中存在多个版本作“六翮”。而且“六”字更便于书手传抄,能够符合写钞本的传播特征。因此,合刊本校语认为“六”是五臣本特征并不完全准确。而“六翮”专指鸟类双翅中的正羽,又代指鸟之双翼。如《战国策·楚策四》“奋其六翮而凌清风,飘摇乎高翔”,班彪《王命论》“燕雀之畴,不奋六翮之用”等句,都是用“六翮”表翅膀,以示振翅高飞的姿态。
其次,同一文本系统内部的“变本”颇多,就今人所见具体版本而言,其写钞本与刊本亦存在诸多差异。有李善写本异于李善刊本者:
《六代论》“而天下所以不能倾动”之“不能”二字,北宋本、尤本同。李善注拔萃、杨守敬本、观智院本作 “不”。奎章阁本注记:“善本有能字。”
笔者按:早期作“不倾动”与下句“百姓所以不易心者”之“不易心”显得更为整齐对仗,但是刊本中存在“不能倾动”的版本。
同上“徒以权轻势弱”之“徒以”二字,北宋本、尤本同。李善注拔萃、杨守敬本、观智院本作“徒”。奎章阁本注记:“善本有以字。”
笔者按:该句指出盖因权轻势弱,宗室子弟缺乏固定操守,所以才出现在惠帝文帝时尽忠尽孝,在哀帝平帝时背叛祖宗的现象。“徒”表仅仅、只是,单用“徒”字可理解得通。而“以”表因为,与“徒”连用,形成“徒以”。该词汇的使用由来已久,如“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战国策》),“盖徒以微辞相感动”(《登徒子好色赋》),“而蔺相如徒以口舌为劳,而位居我上”(《史记》),以及“徒以诸侯强大,盘石胶固”(《六代论》)。大概因此,刊本当中出现了“徒以”的版本。
也有五臣注写钞本异于五臣刊本者。譬如日藏五臣注钞本异于五臣注刊本:
《奏弹曹景宗》“致辱非所”之“致”字,陈八郎鲜朝本、正德四年本、奎章阁本作“累”。奎章阁本注记:“善本作致字。”但是三条本亦作“致”,反合于李善刊本而异于五臣刊本。
笔者按:该句悲悯司州之民因沦落敌手而无辜受辱,“致”在句中表造成、导致、招致,用法同下句“致兹亏表”。而“累”后接续动词“辱”,指屡次、多次,言无辜司民屡次遭辱,呼应前文“自逆胡纵逸,久患诸夏”,亦可说得通。
《与魏文帝笺》“优游转化”之“转”字,陈八郎鲜朝本、正德四年本、奎章阁本作“变”。奎章阁本注记:“善本作转字。”三条本亦作“转”,亦合于李善刊本而异于五臣刊本。
笔者按:“转化”用于表现声音之宛转自如,若用“变化”则失去该层含义。
以上为三条本异于五臣刊本之例。再如三条本、《集注》五家本异于各五臣注刊本:
《奏弹曹景宗》“优劣若是”之“劣”字,朝鲜正德四年本、奎章阁本作“当”。奎章阁本注记:“善本作劣字。”明州本校语同。赣州本作“劣”,校语云:“五臣本作当。”尤袤《李善与五臣同异》:“五臣劣作当。”三条本、《集注》、杨守敬本、九条本、陈八郎本作“劣”且《集注》无校语,可推知《集注》所见五家本亦作“劣”。
笔者按:“劣”当为萧《选》旧貌。上句言“道恭云逝,城守累旬;景宗之存,一朝弃甲”,引出“生曹死蔡”的喟叹,孰优孰劣,对比鲜明。
《答临淄侯笺》“然而弟子箝口”之“然而”,朝鲜正德四年本、奎章阁本无。奎章阁本注记:“善本有然而字。”明州本、赣州本校语同。三条本、《集注》、杨守敬本、九条本、陈八郎本有且《集注》无校语,可反推原来五家本同,则五家本不同五臣刊本。
笔者按:有“然而”两字当为萧《选》旧貌。《新校订》编者按曰:“此’然而’为承接连词,犹云’如是而’也,与今习用之’然而’为转折连词者,其义有别(参王引之《经传释词》卷七)。盖后人以习语读此故妄删之矣。”是也。该词接续“弟子箝口,市人拱手者”一句,运用的是“然而……者”的表达句式,表示一种现象或结果,借此暗中称扬曹植的作品:这是圣贤卓绝出众、异于平庸凡俗之作。这个表达句式能够起到连接自然、语气流畅的作用,确实与今人惯用之表转折的“然而”有所不同。
再次,二注系统从写钞本到刊本还存在彻底变异。譬如:
《西京赋》“濯灵芝以朱柯”,“以”奎章阁鲜朝本、正德四年本、陈八郎本作“于”。北宋本、尤本作“以”。赣州本作“以”,校语云:“五臣作于。”但是P.2528、上野本、九条本、正安本、弘安本均作“之”。
《答客难》“黈纩充耳所以塞聪”,“充”陈八郎鲜朝本、正德四年本、奎章阁本作“蔽”。奎章阁本注记:“善本作充字。”尤袤《李善与五臣同异》:“五臣充作蔽。”然而P.2527、杨守敬本、九条本均作“塞”。
笔者按:上述二例的写钞本异文(“之”与“塞”)复见于敦煌出土残卷和日藏古钞,分布于多个文本来源,当非偶然讹误所致,而是暗示了某一个共同的源头。“以”与“于”、“充”与“蔽”,或是在二注的传抄或刊刻过程中产生的异文,可算是二注刊本的区别特征,但非《文选》早期旧貌。
最后,二注在刊本无异文的情况下,其写钞本也可能存在变化。例如:
《答客难》“修学敏行而不敢怠也”,诸刊本不异,P.2527、杨守敬本、九条本无“修学”。
《答客难》“得信厥说”,“得”下诸刊本不异,P.2527、杨守敬本、九条本有“明”。
《解嘲》“下谈公卿”,“卿”诸刊本不异,P.2527、杨守敬本、九条本作“公王”。
笔者按:若非确实存在两个以上的版本可供证明,上述异文在二注刊本系统中将无法被识别出来,而且由于并不影响具体文义,理校之法亦毫无用武之地。刊本不异而写钞本异这一重要的《文选》文本现象,同样是化解二元对立认知的重要视角。
基于上述分析可知,二注系统在传抄阶段和刊刻阶段均存在一些差异。善注钞本可能异于刊本,五臣钞本也会异于刊本,甚至二注写钞本均异于刊本。这些现象促使我们认识到,不能单凭刊本便遽然断定《文选》异文的产生环境,进而推断异文的形成缘由。因此,前人在校订刊本过程中所说的“五臣作某”“李善作某”“五臣乱入”等意见,放在写钞本身上未必成立。这也正是傅刚师所提到的刊本特征并不能适用于写钞本的重要论断。写钞本与刊本毕竟是两种不同的文献形态,从手抄本到刊本之间存在的种种文本流变现象均值得仔细推敲。
更何况,《文选》在刊刻之前,不但长期以手抄方式流行,而且存在多个文本系统。如今,白文本得以发现,注文本方面则有赖于《文选集注》对诸家唐注的保存。更多文本系统的发现,乃至不同文本系统的共存,有助于进一步突破二元对立的认知方式。
确认并考察超出二注以外的文本系统,同样能够有力地突破二元对立的认知方式。现已发现二注以外的文本系统共计三类,一是白文本系统,二是集注本系统,其在二注之外还提供了《钞》《音决》和陆善经注。三是无名注系统,主要是敦煌出土的佚名注和单注本,包括俄藏Φ242号的“佚名注”,永青文库、天津艺术博物馆藏107号敦煌单注本和P.2833、S.8521的“文选音”。这些已经亡佚的唐人注释,与二注既有相同,也有差异,因此更为直接地冲击着既有认知。
首先,白文本系统正是注文本系统之外一个无法忽视的存在。不少在合刊本中被认为是二注有别的异文,也存在合于敦煌残卷与日藏古钞的现象。此乃“萧《选》旧貌”的特征,具体例证可参前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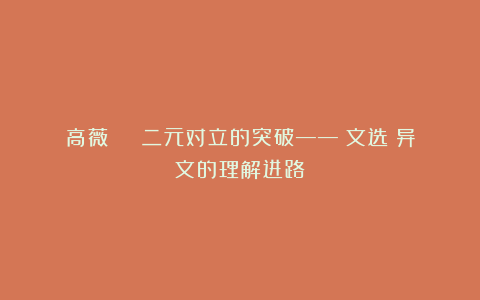
其次,在注文本系统当中,除了李善本系统和五臣本系统之外,尚存在其他注本,即前举《集注》中诸家唐人注和敦煌无名注。如此一来,二注刊本当中出现的异文,也可能与二注无关,而与其他注本发生关联。
一方面,存在正文用字合于其他文本系统的例子。譬如:
《出师颂》“五曜宵映,素灵夜叹”句下,奎章阁本注记:“善本有’皇运来授,万宝增焕’二句。”明州本校语同。《集注》和朝鲜正德四年本、奎章阁本均无此二句。《集注》按:“陆善经本此下有’皇运来授,万宝增焕’二句。”北宋本、尤本、赣州本有此二句,但赣州本无校语。
笔者按,由《集注》正文可知李善本的早期材料存在无此二句的版本。然《集注》按语指出,此乃陆善经注本的特征,则北宋本、尤本、赣州本合于陆善经注本的特征。奎章阁本与明州本的校语指出“善本”有此二句,正因其所说“善本”即为北宋本。
《夏侯常侍诔》“贤良方正征仍为太子舍人”,《集注》和杨守敬本、北宋本、陈八郎鲜朝本、正德四年本、奎章阁本、明州本、赣州本无“仍”字。《考异》谓“此尤本衍”。《集注》按:“《钞》、陆善经本’征’下有’仍’字。”
笔者按,尽管合刊本对此没有出校,但是《考异》认为是尤袤添上“仍”字。据《集注》按语,“仍”是《钞》和陆善经注本的特征。《晋书》卷五十五载其仕宦履历:“少为太尉掾。泰始中举贤良,对策中第,拜郎中,累年不调”,“后选补太子舍人,转尚书郎,出为野王令”,此后“居邑累年,朝野多叹其屈。除中书侍郎,出补南阳相。迁太子仆,未就命,而武帝崩。惠帝即位,以为散骑常侍。”可知在选补太子舍人之前,夏侯湛长期担任郎中一职,“仍”字无所依傍。
另一方面,也存在注释合于其他文本系统之处。
如合于陆善经注之例:《集注》卷八《三都赋序》中有陆善经的注释,陆善经说“旧有綦毋邃注”并引用了綦毋邃注释五条。据《集注·蜀都赋》“刘渊林注”下的陆善经曰“綦毋邃序注本及《集题》”云云,说明陆善经得见綦毋邃序注之本。上述五条内容未必皆为陆善经所引的全貌,可能已经《集注》的编纂。而这五条注在李善本中也得到了保留,现存最早的李善本北宋本便有相应的内容。但是北宋本却无其他说明,使人长期以为该注出自刘逵之手。从这个例子来看,陆善经所引旧注,不知何时变成了善注刊本所引旧注。
又合于《钞》之例颇多。例如李善本方面:
《难蜀父老》注“毛诗小雅文滨涯也本或作宾”。《集注》善注有’毛诗小雅文’,其余七字见于《钞》:“率,循也。滨,涯也,或本为宾字者。”《新校订》编者按:“则此七字盖后人改正文’宾’为’滨’,又略取《钞》文以充善注耳,且’滨涯也’乃《毛传》文,若善引之,例当在上有’毛苌曰’三字。知其非善自注无疑。”
再如五臣本方面:
《檄吴将校部曲文一首》注“良曰:侯成,小吏。不知其所赏也”,又见《钞》曰:“侯成,小吏,不知所赏也。”《新校订》编者按:“良乃袭《钞》注。”
合于《音决》之例则有:
《与魏文帝笺》“繁休伯”下,陈八郎鲜朝本、正德四年本、明州本、赣州本、奎章阁本均有五臣吕向注音:“繁,步何反”。三条本无该音注。《集注》无五臣注,但见于《音决》:“繁,步和反”。《新校订》编者按:“五臣音例夹注在正文间,不在注末。此当是善音。日藏三条家五臣本向注无此音,而集注本善注末正有此音可证。今移此四字于善注末。尤本善注脱此四字。”
笔者按,从注音体例可确认该注音并非五臣音。但是根据《集注》,李善无此音注,反见于《音决》,恐怕出于《音决》。《新校订》按语有误。
以上主要以《集注》的诸家唐人注为比照对象,此外另有合于敦煌佚名注之例,多出自尤本李善注。譬如直接合于原文的例子:
《讽谏诗》“乃命厥弟,建侯于楚”句,敦煌Φ242注曰:“厥弟谓元王。元王封于楚国也。”
尤本善曰:“弟谓元王也,元王封于楚国。”
陈八郎本良曰:“厥弟,元王也。建,立也。谓立为侯伯于楚。”
笔者按:尤本此条善注不见于奎章阁本、明州本、建州本等合刊本,且在今本《汉书·韦贤传》中无对应出处。然而这条注文,特别是后半句话“元王封于楚国”完全合于敦煌佚名注。再如合于释义的例子:
《讽谏诗》“在予小子,勤唉厥生”句,敦煌Φ242注曰:“言生时唉唉啼泣。自谓言叹辞。”
尤本善曰:“应劭曰:’小儿啼声唉唉。’颜师古曰:’唉,叹声。’善曰:’《方言》曰:唉,叹辞也,许其切。’”
陈八郎本翰曰:“予小子,孟自也。唉,叹也。勤叹其生之为微也。”
笔者按:尤本中的《汉书》应劭及颜师古注共十六字,不见于奎章阁本、明州本、建州本等。《考异》说袁本、茶陵本无“应劭曰”以下十六字。尤本多出的善注实合于敦煌佚名注。因为从内容的理解来看,尤本的善注与敦煌佚名注相近,而五臣注与之相远。“在予小子”之“小子”,敦煌佚名注解作“小儿”,“勤唉戚生”之“生”,敦煌佚名注则释作“生时”,整句理解为婴儿出生之时唉唉啼哭,正是尤本善注引《汉书》应劭作“小儿啼声唉唉”之意。然而,五臣李周翰则将“小子”理解为韦孟自称,“厥生”理解为“其生”,表自我生平,进而引申为一种“其生之为微”的感叹,与前二者谈出生小儿啼哭的内涵截然不同。
总而言之,二注刊本从正文到注文均存在合于其他文本系统的情况揭示,二注之异文可能源自二注之外,故不可光在二注的范围内进行理解,更无法以“五臣乱善”为理由去处理《文选》文本产生的一切异文。正是基于此,二元对立的认知方式便应当被重新审视和谨慎对待。
纵览《文选》由手抄到刊刻的诸种异文,揭示出文本从“母本”到“变本”的衍生过程。而《文选》从白文本到注文本的形成历史,也说明《文选》文本系统具有多样性。上述现象促使我们对此进行反思:无论是二注内部的差异,还是二注以外的文本系统,均突破了以往非李善即五臣的惯有认知方式,为我们重新审视二注关系及《文选》异文的真正来源打开新局面。这也是我们破除二元对立认知之后面临的迫切问题,如何全面理解《文选》从正文到注文出现的异文。
如何看待《文选》异文的产生缘由,既有认知亟须跟随新材料的出现而获得调整与修正。以往限于早期材料的不充分,我们对《文选》在传抄与刊刻过程中的很多细节并不了解,对《文选》异文的理解也有不少存疑之处。以下将尝试结合前文讨论,逐一检讨刊刻、传抄、编注等环节对异文形成的影响,把握不同环节所对应异文的判定条件。
(一)刊刻环节
由于刊本材料相对丰富,前人往往习惯先从刊本身上寻找原因,下意识地认定异文乃是在刊刻环节中产生,由此也发现了很多文本例证。又李善本和五臣本的刊刻者,现有明文记载的官方刊刻者为“北宋国子监”,私家刊刻者为“綦毋昭”和“尤袤”,因此刊刻环节中产生的问题往往归咎于上述机构或人物。
刊刻行为的确会对《文选》文本面貌产生影响。刊刻过程中发生的校勘、整理结果,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文本的面貌。反映《文选》刊刻过程的文献记载除了前举秀州本和尤本,还有北宋本和陈八郎本。
奎章阁本卷末的《李善本文选跋》揭示出天圣明道年间官方刊刻李善本的情况。据跋文可知,是书分别于天圣三年(1025)由七人共同完成底本校勘,于天圣七年(1029)完成雕版,参与过底本校勘工作的公孙觉和黄鉴,又再次参与了印版的校勘。这次的印版校勘可能又进行了一些订正,因而又历时两年,最终定板进呈天子。进呈者包括蓝元用、皇甫继明、王曙、薛奎、陈尧佐、吕夷简。
由此可见,北宋国子监本的刊刻不但经由多人整理,更是经由多次校订而成,并非仓促草就。参与校勘工作者主要是国子监说书,其中两次参与校勘工作的公孙觉,天圣七年右至国子监直讲。此前天禧五年(1021),时任内殿承制兼管勾国子监刘崇超曾上奏“内《文选》只是五臣注本,切见李善所注该博,乞令直讲官校本,别雕李善注本”(《宋会要辑稿》职官二八之二《国子监》),可见国子监本版刻之本,包括了国子监直讲官讲授所用之本,亦是官方认可的文本。
他们的校勘整理成果,塑造了《文选》李善注刊本的面貌;该版本一旦雕版发行,刊刻环节对文本的影响就此保留下来,直到下一次的校勘工作来临。
来自非官方的刊刻行为亦是同理,陈八郎本牌记曰:
凡物久则弊,弊则新。《文选》之行尚矣,转相摹刻,不知几家,字经三写,误谬滋矣,所谓久则弊也。琪谨将监本与古本参校考正,的无舛错,其一弊则新与。收书君子,请将见行版本比对,便可概见。绍兴辛巳龟山江琪闻。
该书刊刻于福建建阳崇化里,属于“建本”。根据绍兴辛巳(1161)江琪的记述,该书使用了“监本”和“古本”参校,以做到“的无舛错”。这也表明,即便是坊间刊本,也会对文本进行整理之后再行版刻之事。而市面上流通的《文选》版本,是“转相摹刻,不知几家”,展现了多家出版的盛况。
然而就在如此号称精心考校的情况下,二注当中仍有不少光从刊刻环节难以理解的地方。按理说各类“舛错”本应在轮番校勘过程中无所遁形,面对二注存在不少合于其他文本系统的异文现象,许多前辈学者仍然习惯从刊刻环节寻找解释。王立群先生看到前述陆善经所引的五条綦毋邃注复见于善注刊本,指出这是由于“北宋天圣监本的刊刻者不愿刻板地遵从《三都赋序》只能存留刘逵注与李善注的体例,破例地保留了綦毋邃注,只是囿于《李善注文选》的体例,无法在注释中保存綦毋邃的姓名,才采取了存其注释而略其姓名的特殊处理”。而刘群栋先生则提出“明显是北宋本李善注校理者取《钞》入善注之处”“北宋本校理者及南宋时期尤袤刊刻李善注时,应该看到过类似于今天所见《文选集注》残卷的集注本子,并参考吸收了《钞》、陆善经注以及类似于集注本的李善注”等理解。刘先生参与了《新校订六家注文选》的整理工作,上述说法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新校订》的整理意见,前述转引的《新校订》编者按语也多次表达“北宋本取集注本之《钞》而入于善”的说法。
刊刻环节诚然会产生异文,但正如前举二注在写钞本与刊本当中均存在异文,已充分说明刊刻并非异文产生的唯一来源。朱晓海先生曾在假定《集注》所录的五臣注为原貌的情况下,探讨了明州本、陈八郎本中远为丰富的五臣注来源,仍然得出五臣注的“剿袭在晚唐之前已经开始”和“中、晚唐世间流传的五臣《注》本不止一种”等结论。这启示我们,刊本呈现出来的问题不可完全归咎于刊本,而更可能发生在刊本诞生之前。
(二)传抄环节
当传抄材料进入到研究视野之中,我们终于有更多的实例可以证明,刊刻环节无法解释的现象,可能来自传抄环节。首先应当指出的是,刊本所出现的异文理应在对应的写钞本中便已存在。因为从同一系统的继承性质来看,晚出的文本理应具备早期文本的特征。换言之,善注钞本与五臣钞本的区别性异文当为刊本系统所继承。在这个意义上,异文形成于传抄环节的判断无须多言。
但是,经由前举例子可知,从传抄到刊刻产生的文本之间具备多种对应的现象,因此仍有单独讨论的必要。若是写钞本异而刊本不异的情况,由于刊本晚出,所以我们一般径直认为是写钞本存在异文,晚出的刊本进行了更正。这种情况的异文自然来自传抄阶段。但是还存在二注的写钞本异、刊本也异的情况,则指向了两种可能性:或是刊本阶段出现的异文,或是传抄阶段出现的异文。为了确定异文出现的阶段,我们需要引入其他文本系统,一般选择的是反映了萧《选》旧貌的白文本系统作为参照。当二注刊本用字合于白文本,则二注写钞本异于白文本,可以说明注文本系统在传抄当中产生了异文,后在刊刻之际获得了订正。
而对传抄环节的充分理解,将帮助那些在刊本当中无可考订的异文寻得来源。例如:
《西京赋》“乃览秦制”,《考异》指出袁本、茶陵本“乃”上有“尔”字,认为“此无以考也”。
笔者按:北宋本、尤本无“尔”字。奎章阁本有“尔”字。上野本、正安本、弘安本有“尒”,九条本直接作“尔”。
《夏侯常侍诔》“入侍帝闱”,《集注》、杨守敬本同作“闱”。九条本、陈八郎鲜朝本、正德四年本、奎章阁本作“闼”。《考异》指出袁本、茶陵本“闱”作“闼”,但是却认为该字“此无以考也”。
笔者按:《集注》中按语已经提示:“今按:五家本闱为闼也。”
《考异》所提出“无可考”之解释,乃是限于所见材料,无法寻得异文出处。但是这些例子往往在写钞本当中可找到版本依据。隐藏在不同刊本之间的矛盾,答案可能远在刊本之外。
传抄环节产生异文的因素多种多样,值得一提的是抄写形制也可能造成文本面貌的改变。比如为了行款整齐美观而增字,《答东阿王笺一首》“焱绝焕炳”句,三条本向曰多“焱,火光;焕,炳,皆明也”八字,便是为了补足行末空白。类似情况虽然不影响具体文义,却是在传抄环节才会形成,并造成文本面貌的改变。尽管有的内容可能经由刊刻加以整理,但是作为底本所产生的影响实在不可估量。
在排除了传抄环节导致的异文之外,是否存在另外的理解进路?当下种种对刊刻、传抄环节中的推测,我们都不妨往文本成立更早的阶段去追溯,即考察注文形成与编纂之际的情况。
(三)编注环节
注文本系统的形成过程及其内部充满了多样性:首先注文本系统的底本——白文本,并非有且仅有一个版本;其次注文本系统在形成的过程中存在改动白文本系统的情况(如李善改三十卷本为六十卷);而且注文本系统的形成有各自的体例和风格(如李善注和五臣注具有不同的注释体例和特点)。如此种种因缘也为异文的发生提供了契机。下面试以文献记载和文本例证探寻蛛丝马迹。
1.善注本存在多个“变本”
《文选》李善本自身存在多个“变本”,唐人早有记载。《新唐书·李邕传》说“始善注《文选》,释事而忘意,书成以问邕。邕意欲有所更,善因令补益之,邕乃附事见义,故两书并行”,表明了李善之子李邕参与了李善“变本”的生成过程。而李匡乂《资暇集·非五臣》则记载:
代传数本李氏《文选》,有初注成者,覆注者,有三注四注者,当时旋被传写之。其绝笔之本,皆释音训义,注解甚多。余家幸而有焉。尝将数本互校,不唯注之赡略有异,至于科段互相不同,无似余家之本该备也。
李匡乂并没有提及李邕之名,但所谓“初注、覆注、三注四注”大概已能反映出晚唐李善本在辗转流传抄写过程中的复杂现象。“绝笔之本”不论是否为李善真正的绝笔之书,乃具有“注解甚多”的繁复特点。“数本”证明抄传甚众,“赡略有异”表明各传抄本之间互有异同,且注释详略不一,甚至连正文的“科段”也存在一些差异。则不单是注文内容发生了变化,相应的下注位置也互有不同。当然,李匡乂所握之“数本”,后来流落何处,是否为宋代刊本所吸收,已无从考究。但从各种刊本跋文说明的情况来看,刊刻者在刊刻之前都有进行一番搜集工作,想必也会穷尽晚唐以来的写钞本。
这条记载直接证明了李善本在唐代存在多个“变本”的情况,甚至其中有些可能直接源于李善本人的修订行为。尽管这并不是造成文本异文的唯一理由,但应当是非常源头且关键的因素。
2.五臣袭他注的表现
李匡乂《资暇集·非五臣》最早提出,五臣注在形成之际曾对他注有所参考,且主要参考对象为李善注。在书中,李匡乂痛斥了五臣改字的现象:一是李善不随便改字,相反,五臣参考李善的出校而改动萧《选》旧貌。其曰:“(五臣)又轻改前贤文旨。若李氏注云’某字或作某字’便随而改之。”如以曹植乐府“寒鳖炙熊蹯”为例,其曰:“五臣兼见上句有’脍’,遂改’寒鳖’为’炮鳖’,以就《毛诗》之句。”法藏敦煌本P.2528的异文证实了上述说法。敦煌本中“臣善曰”引出的异文,虽与正文、薛综旧注用字不同,却往往合于五臣本用字,说明五臣曾依据善注改字。五臣改字的现象是“斯类篇篇有之”,这意味着五臣注存在改动底本用字的情况。
五臣除了从李善修改底本用字之外,注文方面也对其他本子有所参照。李匡乂指出“因此而量五臣,方悟所注,尽从李氏注中出。开元中进表,反非斥李氏,无乃欺心欤”。宋人王楙《野客丛书》卷五“《文选》注谬”、卷八“二老归周”等认为五臣注文内容多承袭李善注。元人李治《敬斋古今黈》也指出五臣注“然则凡善所援理,自不当参举,今而夷考,重复者至居十七,殆有数百字前后不易一语者,辞札两费,果何益乎”。《考异》也常有指认“五臣袭善注”之处。如《关中诗》注“惴惴或喣嘘”,《考异》云:“五臣铣注云’熙犹喣也’,即袭善此注为之。”
在这一提示之下,前举五臣合于《钞》的例子,可知五臣注并非仅参考了李善一家。而五臣注文合于他注的现象,则在合注过程中被剪裁甚至省略,由此形成了新的文本面貌。正如合刊本选择省略二注重叠内容,该编纂体例又见于《集注》。
3.编纂体例的影响
将三条本、《集注》和五臣刊本对校可以发现,三条本及五臣刊本出注而《集注》无注者,共有5例,《集注》少注共有10例。例如:
《答东阿王笺》“陈孔璋”,《集注》无五臣注,三条本、陈八郎本、奎章阁本“向曰”,合于善注引《文章志》。
笔者按,关于“陈孔璋”名下注,五臣注的古钞和刊本均有一条“向曰”,《集注》却没有五臣注。这种情况或是《集注》缺注,或是他本增注。然而,由于多个五臣本均有该条注文,且各本之间不存在直接联系,可知其底本便有该注。五臣本当比《集注》此类汇注本的内容更为完整。因此,这并非一种“增注”的行为,反而更像是《集注》的省略行为。
《奏弹王源》“以彼行媒同之抱布”句,三条本与陈八郎本“翰曰”较之《集注》多引《礼》与《诗》,合于善注。
《奏弹王源》“且非我族类”句,三条本与陈八郎本“济曰”较之《集注》多引《左氏传》季文子曰,合于善注。
《奏弹曹景宗》“载怀矜恻”句,三条本与陈八郎本“翰曰”较之《集注》多“载则也”,合于《钞》。李善无注。
《与魏文帝笺》“巧竭意匮”句,三条本与陈八郎本“翰曰”较之《集注》,多“竭尽匮乏也”一句,合于《钞》。
《奏弹曹景宗》“故能出必以律”句,三条本与陈八郎本“铣曰”较之《集注》多“《易》云师出以律”,善注与《钞》均有“《周易》云师出以律”一句。
上述例子证实《集注》省文合于他注的情况。这一省文体例正类同秀州本的二注合并体例:“其间文意重叠相同者,辄省去留一家。”文意重叠者悉数化为“善同五臣注”一句校语。《集注》中五家本的注文当因囿于编纂体例而有所裁剪,从而失去了原貌。当然也有的注文虽被裁剪,但找不到与其他系统的重合之处,比如《奏弹王源》“岂有六卿之胄纳女于管库之人”句,三条本与陈八郎本“良曰”比《集注》多“周礼有六卿”“掌管库贱人”二句,然从省缘由不详。
囿于编纂体例而改动注文的情况,同样会对文本面貌带来改变。因为这对文本的改动是一种大面积的、有意识的修改行为。这同二注合刊而引发的文本面貌变化的现象如出一辙。
利用《文选》新发现的写钞本材料同刊本的校勘结果显示,以往仅从二注身上来寻找《文选》异文原因的“二元对立”认知方式是一把双刃剑。这一认知方式诞生于李善本与五臣本的校勘过程之中,对应二注有别的特征,拥有一定的文献依据,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合理解决二注合刊造成的异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与现实指导意义。但是,上述校勘过程主要发生在宋代以降,且针对具体的刊刻版本,在此之前的《文选》主要依靠手抄方式进行传播,也存在二注以外的其他文本系统。因此,这一认知方式便具有一定的适用范围,不可泛论所有异文。
因此,通过二注内部的混乱失次及合于其他文本系统的异文分析,本文重新梳理了李善本和五臣本的关系认知,进而梳理出《文选》异文理解的三个进路:
第一,刊刻环节会形成新的异文。前人指出刊本中的“五臣乱善”现象,有些来自二注合刊的环节当中。但是,刊刻环节中发生的校勘、修改、讹误,尚不足以解释目前所见到的全部注文现象。
第二,传抄环节已经出现了二注混同、省略、剪裁的情况。这便导致了《文选》上梓刊刻之际,哪怕历经多次校勘,除非寻得更早、更接近原貌的本子,否则很难发现造成异文的实际来源。
第三,注者作注过程中的修订行为,注释汇编过程中设定的体例,也会影响文本的面貌。李善本存在多个“变本”的情况众所周知,五臣注对他注的参照亦不可忽视。汇编多家注释的从省体例,侧面印证了诸家注的重合现象。
上述三个理解进路,本文试图通过文本例证与文献记载详加说明。但是,想要进一步判定三者当中何者更为关键,则目前材料尚不足以对此做出圆满回答。从常理来看,显然文本一旦经由雕版发行,传播范围广,影响势不可挡。但若是论及更为深远、根源性的因素,则注文形成之际注家之作注行为实难轻忽。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artContent h1{font-size:16px;font-weight: 400;}#artContent p img{float:none !important;}#artContent table{width:100% !important;}